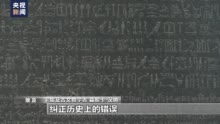3300多年前的古埃及墓穴壁畫中,這種羅非魚究竟有什麼神祕寓意

藝術品之所以珍貴,並不僅僅是因工藝材質或者好看,而是背後深厚的歷史社會背景,以及極富想象與創新的表現手法。最近,大英博物館新推出的《大英博物館人類簡史》《大英博物館動物簡史》引進出版,以人臉和動物兩條線索串起人類歷史,予人啓發。
作爲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大英博物館擁有藏品800多萬件,由於空間的限制,目前還有大批藏品未能公開展出。有了這些藝術珍寶,大英博物館還聯合世界上最著名的藝術出版社之一泰晤士&赫德遜打造這兩本書,強調書裏的文字和圖片能夠彼此結合,讓藝術成爲“沒有牆的博物館”。

書中不是像傳統歷史書那樣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是按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來展開,在每一章的同一主題下,彙集了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不同歷史階段的文物來進行講述;也不是通常的哺乳、魚類、鳥類這樣的動物類別體例,而是按照動物的社會屬性來劃分,由弱到強,從野生,馴養,珍藏,一直到人類自己虛構創造,從自然動物到非自然動物,來展開的。

全書精選大英博物館600餘件館藏品,藝術形式上,包含了繪畫、雕刻、手工藝品,以及一些珍貴的出土文物;風格上,有自然主義作品,也有諷刺主義的現實題材;時間跨度上,囊括了從遠古的冰河時期到今天。其中,《大英博物館人類簡史》選取了360件以人類面孔爲主題的藝術品。全球70多億人中,沒有任何兩個人長得完全一樣。每張面孔都是一種身份的標誌,是人類表達、情感和性格的主要載體。人類的一切經歷都寫在臉上。因此,人類的臉成爲藝術史上最強大、最永恆的主題,也是最適合來表現人類的生活。
《大英博物館動物簡史》選取了大英博物館260件動物相關的藝術品。人類對動物有着複雜的感情,無論是作爲經濟商品、人類夥伴,還是文化符號,動物都已經深刻地融入到人類社會中,成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類各個時期關於動物的文物藝術品,不僅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從側面詮釋了人類歷史與文化。

正如“博物君”張辰亮所推薦的:“展示博物館藏品的書很多,但是這套書用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思路。他把大英博物館裏的海量藏品重新分類。同一個動物題材的文物分到一起,戴帽子的人分在一起,坐着的人分在一起。這樣的話,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不同歷史階段的文物就以這種奇妙的形式展現出來。乾隆皇帝的精美坐像旁邊,就是剛果國王的樸素的雕像。古埃及的魚形玻璃瓶兒下一頁就是日本匠人雕刻的精美鐵鯉魚。文明之間的界限一被打破,就很容易發現世界各大文明之間的共性和傳承。你不會以我們國家怎麼樣、他們國家怎麼樣來看待文明,而是站在上帝的視角,欣賞整個人類的文明。”
這些藝術品運用多變的形狀、豐富的色盤、不同的質地,以及點、線、面、體等造型手段,在二維平面或三維空間中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形象。在無形中潛移默化,提升藝術修養與審美。在今天,無論對產品的商業價值,還是個人的社交來說,審美都是重要的競爭力。

大英博物館最新作品分別從不同角度來講述人類社會,《大英博物館人類簡史》從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即人與人的互動,來進行講述;《大英博物館動物簡史》是從人類視角下的各類動物,即人與動物的互動,來進行講述。它們綜合起來,涵蓋古今,使人類社會更加立體化、具象化,全景式描述了人類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是藝術化的人類社會百科全書。

無論是遠古的狩獵,馴化家畜,還是日常生活中需要高度專注的手工勞工,經濟活動都是人類社會的基礎和必需。人類社會的存在需要一定的秩序,統治與戰爭不可避免,它們構成了人類的政治。人類的認知能力是逐漸發展的,越往前,自然與超自然的界限就越模糊,人類相信有尚不能理解的超自然力量,於是用虛構和想象,誕生了各種神獸、神話、宗教,人類還對一無所知的死亡,以及善惡等這些問題的思考,所形成的看法,它們一起就構成了人類社會的文化。

同時,經濟、政治和文化又是相互交融的。比如狩獵,它從人類一開始的爲生存而戰的職業,逐漸演變爲社會精英階層的休閒娛樂活動,而成爲一種文化。甚至在都鐸王朝時期,追逐獵物是君王和貴族專屬的活動,是權力的象徵,如果平民狩獵,則會受到死刑處罰,它又具有了政治屬性。
對同一主題,內容上的橫向比較結構,有助於我們形成用全球化的視野、整體的眼光來看問題,也能體會人類共有的情感和價值。比如紀念先祖,1000年前智利人用艾摩石像;非洲尼日利亞卡拉巴里族有紀念祖先的木刻屏風;中國有清明祭祖的傳統;墨西哥還有專門的“亡靈節”,他們相信那些死去的親人會回到人間來享受世間的歡樂;大洋洲的所羅門羣島,認爲祖先去世後,還可以化爲鯊魚來保護後代在海上的安全。
現實中的自然、歷史和社會,三者從來都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傳統的學校教育,以學科來劃分,相互隔離,往往使我們喪失了綜合思考的能力,看待事務缺乏一個整體和全面的視角。《大英博物館人類簡史》和《大英博物館動物簡史》對同一主題,從多方面運用綜合知識,用簡潔的文字,去分析和解釋。

比如說在古埃及的很多墓穴壁畫中,發現一處細節——羅非魚。文中給出瞭解釋,古埃及人注意到,雌性羅非魚爲了保護後代,會將魚卵含在口中孵化,有時甚至幼魚也會受到這種庇護。古埃及人把羅非魚這種能吐出活魚的能力看作重生的象徵。羅非魚的這種能力是自然屬性,而人類嚮往死後復生卻是一種社會屬性,但它們在歷史中又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大英博物館的這些藝術品,表達的不只是藝術,更是300萬年來人類生活的真相,生活總是要面對的一些挫折與憂傷。它們啓發了我們的共情能力與同理心,提高抗壓能力,增強生命的韌性。比如5000年前在軍旗的一面描繪的是戰爭場景,許多蘇美爾人佩着刀劍,併發明瞭戰車,戰馬下躺着死人,充滿了戰爭的血腥。而軍旗的另一面是宴會的和平場景,有樂師,有歌手。
人類社會從最初就是在血腥的戰爭與和平中交替前行,衝突與協作共存;美好的愛情令人嚮往,但它也會摻雜着欺騙和背叛,還有可能永失我愛。辛苦專注的工作才能讓一家人過上幸福的生活;成人的世界充滿掩飾與僞裝,統治者更是用神話來包裝自己;人們對來世一無所知,卻也滿懷期待;野生動物們成爲家畜、役畜後,仍然面臨着悲慘的命運;瘟疫與人類總是如影相隨。

人類持續的探索,對自身以前的生活有了不斷的瞭解,對文化現象也有了解釋。像從古至今最常出現的獻祭主題之一是人對公牛的祭宰。儘管早在一萬年前就被人類馴化,但公牛似乎被廣泛視作典型的黑暗象徵。回望人類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公牛代表着馴養和野生的分水嶺,而人類也正是跨越了這道界線進化而來。宰殺公牛也象徵着人類戰勝野蠻。

密特拉神和公牛的故事源於波斯,在羅馬帝國廣爲流傳。在密特拉神殺死公牛的同時,刺出的鮮血使生命和光重生。無論是對自然,還是對人類社會,所有的疑問的並沒有打開,總還有許多未知等待着去探索。
哪怕在已發現的文物中,仍然有許多未解之迷。像烏爾軍旗,還有廣爲流傳的綠松石雙頭蛇,目前對它們的用途,仍尚未可知。冰河時期的投矛器也會激發我們的好奇心,看看它到底是怎麼使用的。這套書每件藝術品的背後,都有着深厚的歷史背景,可以順着書中簡潔的說明文字線索,再去挖掘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