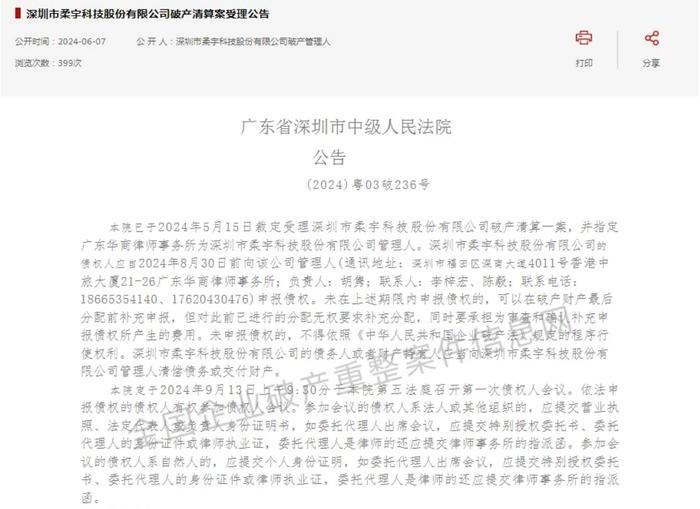張維迎在黑馬大賽和周鴻禕討論: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

來源丨人文學會(ID:HES1929) 作者丨張維迎
【編者注】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曾有一次給黑馬會研修班的學員講課,當時,學員們在做一個商業計劃競賽,他就坐下來聽。奇虎360的周鴻禕正在對一個年輕創業者的商業計劃書做點評,他聽到的基本上是否定態度,說這個想法不可行。等他上臺後就對小夥子說:“周鴻禕說你不行,不等於你真的不行,因爲當初他做企業的時候,別人也說他不行,說他不行的人當時的名氣比他現在的名氣還大!”
用周鴻禕自己的話說:自我創業以來,所做的每個決策都不被別人看好。
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
張維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刊於《管理視野》第20-22期
關於什麼是企業家精神,人們已經談了很多,諸如冒險精神,好奇心,創新,自信,果斷,偏執,有擔當,不循規蹈矩,英雄主義,百折不撓,等等。這些描述企業家精神的詞彙,我們都已耳熟能詳。
研究企業家三十五年,我最近的體會是,要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麼,必須理解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在這篇文章裏,我將集中談談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我從案例出發,通過分析,引出一些我認爲具有普遍性的結論。我講的每個案例,都具有典型性。
01
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
保羅·歐德寧(Paul Otellini, 1950-2017)是英特爾公司第五任CEO,我在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期間,他曾是我的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
英特爾公司的前三任CEO都是公司的創始人,可以說是真正的企業家,而且三人性格互補,珠聯璧合,把英特爾做成計算機和IT行業的“發動機”。其中羅伯特·諾伊斯還是集成電路的發明人之一,戈登·摩爾是“摩爾定律”的提出者。
在諾伊斯時代(1968-1975),英特爾生產RAM和DRAM,研發出微處理器。在摩爾時代(1975-1987),英特爾仍然是DRAM的專業製造商,但面對日本廠商的競爭,英特爾迅速失去了市場份額,1984年市場佔有率甚至一度降低到1.3%。此時,公司開始將重心轉到微處理器,並決定退出DRAM業務。在安德魯·葛洛夫時代(1987-1998),英特爾集中於PC處理器業務,使得英特爾取得巨大的發展,英特爾和微軟共同成爲PC業界當之無愧的統治者。但公司的經營戰略開始顯得僵化。
安德魯·葛洛夫退休的時候,把克瑞格·貝瑞特提拔爲CEO。貝瑞特原來是葛洛夫的得力助手,一個典型的職業經理人,長期擔任公司COO,因而被稱爲“主內先生”(Mr. Inside)。貝瑞特1998年上任的時候,互聯網和手機開始普及,貝瑞特開始大規模收購其他公司,試圖轉型爲手機和互聯網公司。但以失敗告終,貝瑞特於2005年辭職。

本文作者與保羅·歐德寧2008年的合影
接替貝瑞特的保羅·歐德寧也是一位“主內先生”,從COO升任CEO. 歐德寧主政期間,英特爾業績斐然,營收創紀錄,從388億美元增長到540億美元。但出人意料的是,2012年11月19日,歐德寧宣佈第二年5月辭去CEO職務,當時他只有62歲,遠不到英特爾65歲的正常退休年齡。而且,歐德寧是在尚未確定新任CEO人選的情況下宣佈退位的,這在英特爾歷史上還是首次。
保羅·歐德寧的突然辭職,主要原因是自己在應對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業務時決策失誤,被認爲是“英特爾史無前例的誤判”。在接受《大西洋月刊》採訪時,歐德寧承認在他擔任CEO期間,曾親手扼殺了成爲第一代iPhone處理器供應商的機會。
故事是這樣的:蘋果公司在2007年和2010年先後推出了iPhone和iPad產品。蘋果公司曾考慮將第一代iPhone處理器的生產委託給英特爾公司。喬布斯找到歐德寧,開出的價格是每枚處理器10美元,除此之外不給一分錢。
於是,歐德寧組織了一個團隊,進行了一系列的測算:根據這個開價,要確保多少產量才能盈利,而這取決於iPhone的銷量。算來算去,英特爾的團隊認爲,爲iPhone開發處理器需要鉅額資金投入,每枚才賣10美元,肯定是筆賠本的買賣,不值得做。
歐德寧接受了下屬的意見,回絕了蘋果提出的交易。蘋果因此轉向三星電子。三星由此迅速壯大,僅用了三年時間,在晶圓代工行業的排名就從第10位躍升到第3位,並開發出自己的智能手機Galaxy,成爲蘋果的競爭對手。蘋果公司後來因知識產權問題控告三星,這是後話。
事實證明,英特爾當時對成本和銷售的預測是錯誤的。iPhone手機生產量竟達到英特爾團隊所預期的百倍之多。這讓英特爾後悔莫及![1]
我想用這個故事說明的是: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
經濟學和管理學中講的決策,是科學決策,不是企業家決策。
科學決策是基於數據和計算。給定數據,最優選擇是唯一的。
企業家決策是基於直覺、想象力和判斷。同樣的數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力和判斷,選擇會很不同。[2]
因此,科學決策能形成共識,有標準答案;企業家決策是非共識的,沒有標準答案。換言之,有標準答案的決策都不是企業家決策。
我們可以用考試或課程作業爲例說明這一點。一個考題,考卷上可能寫出A、B、C、D四個可能的答案供你選擇,但正確的答案是唯一的。設想考完試後,你問周圍其他同學是如何選擇的,如果大部分同學選擇了A,而你實際上選擇了C,你心裏一定發毛,因爲十有八九你錯了。
但對企業家決策而言,多數人認爲正確的很可能恰恰是錯誤的。所以,我們看到,那些傑出的企業家做出的最重要的決策,最初常常是多數人不認同的,甚至被認爲是荒謬的。多數人認同的決策,只能是科學決策,一定不是企業家決策。當然,我們也不能反過來說,多數人反對的決策一定是正確的決策。我的意思是說,企業家不會按照多數人的意見做決策。當然,他一個人的意見,可能對也可能錯,要由市場事後檢驗,事前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多數人的意見不能成爲判斷的標準。
我曾有一個學生,畢業後到一個跨國公司當僱員,薪水很高,有一天找到我,說自己想下海創辦企業,當企業家,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我沒有辦法說行還是不行,我就問你一個問題:“你爸你媽什麼意見?”他說:“父母堅決反對!”我說:“那你就不妨試一試!”在我看來,連父母都同意的決策,不大可能是一個企業家決策。這個學生果真下海了,至目前爲止,企業做得還不錯。
我曾有一次給黑馬會研修班的學員講課,我到達的時候,他們在做一個商業計劃競賽,我就坐下來聽。奇虎360的周鴻禕正在對一個年輕創業者的商業計劃書做點評,我聽到的基本上是否定態度,說這個想法不可行。我上臺後就對小夥子說:周鴻禕說你不行,不等於你真的不行,因爲當初他做企業的時候,別人也說他不行,說他不行的人當時的名氣比他現在的名氣還大!用周鴻禕自己的話說:自我創業以來,所做的每個決策都不被別人看好。
數據和計算之所以在企業家決策中不起關鍵作用,是因爲企業家決策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所謂不確定性,是指企業家決策時面對的未來事件是主觀的,未知的,獨一無二的,沒有統計樣本,沒有概率分佈,因而無客觀數據可用。[3]進一步,未來的不確定性受現在和未來選擇的影響,而不是由過去發生的事情預先決定的。同樣的行動帶來無數可能的後果。因此,不僅如同哈耶克講的,市場是一個發現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4],一個不斷獲取信息的過程,不是給定數據下解方程;市場更是一個創造過程(creative process)[5],是人類想象力和創造力潛能的運用過程。企業家不是給定數據下做決策,而是發現還沒有被發現的數據,想象可能的未來,創造本來不存在的東西。用郵政馬車的數據預測汽車是沒有用的,風帆木船的數據也不可能告訴我們鐵船是否可行,因爲汽車和鐵船很大程度上是卡爾·本茨和約翰·威爾金森這樣的企業家想象出來的。經濟學家把“不確定性”等價於“風險”,進而把“風險”等價於統計學上的方差,是嚴重誤導的。
正如德國學者雷納·齊特爾曼指出的:“企業家通常不會按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的理性假設行事。他們通常不把自己的決策建立在概率計算上,也不傾向於遵循複雜的理論假設,而更憑直覺行事,主要靠感覺。”[6]
我並不否定數據和科學決策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要性。事實上,在我看來,成熟企業90%以上的決策屬於日常管理決策,可以藉助管理學院學到的科學決策方法做出。但決定企業命運的是不同於管理決策的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比如,是否在一個特定的地方開一個飯館是企業家決策,而一個飯館每天購進多少食料、僱傭多少廚師和服務人員,屬於管理決策。管理決策可以藉助於數據和計算做出,企業家決策更多依賴於直覺、想象力和判斷,不是數據和計算。在大的科層公司,位於頂層領導崗位的人做的決策,主要是企業家決策,而位於中下層管理崗位的人做的決策,主要管理決策。因此,對高層領導而言,最重要的是直覺、想象力和判斷,而對中下層管理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數據和計算。
我相信,隨着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管理決策可以由計算機自動做出,但計算機永遠代替不了企業家決策,儘管企業家決策的範圍會隨着技術和知識的積累發生變化。企業家做的是無法用數據和計算替代的決策,任何可以用數據制定的決策都不再屬於企業家決策,只是普通的管理決策。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現實中的企業家通常身兼數職,既是企業家,又是管理者,因而除了企業家決策,還要做不少管理決策。但企業家首先必須判斷哪些是企業家決策,哪些是管理決策。
保羅·歐德寧的失誤在於,他把一個企業家決策誤當作管理決策。喬布斯推出iPhone是一個典型的企業家決策,相應地,是否給iPhone提供處理器也是一個典型的企業家決策,需要的是直覺、想象力和判斷,而不是公司財務人員和營銷人員的計算。三星電子公司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蘋果公司的委託,正是基於三星董事長李健熙的企業家直覺。
歐德寧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到:“當時直覺告訴我,應該接受蘋果提出的交易。”但這可能有點“事後諸葛亮”的味道。事實是,他相信了數據,沒有按照自己的直覺行事。這就是管理者和企業家的區別。
02
企業家決策不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而是改變約束條件本身
杜廈是我的一位老朋友,1982年2月西安舉辦的“全國數量經濟學會議”上,我們倆相識,當時他是南京大學計量經濟學研究生,即將畢業,我是西北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生,剛開始就讀。1984年9月,我們又在莫干山會議上相見,他當時已是南開大學副教授。莫干山會議之後,他的名氣越來越大,組織了1985年春天在天津召開的第二屆“中青年經濟改革討論會”,參與創辦了《中青年經濟論壇》學術期刊,很快就成爲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的座上客,指點天津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
1985年年底,杜廈參加了國家教委組織的“國務院赴美留學工作組”,在美國訪問了45天,與當時大名鼎鼎的曲嘯同臺給留學生巡迴演講,深受好評。回國後,他又應邀去多個國內大學演講。但他在國內大學的演講內容讓國家教委負責人感到不爽,在隨後申請去英國訪問時,辦手續“卡殼了”。一氣之下,他決定下海經商。

杜廈
1987年,杜廈來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靠諮詢和組織“李寧告別體壇晚會”,到1989年初,他的“克瑞思公司”已積累了300萬元人民幣的資金。此時,他決定投入200萬元在香港市場做外匯交易,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淨賺200萬港幣。這樣的旗開得勝讓他信心爆棚,立志做一個金融家,成爲中國的索羅斯。
靠着朋友的幫助,他從銀行融到了資金,外匯交易越做越大。他賭日元升值,信心滿滿。但很不幸,他沒有預料到日本政壇開始跌宕起伏,首相像走馬燈似的換了一個又一個,日元對美元持續走低,不到三月時間,就從每美元145.69日元貶值到158.46日元。不得不平倉之後,他發現自己不僅把原來賺的400萬賠光了,而且欠下1400萬港幣的債。真是黃粱美夢一場空。
杜廈陷入絕望。他曾有過從深圳國貿大廈50層的天台上跳下去的念頭,但沒有勇氣付諸行動。他必須在10個月的時間內賺到足夠的錢,把所欠的1400萬債務還清。債是欠銀行和朋友的,銀行的錢也是託朋友關係借來的,如果錢還不上,不僅會得罪和連累朋友,還可能有牢獄之災。
怎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賺到這麼大一筆錢呢?
1989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他躺在牀上無聊地看電視,突然,一個鏡頭映入他的眼簾: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緊緊地把手握在一起,宣佈中蘇關係正常化。這讓杜廈有了個奇思妙想:中蘇關係正常化首先會從文化交流開始,如果我能把蘇聯馬戲團引到中國演出,也許能賺一筆大錢,還清1400萬欠債。1957年,在九歲的時候,他曾在北京看過蘇聯國家大馬戲團的演出,精彩絕倫,讓他終身難忘。當時在演出現場觀看演出的,除了他,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很多人。
那個時候,中外文化交流還是政府間的事務,不是杜廈這樣一個個體戶可以輕易染指的。但他還是爲自己的奇思妙想走火入魔,躍躍欲試。
1990年正月初二,他便坐火車來到北京。他的目的是向文化部正式提出邀請“蘇聯國家大馬戲團”訪華巡迴演出的建議,並且由他的企業承辦。託了多次關係,他終於見到了文化部外聯局局長遊琪女士。他告訴遊局長,在中蘇關係迅速恢復的過程中,由他來承辦這件事,既給文化部提供了一個撥得頭彩的表現機會,又開創了對外文化交流的新形式,還給文化部節約了大量預算經費,因而對文化部來說,是一個一舉三得的好事情。
他說的很讓遊局長動心。但局長還是有些猶豫不決:小杜啊,你如果能做成這件事,當然是件大好事,我們會全力支持。但萬一你賠了錢,半路撂挑子走了,還得文化部出面把項目接過來,到時候,花錢不說,免不了我在文化部內部丟人現眼。你有什麼辦法讓我們放心的保障措施嗎?
杜廈明白局長的意思,脫口而出:如果文化部能確定由我們來承辦這次商業巡演,我可以給文化部一份50萬美元的不可撤銷的擔保函。有了這份擔保函,您本人和文化部沒有任何風險。
一週後,遊局長電話告訴杜廈,文化部部長高佔祥批准了邀請蘇聯國家大馬戲團訪華巡迴演出的建議,並同意由他的深圳克瑞思公司全權承辦,自負盈虧。前提是,他必須交來50萬美元的擔保函。
但哪裏去搞50萬美元的擔保函?杜廈現在不僅身無分文,而且還欠着一屁股債,不可能有任何銀行願意給他開具這樣的擔保函。他想到,唯一的希望是求助於他的隔壁鄰居、中國“中國租賃總公司”的總經理李西元。李曾從他手中買過一套房子,兩人有些交往。
回到深圳後,杜廈登門拜訪了李西元,說:我要把蘇聯國家大馬戲團請到中國巡迴演出100場,可以把最顯著的廣告位置給你們公司。李問:那需要多少廣告費?杜廈說,你不需要出廣告費,只要給我開具50萬美元的不可撤銷的擔保函就可以了。李考慮一會之後,答應了。交談中杜廈得知,李也曾在1957年觀看過蘇聯國家大馬戲團在北京的演出,印象深刻。1988年,李曾受邀參加過深圳體育場舉辦的“李寧體壇告別演出”,這場演出是杜廈策劃組織的,因而李對他的組織能力有些基本的信任。
有了50萬美元的擔保函,文化部這方面算搞定了!
但馬戲團又在哪了呢?自1957年之後,杜廈再沒有觀看過蘇聯馬戲團的演出,也不曾去過蘇聯。要請到蘇聯馬戲團,必須去蘇聯。但當時的蘇聯仍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可能接待一箇中國個體戶的來訪。只有文化部出面才能解決問題。文化部說:我們可以組織一個赴蘇談判代表團,但外匯經費要你自己解決!杜廈只好再次找到李西元,說:文化部要組織代表團去蘇聯,你是代表團成員,但對不起,你得承擔代表團成員出國訪問的經費。李很高興作爲文化部代表團成員去蘇聯,經費數額也不算大,就同意了。
到莫斯科後,談判成了一場心理戰。全蘇聯加盟共和國一級的馬戲團,大大小小有80多個,但出國演出由蘇聯文化部對外演出總公司統一安排組合,統稱“蘇聯國家大馬戲團”。蘇聯對外演出總公司總經理馬克西莫夫親自出面談判,中方的談判代表是杜廈,其他人沒有發言權。談判的中心是演出報酬問題。馬克西莫夫是一個強硬的談判對手,要價是每場演出5千美元,一分也不能少。杜廈的出價是1萬人民幣,一分也不能多。第一次沒有談成。在代表團即將飛回中國的當天上午,對方把價格降到3千5百美元,杜廈仍然堅持1萬人民幣。還是沒有談成。
在回國的飛機上,除了杜廈本人,其他六個成員都垂頭喪氣。文化部官員抱怨說:小杜啊,即使我們文化部邀請,5千美元也拿不下來,人家已經降到了3千5百美元,你還不答應,我們這一趟不是白跑了嗎?杜廈不吭聲,心裏想的是,他們沒有演出,連工資都發不出,一定會接受他的報價。所以在離開莫斯科前,他給對方留下話:給你們一週時間考慮,如果接受1萬人民幣報價,就發傳真通知我們吧。
但對方真的會自己的報價嗎?杜廈心裏也沒底。
回到北京後,杜廈一直忐忑不安,每天去文化部電傳室等傳真,從早八點到下午五點,一天一天過去了,一直沒有消息。到了星期五,約定時間的最後一天,下午五點過了,下班時間到了,對方仍然沒有回覆。他徹底絕望了,垂頭喪氣地回到了自己的酒店。
喫過簡單的晚飯,杜廈躺在牀上,無精打采。突然,他想到,莫斯科與北京有5個小時的時差,對方還沒有下班,也許還有希望。他又匆匆忙忙趕回文化部電傳室。
北京時間下午9:45,莫斯科時間下午4:45,傳真機響了。對方同意了1萬人民幣的報價,杜廈激動得幾乎落淚。
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後,由83名英俊漂亮的男女演員、12頭猛獸和10頭大型動物組成的“蘇聯國家大馬戲團”,浩浩蕩蕩從滿洲里口岸進入中國。大馬戲團在中國曆時三個月,巡遊7個城市,共演出97場。最後一場演出安排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座無虛席。爲了中蘇友好關係,江澤民、李鵬、李瑞環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出席觀看了演出。杜廈自豪地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門票也是中央辦公廳出錢買的。事實上,從始到終97場演出,他沒有送過一張票。這倒不是他捨不得,而是他的營銷策略。
演出結束後,杜廈一算,扣除所有成本,淨賺1500多萬人民幣。此時,離他償還債務的最後日期不到一個月。他飛回深圳,還清了所有債務,然後帶着剩餘的幾十萬元回到天津,重新開始自己的創業歷程。[7]
我想用這個故事說的是:企業家決策不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而是改變約束條件本身。
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所謂理性人決策,就是給定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目標函數。就企業而言,這裏的約束條件包括資源給定、技術給定、消費者偏好給定、制度和政策給定,目標函數就是利潤。給定約束條件,決策就是一個數學上的最優化問題。一個企業家能實現多大的利潤目標,完全取決於約束條件,與企業家的能力無關。而約束條件完全是外生的,企業家無能力改變。因此,企業家就是一個計算程序。
這樣的理性人決策模式與真實世界的企業家決策相距甚遠。對真實世界的企業家來說,約束條件從來不是給定的,而是可以改變的。不僅資源、技術和消費者偏好不是給定的,甚至遊戲規則也是可以改變的。當然,不是所有的約束條件都可以改變。但企業家絕不會把所有約束條件當作給定的、不可改變的。事實上,人與人之間企業家能力的差異,很大程度上表現爲改變約束條件的能力差異。沒有能力改變約束條件的人,不可能成爲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所謂創新,本質上講,就是改變約束條件,把看起來不可能的事情做成。
杜廈的成功,就在於他改變了自己面臨的約束條件,而不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做選擇。中外文化交流本來是政府間的事情,他把它變成了私人可以從事的商業活動。這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蘇聯馬戲團是蘇聯的國家資產,他把它請到中國巡迴演出,變成自己賺錢的工具。這是資源的改變。實際上,他還改變了中國消費者的偏好。中國觀衆本來沒有看蘇聯馬戲團演出的“需求”,是他請來了蘇聯馬戲團,並採取獨特的營銷策略推廣,才讓他們大飽眼福。
我們可以用“巧婦難爲無米之炊”這句流行的話解釋企業家與常人的不同。對常人來說,米是做飯的先決條件,你要讓他做飯,他會問:米在哪了?沒有米,他會兩手一攤,一副無能爲力、愛莫能助的樣子。但企業家並不是有了“米”才“做飯”。如果他認爲有人想喫飯,賣飯能賺錢,他就想方設法找到米。即使沒有現成的米,他也能說服別人種稻子,生產出米來。杜廈不是有了馬戲團才組織巡迴演出,而是想象巡迴演出能賺錢,纔去北京找文化部,去莫斯科聯繫馬戲團。他把常人看來根本不可能的事做成。巧婦不爲無米所難!
想改變約束條件的人,一定對自己的想法充滿足夠的自信。悲觀主義者不可能有改變現狀的衝動。所以,企業家比常人更樂觀,相信“夢想”一定能夠實現,“假設”一定能夠變成現實。
事實上,企業家常常是過分樂觀。比如,一項對針對2994名已經創業的美國企業家的調查顯示,81%的受訪者認爲自己個人的成功率在70%以上,33%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失敗率爲0,雖然當時美國創業企業2/3都在4年內面臨經營不善的問題。[8]
正是過分樂觀,使得企業家做許多從理性計算來看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如重大創新)。VC和PE投資人告訴我們,投資100個項目,有5個成功就不錯了。但做一件事如果只有5%的可能性成功,我相信絕大部分情況下是沒有人願意去做的。企業家對成功的信心遠大於事後的統計概率。我多次聽到過成功的企業家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當初知道這麼難,根本就不會開始。低估困難在企業家中是普遍現象,也是企業家之所以成爲企業家的重要原因。
進一步,企業家要改變的約束條件通常不是一個,而是多個。並且,多個約束條件又是相互依賴的,不是獨立的。要有A,先得有B;要有B,先得有C;而要有C,又先得有A。這就類似用三根木棍相互支撐成一個三腳架,必須同時立起來纔行。因此,企業家必須具有高超的操作他人信念和行爲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現實扭曲場”(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一個流傳的笑話有助於理解這一點:一個名叫約翰遜的先生找到世界銀行的行長,說:你該提拔我兒子當副行長了。行長問:爲什麼?約翰遜回答:他馬上就是比爾·蓋茨的女婿了。約翰遜又找到比爾·蓋茨,說:你女兒應該嫁給我兒子,因爲他馬上就當世界銀行副行長了。行長和比爾·蓋茨都相信了約翰遜的話,小約翰遜不僅當上世界銀行副行長,而且娶到了比爾·蓋茨的女兒。事後看,他講都是事實,他對誰也沒有說謊!
但不確定性意味着企業家能力再高,也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外部因素。因此,企業家改變約束條件的行爲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成功了,人們說他是英雄;失敗了,他就是一個十足的“騙子”!杜廈如果不能在10個月的時間賺到足夠的錢,把1400萬債務還清,借錢給他的朋友和銀行都會認爲他是一個騙子;如果不能從中國租賃總公司拿到50萬美元的擔保函,文化部官員會認爲他是騙子;如果不能邀請到蘇聯國家大馬戲團來華演出,文化部官員和中國租賃總公司的李總都會認爲他是騙子;即使蘇聯國家大馬戲團來華演出了,但如果沒有賺到足夠的錢,還不清1400萬欠債,他還是會被認爲是一個騙子!幸運的是,他的三根木棍同時立起來了。當然,他的成功靠的主要不是運氣,而是他的企業家精神。
與騙子不同的是,企業家在做出許諾的時候,是想做成事,相信自己會成功,因而所有的許諾都能兌現,而騙子一開始就是想騙取他人的財物,也知道事後一定會露馬腳。騙子只要當場不露馬腳就算成功了,而企業家要永遠不露馬腳纔算成功!
03
企業家有夢想,賺錢不是唯一目標

塞勒斯·韋斯特·菲爾德
塞勒斯·韋斯特·菲爾德(Cyrus West Field,1819-1892)是19世紀美國一位傑出的企業家、金融家,因鋪設第一條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而名垂青史。
菲爾德是一位傳教士的兒子,靠經營造紙業發了大財,在風華正茂的年紀,已腰纏萬貫。34歲的時候,因身體原因,他賣掉了自己的企業,休閒在家,過起隱居生活。但對他這樣的人來說,長期無所事事未免太空虛了一點。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遇到了加拿大來的英國企業家、工程師弗雷德裏克·牛頓·吉斯伯恩納(Frederick Newton Gisborne)。吉斯伯恩納正在鋪設一條從紐約到美洲最東邊的紐芬蘭的海底電纜,以便能提前數日獲得有關船舶到達的信息,但工程做到一半時,資金枯竭,於是只好來紐約尋找金融家的支持。
菲爾德對電一竅不通,也從未見過什麼電纜。但他還是被吉斯伯恩納的項目所吸引,決定投身於這項事業。但他的想法比吉斯伯恩納大得多。他問吉斯伯恩納:爲什麼只鋪設到紐芬蘭,不繼續鋪設到愛爾蘭,把美洲和歐洲連接起來呢?
這是一個很瘋狂的想法。儘管英國與法國之間的海底電纜已於1951年11月鋪設成功,不幾年功夫,英國與它周邊的愛爾蘭、丹麥和瑞典,科西嘉和歐洲大陸之間,都建立了電報聯繫,但這些海底電纜長度都不超過數十公里,與橫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不可同日而語,二者之間的區別如同小平房與摩天大樓的區別。
從紐芬蘭到愛爾蘭的海域長達兩千多海里。大西洋海底有多深?海水的壓力有多大?電纜能否承受這樣的壓力?大洋深處的磁場是否會導致電流失散?這些問題當時都不清楚。雖然“古塔膠”已經發明幾年了,但當時還沒有絕對可靠的絕緣材料,也沒有準確的測量儀器。即使這些技術問題解決了,由銅和鐵製成的電纜重達9千多噸,從哪裏弄到可以運載電纜的巨型船隻?當時,最大船隻的載重量只有5千噸。又從哪裏弄到這樣大功率的發電機,把電流不間斷地輸送過用輪船橫渡也得兩三星期的距離?

(大西洋海域:從加拿大紐芬蘭到歐洲愛爾蘭)
因此,當菲爾德提出他的想法的時候,學者們都反對,認爲“這絕對不可能”。甚至電報的發明人莫爾斯也覺得這個計劃是不可思議的冒險。西部聯盟(Western Union)是當時美國最大的電報公司,對菲爾德的計劃不屑一顧。他們計劃鋪設從阿拉斯加經過白令海峽到達西伯利亞的電纜,然後再經陸地電線槓上的電報線把美洲和歐洲連接起來。畢竟,白令海峽最窄處不過53海里,鋪設這麼短距離海底電纜的技術已經成熟,也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借鑑。
但菲爾德很爲自己的想法着迷,沒有被困難所嚇倒。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所有財產貢獻出來,創辦了大西洋電報公司(Atlantic Telegraph Company)。他用自己的執着和三寸不爛之舌說服美國和英國一些有錢人加盟,他的股東名單裏有英國著名小說家威廉姆·薩克雷(《名利場》作者)和著名詩人拜倫的遺孀安妮·拜倫等人。這些人投資於他,僅僅是出於道義上的熱忱,完全沒有賺錢的目的。菲爾德與所有的專家建立了聯繫,尋求他們技術上的支持。在幾年時間裏,他橫渡大西洋往返於兩大洲之間31次。他說服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各租給他一艘戰艦,用於運載總重量9千多噸的電纜。這是當時所能得到的最大船隻。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1857年8月5日,菲爾德親自坐鎮,“尼亞加拉號”戰艦載滿一半的電纜和上百名水手從愛爾蘭瓦倫西亞海港出發,開始了鋪設大西洋海底電纜的壯舉。“阿伽門農號”戰艦載着另一半電纜使往大西洋中心,準備接着鋪設下一半。出發前,成千上萬的人湧到港口,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英國政府派來了代表,致了賀詞。一位牧師前來爲它祈禱。
最初的幾天,一切順利,到第六天的時候,已經鋪設了335海里,電報訊號仍然清晰。但第六天晚上,菲爾德正準備入睡的時候,那熟悉的嘎嘎絞盤聲突然停止了。電纜從放纜車上斷裂了。要找到那扯斷的一頭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鋪設失敗了!
經過近一年的等待和準備之後,菲爾德準備第二次鋪設。1858年6月,兩艘戰艦計劃分別從兩岸使往大西洋中部,然後同時向兩個不同的方向鋪設。但“阿伽門農號”戰艦出發不久,就遭遇到特大暴風雨的襲擊,儘管按計劃到達了預定地點,但所載電纜已被嚴重損毀,勉勉強強鋪設200海里之後,不得灰溜溜地回家。
第二次鋪設也失敗了。
兩次失敗已消耗掉資本金的一半,可是什麼結果都沒有,實在令人沮喪。股東們不幹了,董事長主張將剩下的電纜賣掉,把損失減少到最低;副董事長附和,並且書面提出辭職,以此表示他不願再同這件荒唐的事有任何瓜葛。
但菲爾德堅定的信念並沒有因此動搖。他解釋說,經過這樣的考驗,證明電纜本身的性能非常好,船上的電纜還足夠進行一次新的實驗,我們什麼也沒有損失。他強烈的意志戰勝了股東們的猶疑不決。在他的堅持下,第三次鋪設啓動了。
1858年7月28日,兩艘鋪設船在大西洋中間預定的地點會合,然後同時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出發。到8月5日,向西的“尼亞加拉”號報告說,它在鋪完1030海里後,現在已到了紐芬蘭的特里尼蒂海灣,並已看到美洲的海岸;向東行使的“阿伽門農”號也報告說,在鋪設完一千多海里之後,它看到了愛爾蘭海岸。
成功了!8月16日,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和美國總統布坎南互致電報表示祝賀。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能把一個信息瞬時飛越大西洋,新世界和舊世界連接起來了!全球轟動了!所有人都興奮了!8月17日,紐約和倫敦的報紙用特大號的醒目標題歡呼這次勝利。8月31日,紐約全城萬人空巷,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菲爾德成爲大英雄,坐在遊行隊伍的第一輛馬車上,沉浸在“哥倫布第二”的讚美聲中。美國總統也參加了慶典,但只能坐着第三輛馬車上。


但在遊行隊伍出發前,菲爾德已經得到消息:電纜突然不工作了。9月1日之後,不再有電報信號傳來!後來證明,失敗的原因是,維爾德曼·維特豪斯(Wildman Whitehouse),這個菲爾德僱傭的首席工程師,其實是個業餘工程師,本職是外科醫生,當電流信號弱時,他就不斷加大電壓,結果把電纜燒壞了。
不幾天,這個壞消息不脛而走。驟然之間,輿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菲爾德成了罪人,人們說他是個大騙子,“欺騙了一個城市、一個國家,騙了全世界。”有傳言說,越過大西洋的電報從來就沒有傳來過,什麼英國女王的電報!完全是菲爾德自己捏造的。還有人說他早就知道電報失靈,但爲了自己的私利而隱瞞事實,並利用這段時間把自己的股票高價脫手。
塞勒斯·韋斯特·菲爾德,這個昨天還被當作民族英雄的人,現在卻不得不像一個罪犯一樣躲避自己昔日的朋友和崇拜者。
但菲爾德不是一個容易被失敗擊垮的人。在揹着沉重的十字架沉寂了六年之後,他又重新振作起來,再次獻身於自己的夢想。
當時美國處於內戰期,不可能籌集到資金,也沒有人關心這件事。菲爾德來到英國,在曼徹斯特、倫敦、利物浦籌集到了60萬英鎊,獲得原來的經營權,兩天之內就買下了當時最大的船---“大東方號”(the Great Eastern),並且爲遠航進行了必要的準備。
大東方號是英國傑出的工程師伊桑巴德·布魯內爾建造的,耗資25萬英鎊,於1858年下水,原來計劃用於倫敦與悉尼之間的直航,但因爲貨源不足,只在倫敦和紐約之間航行三次,搞破產了三個企業家,此時正閒置待售,讓菲爾德撿了個大便宜,只花了區區2萬5千英鎊,建造成本的十分之一。大東方號喫水兩萬兩千噸,能負載全部電纜。
1865年7月23日,大東方號裝載着重達九千多噸新電纜,離開泰晤士河。
沒想到,第一次試驗又失敗了——在鋪到目的地以前兩天,電纜斷裂,損失60萬英鎊。
菲爾德想重整旗鼓,但融資非常困難,銀行不再願意提供貸款。幸運的是,蘇格蘭紡織企業家約翰·彭德爾爵士(Sir John Pender)看好這項事業,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抵押給銀行,貸到25萬英鎊,投資於菲爾德的事業,製造商才願意製造電纜。
1866年7月13日,大東方人號第二次出航,終獲成功!從大西洋彼岸傳來的電報信號十分清晰。1866年7月29日,維多利亞女王和約翰遜總統交換了正式的電報信息。更巧的是,數天後,原先那條失蹤的舊電纜也被找到了。這樣,兩條電纜終於把舊大陸和新大陸連成一個世界!電纜運營服務的第一天就賺了1000英鎊。菲爾德也洗刷了自己揹負的“騙子”名聲,再一次成爲大英雄![9]
投資人約翰·彭德爾也發了大財,隨後相繼創辦了32家海底電報公司。這32家公司後來合併成東方電報公司(the Eastern Telegraph Company),鋪設了連接歐、亞、非的大部分海底電報電纜,後又改名爲帝國和國際通訊公司,1934年更名爲Cable & Wireless。

(大東方號輪船在加拿大紐芬蘭弗德灣半島三一港灣,1866年)
我想用這個故事說明的是:企業家決策並不以利潤爲唯一目標;企業家有超越利潤的夢想。利潤與其說是企業家的追求的目的,不如說是企業家衡量自己成功與否和社會約束企業家行爲的指標。
把利潤最大化作爲企業的目標,這是主流經濟學的標準假設。在主流經濟學看來,任何偏離利潤最大化的行爲都是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導致的不可欲現象,會帶來效率損失,因而應該受到遏制。在許多情況下,這樣的假設對我們理解企業行爲和市場運行是有價值的。但這樣的假設也誤導對我們真實世界的理解。在真實世界裏,至少對那些傑出的企業家來說,賺錢並不是他們的惟一目標,更不是終結目標,即便他們是企業惟一的所有者。
熊彼特認爲,企業家真正追求的不是利潤,而是成功的事業。特別地,企業家受三個非金錢動機驅使:(1)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國;(2)征服對手,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3)對創造性的享受。[10]
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人雄心勃勃,想幹大事,想出人頭地。在傳統社會,雄心勃勃和想出人頭地的人只能通過征服別人的領土,掠奪別人的財產,奴役別人的生命,建立自己的王國,最後當上君主。他們使用的是強盜的邏輯。在市場經濟中,個人的權利有法律的保護,這樣的強盜邏輯不大行得通。雄心勃勃的人要出人頭地,最好的方式是當企業家,建立自己的商業王國,通過給客戶提供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戰勝競爭對手,把更多的資源納入自己的掌控範圍。
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阿里巴巴就是他創造的私人王國。看到數億客戶在使用自己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手下有數十萬員工,出行前呼後擁,國外訪問有總統、總理接見,大小聚會都是中心,不時在各種媒體曝光,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確實會有一種當國王的感覺。
王石的選擇也是一個典型。當初做萬科時候,他認識到,在中國的體制下,賺大錢和做大事不可兼得,他更看重做大事,而不是賺大錢,因而放棄了自己應得的鉅額股份,選擇做一個“職業經理人”。但他真正想做的不是“職業經理人”,而是建立一個商業帝國,當房地產業界的領袖。萬科是他實現夢想的載體,萬科的成功就是他自己的成功。他要向人們證明:我能,你不能!
對創造性的享受也是許多人企業家選擇做企業家的重要原因。企業家在不確定性下做事,總是充滿了挑戰,這種挑戰對喜歡創造性工作的人本身就是一種報酬。每戰勝一個困難,就似贏得一場勝利!
塞勒斯·韋斯特·菲爾德鋪設海底電纜,很難說是由於利潤的驅動。想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想當“哥倫布第二”,想用自己的行動改變世界,這纔是他的目的。在鋪設海底電纜的過程中,他總是激情澎湃,其樂無窮,所以才能屢敗屢戰,直至成功。如果不享受這個過程,他不可能堅持到最後。
正因爲企業家追求的不止是利潤,更多的是事業的成功、夢想的實現,企業家的許多決策沒有辦法用“預期利潤最大化”證成。按照標準的經濟學模型,如果一個項目投資1千萬,成功的概率是10%,那麼,只有當成功後的利潤達到1億以上時,企業家纔會投資。但在真實世界裏,企業家考慮的不僅是金錢報酬,還有非金錢報酬。企業家經常做“虧本”的事,如果這件事足夠驚天動地的話。正如熊彼特所說:“即使顯然不成比例的個人成功也有其作用,因爲取得這些成就的可能性發揮着一種更大的激勵作用,比能夠按照理性計算證明的成功概率乘以利潤量之積來標誌的那個激勵要大。對於那些沒有實現這種前景的企業家來說,這種前景也似乎是具有吸引力的‘報酬’。”[11]
一項對照性研究表明,職業經理人比企業家更在乎金錢報酬。他們選擇當職業經理人而不是自己創業,是因爲他們認爲,做職業經理人的報酬更高。[12]
還有大量實證研究表明,美國企業家收入的中位數要低於員工收入的中位數。只是由於極少數企業家獲得極高的收入,才使企業家羣體統計平均值上升到收入中位數以上。[13]
我並不否認利潤在企業家決策中的重要性。事實上,恰恰相反,我認爲,正是利潤這個制度性指標,保證了企業家的個人目標與社會利益的兼容。一方面,市場經濟中,利潤是企業家成功的標誌,企業家如果不賺錢,就很難證明自己成功,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王國。因此,即使不被利潤驅使,企業家也必須把賺錢當做實現自己人生目標的手段。普通人經常問的一個問題是:他已經賺了那些多錢,夠幾輩子花了,爲什麼還要賺錢?對此,簡單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對普通人來說,賺錢就是爲了養家餬口,但對企業家而言,賺錢是實現事業成功的手段。
另一方面,對社會而言,企業的收入如果不能大於成本,大部分情況下意味着企業家浪費了寶貴的社會資源,沒有爲社會創造增加值,應該被淘汰。因此,利潤就像整個社會抽打企業家的鞭子,驅趕其不斷努力;利潤也像一個籠子,把企業家的行爲約束在合理的範圍內。
傳統社會不乏像市場經濟中企業家這樣雄心勃勃的人。但平均而言,他們乾的壞事遠多於好事,有些人甚至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災難。究其原因,就是因爲他們不受利潤的約束,即使犯了錯誤,也可以繼續通過暴力獲得資源,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相比之下,市場經濟下,由於受利潤的約束,企業家不可能持續犯錯。
04
企業家不能完全聽命於投資人
李彥宏1991年北京大學本科畢業,獲信息管理學士學位,隨後前往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學習計算機科學,並獲碩士學位,之後八年,他在《華爾街日報》下屬的金融信息系統設計商道·瓊斯當過諮詢師,在搜信(Infoseek)做過高級工程師。在這些年裏,他發明了ESP技術和Go.com搜索引擎,被授予一項基於質量的網頁排序技術專利。基於自己的工作經驗,李彥宏甚至寫了一本名爲《硅谷商戰》的中文書。在這本書裏,他問自己創業是否太遲?他說服自己,不能再等了。於是,他決定返回中國,開辦自己的公司。
1999年,李彥宏順利融到第一筆風險投資金120萬美金,他和徐勇合夥創辦了百度公司。百度最初的業務是向門戶網站出賣搜索技術。2000年6月,在百度成立的9個月之後,不僅一舉拿下新浪、搜狐、網易、TOM的技術委託大單,而且向風險投資商德豐傑和IDG融得1000萬美元的第二筆資金。
儘管出售搜索技術很賺錢,李彥宏意識到做一家出賣技術的公司規模不會太大,決定放棄之前的賣搜索技術和解決方案的模式,轉向自己運營搜索引擎,依靠競價排名盈利。但爲了這決策,李彥宏和董事會吵翻了。
2001年初百度的一次董事會上,李彥宏提出百度轉型做獨立搜索引擎網站。然而,他的這個提議遭到董事會成員(主要投資人)的一致反對。投資人認爲,百度的收入全部來自給門戶網站提供搜索技術服務支持,如果轉做獨立的搜索引擎網站,那些門戶網站不再與百度合作,百度眼前的收入就沒了;而競價排名模式又不能馬上賺錢,百度就只有死路一條。
根據《沸騰十五年》一書的記載:2001年8月,深圳,病倒在這裏的李彥宏正在電話裏和散佈在新加坡、美國、北京的董事爭吵。聯合創始人徐勇反對李彥宏跑到前臺去做搜索引擎、搞競價排名。“我們這樣做,肯定會影響搜索技術的銷售。”董事們支持徐勇:“Robin, 我們當時投資你,可不是讓你做競價排名的!”
李彥宏不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但也不是一個輕易妥協的人。吵了三個小時,李彥宏怒了:“我他媽的不做了,大家也別做了,把公司關閉拉倒!”李彥宏猛地把手機朝桌子上摔去。
董事們被他的態度打動了。最終,投資人同意李彥宏將百度轉型爲面向終端用戶的搜索引擎公司,他們告訴李彥宏:“是你的態度而不是你的論據打動了我們。”
堅持,再堅持,總能贏得勝利。2001年8月,Baidu.com Beta版上市了。2005年8月,百度在美國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IPO成功。
我想用這個故事說明的是:企業家不能完全聽命於投資人。
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假定股東總是對的;標準的管理學理論假定集體智慧大於個人智慧,多數人的意見比少數人的意見更符合真理。但事實並非如此。
企業家與投資人的衝突有兩類:一是利益的衝突,二是認知的衝突。
經濟學承認利益衝突,但把利益的衝突簡化爲物質利益的衝突,也就是誰多得誰少得的問題;企業家追求自己的利益可能損害股東的利益,因而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約束企業家的道德風險。但事實上,利益衝突經常與目標的衝突有關。
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的,純粹的企業家不僅僅爲了賺錢,而且有超越賺錢的目標:
(1)建立自己王國的夢想;
(2)征服欲和戰鬥的衝動;
(3)對創造性的享受。
這三個目標既關係到結果,也是關係到過程本身;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不能說凡是非利潤目標都是不正當的,因爲如果那樣的話,許多傑出的企業家就消失了。熊彼特說:“只有在第一類動機中,作爲企業家活動的結果的私有財產,纔是使得這種活動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而在其他兩類中則不是。”[14]
但純粹的投資人只以賺錢爲目標,只關心投資回報率,小股東更是如此。他們只在乎結果,不在乎過程本身,因爲他們從過程本身得不到享受。
由於目標不同,利益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即便企業家不偷、不搶,也不偷懶。
但在我看來,企業家與投資人的衝突更多來自認知的不同,也就是“意見衝突”。而不是利益衝突。如前例中李彥宏與董事會的衝突,顯然是意見衝突,與利益衝突無關。
經濟學假定所有理性人對未來的判斷都一樣,對“好項目”和“壞項目”有一致的看法,因而企業家讓投資人不爽一定是因爲前者侵害了後者的利益。大謬不然!企業家之所以是企業家,就是因爲他們的判斷與一般人不同,因此,企業家的判斷未必能得到投資人的認同(小股東更是如此)。即便同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判斷也差距甚遠,何況許多投資人並不具有企業家精神。柯茲納說:“企業家精神體現的正是那些市場認爲沒有用的、事實上甚至認爲根本不需要的東西。”[15](柯茲納,1979,P.181)卡森說:“當每個人都認爲錯誤的時候,企業家認爲自己是正確的。因此,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就在於他具有與他人不同的對未來形勢的預期。”[16]
公司治理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企業家與投資人之間的認知衝突,而非利益衝突。一方面,企業家拿了投資人的錢,就得受投資人的約束,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否則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錢交給企業家。另一方面,由於投資人通常不具有企業家的判斷力,對企業家行爲的過分約束會損害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最終會損害投資人自己的利益。公司治理理論不能假定股東總是對的,企業家一定要服從投資人。
公司法上一個里程碑案例是1911年道奇兄弟起訴福特公司。[17]當時的福特公司由亨利·福特掌控,福特本人持有公司60%的股份,是大股東,道奇兄弟總共持有10%的股份,另外一些股份由分散的股東持有。公司賬戶上有一千多萬美元待分配利潤可以支付股息,但是福特沒有支付。於是,道奇兄弟向法院提出起訴。亨利·福特辯護說,公司需要這些錢來擴大規模,他正在計劃建第二個廠房裝配線,不希望企業把增長的負擔通過較高的價格轉嫁給消費者。當時汽車市場確實不是很景氣,但增加投資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一個公司的投資決策不是依現在的市場來制定,而是要看對未來市場的預期。
法院判決道奇兄弟勝訴,福特只好支付了這些股息。
如果我們承認企業家認知的獨特性,法院的判決就可能是對福特企業家判斷的否定,而不是對信託義務(fiduciary duty)的捍衛。福特從此不再信任小股東,認爲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用現金買回了所有小股東的股份。事後看,法院的判決也可能損害了道奇兄弟的利益,讓他們失去了分享福特汽車公司後來爆炸式增長的紅利。人們經常要爲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
投資人的愚蠢讓史蒂夫·喬布斯刻骨銘心。喬布斯和沃茨尼亞克1975年創辦蘋果電腦公司,1985年喬布斯被董事會趕走。趕走他的董事會成員包括蘋果的第一個投資人邁克·馬庫拉和亞瑟·羅克,這二人對喬布斯曾經如同慈父,但最後的關頭對喬布斯的認知產生了懷疑,站在了CEO斯卡利一邊。12年後,當蘋果公司面臨破產的時候,董事會有不得不把喬布斯請回來。但記取上次的教訓,喬布斯的條件是回來可以,但要自己說了算,新的董事會成員必須由他挑選。
1997年1月,喬布斯作爲一個非正式員工的“兼職顧問”入職蘋果公司。1997年7月,董事會讓CEO阿梅里奧下臺,宣佈喬布斯“做一個統領團隊的顧問”。代理CEO安德森說他“會在喬布斯的指導下工作”。
很快,喬布斯就要求董事會全體辭職,只有董事長伍拉德一個人可以留下。董事會順從了。在被要求辭職的人中,包括當初投資他後來又趕走他的邁克·馬庫拉。在伍拉德的幫助下,喬布斯很快就組建新的董事會。喬布斯曾邀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前主席亞瑟·萊維特加入董事會,後者激動不已,並開始與喬布斯討論自己在董事會的角色。但當喬布斯看到了萊維特曾發表的一篇有關公司治理的文章後,又打電話收回了自己的邀請。這篇文章的觀點是:董事會應該承擔強勢而獨立的角色。萊維特後來說:“我很受打擊……很顯然蘋果的董事會不是爲了獨立於CEO而設計的。”是的,喬布斯不喜歡一個強大的董事會。他要自己說了算![18]
(2019年10月19日稿。)
05
企業家不是“好員工”
伯尼·馬科斯(Bernard Marcus, 1929-)是美國著名企業家,建材連鎖超市家得寶(Home Depot)的創始人。
他出生於一個俄羅斯猶太人移民家庭,上中學的時候就曾想當一名醫生,但因交不起一萬美元的賄賂金給招生人員,與哈佛醫學院失之交臂。他進入羅格斯大學讀了藥物專業,靠勤工儉學讀完大學。大學畢業後,他當過藥店藥劑師,也換過其他工作,最後做到聖地亞哥一間建築材料連鎖店的經理。
作爲連鎖店經理,伯尼·馬科斯經常給公司老闆提建議。他提出的全新經營理念與老闆的想法不同,讓老闆煩不勝煩,最後被老闆開除了。
伯尼不服氣,下決心要建一間自己的建材商店,去實踐他全新的經營理念。他找到了在同一間建材商店裏任財務總監的阿瑟·布蘭卡(Arthur Blank),鼓動阿瑟辭職和他一起去創辦屬於自己的全新“建材超市”。
1979年,馬科斯創辦了家得寶建材超市,時年50歲。公司於1981年上市,馬科斯和布蘭卡都成了億萬富翁。2002年,馬科斯從董事長位子上退休,時年73歲,布蘭卡接替了他的位置。2014年,家得寶在全球有2200多家店,僱員超過35萬人。
我想用這個故事證明的是:企業家通常不是“好員工”。
所謂“好員工”,就是執行命令、按程序辦事的員工。他們很具有專業精神,但把服從權威當作天職,缺少企業家精神。
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固執已見,不願意服從權威,經常不守規矩。他們喜歡擺佈別人,而不是被別人擺佈。他們是規則的制定者和破壞者,不是規則的執行者。他們是偏執狂,不是“好好先生”(Mr. Yes)。小時候,他們一般不是乖孩子,經常會惹是生非費。這樣的人在企業內部通常會覺得自己無用武之地,創造力不能得到有效發揮。此時,他們就會離開現在的僱主,創辦自己的企業,成爲企業家。事實上,相當一部分企業家都曾有過當僱員的經歷。像卡耐基、福特、英特爾三劍客,都是如此。
《哈佛商業評論》1985年第11期發表了標題爲《創業的陰暗面》的文章,作者讚許地引用了一位企業家的如下觀點:“通常企業家都是難搞的員工,於是就自己創辦公司。他們不接受別人的建議或命令,並渴求經營自己的公司。”作者認爲,與僱傭的高管不同,企業家是懷疑權威的,他們不願意融入現有組織或科層。“相反,他們往往會覺得這樣的結構令人壓抑。他們發現,在已有的體制中,很難與人合作,除非公司結構由他們創建,工作按他們的要求完成。”他們之所以成爲企業家,是因爲他們無法屈從權威,也不願意遵守已有公司的規則。[19]
王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個性張揚,以自我爲中心,我行我素,追求與衆不同,從不循規蹈矩。他有強烈的征服欲和表現欲,喜歡冒險和挑戰,甚至願意冒着死亡的危險證明“我能,你不能”。所以,無論在部隊當兵,工廠當個人,還是在鐵路局當技術員,政府機關當科員,他都感到憋屈,活得很痛苦。但他又憋不住,一有機會,就鋒芒畢露,喧賓奪主,甚至搞惡作劇,尋找自己的存在感。他讓上級難堪,上級怎能不給他小鞋穿?
幸運的是,改革開放後,王石這樣的人可以選擇不當。1983年,32歲的時候,王石毅然辭去廣東省外經委的公職,離開廣州,來到深圳,自己創業,開始了他的企業家生涯。作爲企業家,王石的標誌性成就是萬科房地產公司。
現在不少人熱衷於討論如何激發公司內部的企業家精神。當老的公司面臨創業和創新精神衰退的時候,激發內部企業家精神是有意義的。像思科、阿里巴巴、騰訊、海爾等公司都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但真正做到並不容易。
當一個公司變得越來越大時,嚴格的規則和科層結構是必不可少的,管理必須職業化和規範化,否則,公司就不可能有效運營。但企業家精神的本質決定了,隨着公司的變大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企業家精神的密度一定會逐步稀釋。或許,這就是企業難以基業長青的主要原因。
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是兩個不同的物種,企業家精神總是在創業企業表現得更突出,大公司很難不被職業經理人主導。雅虎公司收購周鴻禕創辦的3721公司後,曾希望周鴻禕成爲一個職業經理人,管理好雅虎中國。但周鴻禕本質上是一個企業家,不是職業經理人,最終只能選擇離開。[20]
06
對經濟學的挑戰和政策含義
前面,我通過幾個故事引出了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的幾個結論: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企業家決策不是約束條件下求解;企業家決策不以利潤爲唯一目標;企業家不能完全聽命於投資人;企業家不是“好員工”。
正如我在一開始就講到的,我相信,這些結論具有普遍性。
如果我的結論基本是正確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就面臨很大的挑戰。經濟學是有關市場的理論。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範式是理性人決策模型。理性人決策模型就是滿足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目標函數,諸如“市場失靈”這樣的理論就是從這樣的範式推出來的。如果真實世界的企業家不是按照這樣的模型做決策,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理論就是誤導的,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的政府幹預政策就沒有了理論基礎。
比如說,按照主流經濟學理論,如果存在正的外部性,企業家的最優決策就不可能符合社會效率標準。特別地,企業家不可能有足夠的積極性從事重大創新,因爲重大創新的正外部性太大了,企業家從中得到的只佔社會總收益的很小比例。但無論是由於“過分樂觀”,還是因爲追求超越利潤之外的目標,企業家經常做一些從理性計算來看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如菲爾德鋪設海底電纜)。這意味着所謂的“外部性”並不一定削弱企業家創新的積極性。由於過分樂觀,許多企業家會失敗,甚至每個成功的企業家都有過失敗的經歷,但少數成功的企業家給社會帶來的財富是巨大的,遠遠超出他們自己得到的回報。因此,外部性並不構成政府幹預市場的正當理由。
再比如,按照主流經濟學理論,佔據壟斷地位的企業會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排斥競爭者進入,不僅不思進取,而且用高價格剝奪消費者剩餘。但如果企業家決策不是基於計算,而是基於想象力和判斷,競爭總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來自意想不到的對手,任何企業都不可能靠現有的產品和技術維持壟斷地位,除非他們自己做出正確的判斷,爲消費者生產出更好的產品。雄心勃勃的新企業家總是試圖用新的理念打垮在位的優勢企業,取而代之;而成熟的企業由於企業家精神的衰退,官僚主義盛行,面對新的挑戰者,總是應接不暇,顧此失彼。結果,整個經濟猶如旅館,裏邊住滿了客人,但那些客人總是變動不息,許多新客人名不見經傳,許多熟悉的老面孔不得不走人 。[21]因此,所謂經濟學家所謂的“壟斷”,也不能構成政府幹預市場的正當理由。真正打垮“壟斷者”的是新的企業家,而不是政府的反壟斷部門。
產業政策也是一個例子。產業政策的有效性以決策者對未來產業和技術的發展方向能達成共識爲提前。如果企業家的判斷是獨特的,創新是非共識的,產業政策不僅不會奏效,而且會嚴重抑制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因此,最好的產業政策是沒有產業政策,如此,才能形成衆多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創新層出不窮的局面。我們無須擔心沒有產業政策的扶持就沒有“第一個喫螃蟹”的人,因爲企業家的本性就是嘗試新的東西。產業政策導致的“羊羣效應”總是帶來資源的巨大浪費,更別提尋租行爲帶來的消極後果。
我們的結論對公司治理理論和實踐也有重要含義。傳統的公司治理理論不僅忽視了企業家非利潤目標的積極意義(非利潤目標等同於“控制權收益”,控制權收入在經濟學中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而且無視企業家與投資人在認知上的衝突。比如說,主流的公司治理理論假定小股東總是對的,錯的一定是控股股東。結果,“完善公司治理”等同於約束企業家,一整套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策把公司變成了一個準官僚機構,嚴重地抑制了企業家精神。那些公司治理最“規範”的企業,在創新方面往往乏善可陳。我相信,如果華爲是一個上市公司,很難有今天的輝煌!
只有理解了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才能真正明白市場如何運行,政府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2019年10月22日稿。)
參考文獻:
[1] 關於英特爾發展簡史及歐德寧在iPhone處理器上決策失誤的詳細描述,參閱(日)湯之上隆著《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第7章。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
[2] Ludwig Lachman. 1986. The Market as an Economic Process. Oxford: basic Blackwell.
[3] Frank Knight.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Houghton and Mifflin.
[4] F. A. Hayek. 1978.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By F. A. Haye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79-90.
[5] James M. Buchanan and Viktor J. Vanberg. 1991. “The Market as a Creative Process.”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7(1), 167-186.
[6] 雷納·齊特爾曼:《富豪的心理》,第10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田亮譯。
[7] 關於杜廈下海經商及邀請“蘇聯國家大馬戲團”來華巡迴演出的詳細過程,見杜廈著《一個人和他的時代:杜廈自傳》第413-498頁。
[8] 雷納·齊特爾曼:《富豪的心理》,第11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田亮譯。
[9]關於菲爾德鋪設跨大西洋海底電纜故事的文學化描述,見(奧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人類的羣星閃耀時》一書中《越過大洋的第一次通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舒昌善譯。
[10]見熊彼特著《經濟發展理論》第106-107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何畏、易家詳等譯。
[11]熊彼特著《經濟發展理論》第177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何畏、易家詳等譯。
[12]參閱雷納·齊特爾曼:《富豪的心理》,第9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田亮譯。
[13]參閱雷納·齊特爾曼:《富豪的心理》,第115-116頁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田亮譯。
[14]見熊彼特著《經濟發展理論》第107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何畏、易家詳等譯。
[15]I.M. Kirzner. 1979.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P.18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Casson, Mark 1997.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p.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轉引自彼得·克萊因:《資本家與企業家》第72頁。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7] Dodge v. Ford Motor Co., 170 N.W.668 (Mich, 1919). See Clark, Robert C. 1986. Corporate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見(美)沃爾特·艾薩克森著《史蒂夫·喬布斯傳》,第22和23章。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9]Manfred F. R. Kets de Vries. “The Dark Side of Entrepreneurship.”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 1985). 這裏的文字轉引自雷納·齊特爾曼:《富豪的心理》,第8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田亮譯。
[20]見周鴻禕著《顛覆者:周鴻禕自傳》,第十章。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21]這裏,我借用了熊彼特的比喻。見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第179頁。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何畏、易家詳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