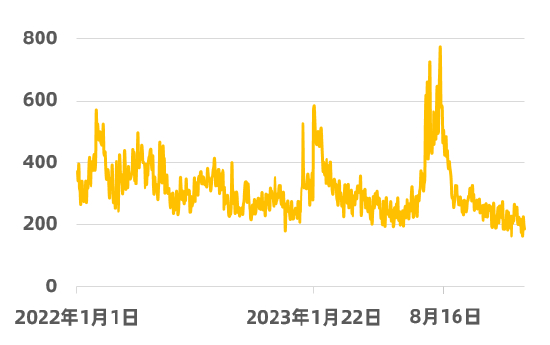失蹤6年大學生:沉迷遊戲錯失畢業 看到報道決定回家
(原標題:失蹤6年大學生:沉迷遊戲錯失畢業證,看到澎湃報道決定回家)

在鄭永全“消失”的6年裏,沒有人知道他的祕密。
“我沒被任何人控制,是我自己的原因。這6年來一直想家人,就是沒臉回家,沒臉面對家人。”
日前,失蹤了6年又重現的畢業大學生鄭永全告訴澎湃新聞,“謝謝大家把我從迷途拉出來,要不是看到你們的報道,我可能現在還沒有回家。”
澎湃新聞此前報道,2014年7月,鄭永全大學畢業回家,幾天後,以和學校簽訂合同去西安某電子廠實習爲由離家。離家後,鄭永全曾與父親通電話報平安,然而電話卻被陌生女子接過並掛斷。此後,鄭永全“消失”了整整6年。
這6年來,家人想盡一切辦法苦苦尋找鄭永全,上了年紀的爺爺奶奶相繼離世。下落不明的鄭永全成了一家人心頭的“痛”。看到報道的鄭永全,躲在被子裏哭了一宿,做了一個6年來都沒有勇氣做下的決定:回家!
7月28日深夜,母親和叔叔到西寧火車站接他回家。六年沒見,當鄭永全還沒從火車站出來的時候,母親一直在那裏哭,等兒子出來之後,母親馬上擦乾了眼淚,跟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比以前胖了”。
“媽媽沒有責怪我,只是擔心我,問我這幾年過得好不好,有沒有受過啥欺負。”鄭永全說自己耽誤了6年的青春,改了一個微信名“重新開始”。

揭開“消失”六年的謎團
鄭永全“消失”這六年,對於家人來說,是空白的。
他失蹤前後的種種跡象:身上有傷、頻繁向家裏要錢、電話被陌生人掛斷、遺落的身份證、跟某電子廠簽訂的工作合同並不存在等等,成了家人牢牢抓住的“線索”。
他們曾猜測過種種可能:鄭永全可能被傳銷組織或非法組織控制。
“家人以爲我被壞人害死了,我不忍心看到他們這樣擔憂,就下定決心回家了。”回家後,鄭永全坦白了“失蹤”的真相:大學期間因貪玩成績很差,最終沒能拿到畢業證,沒有勇氣跟家人聯繫。
而沉迷網絡遊戲是罪魁禍首。事實上,鄭永全從高二開始就沉迷於網絡遊戲,成績也因此一落千丈,班級排名從前幾名倒退到十幾名。起初被班主任作爲重點生培養的他,最後高考僅考了個大專。
2011年-2014年,鄭永全就讀於南昌大學共青學院(現爲“南昌大學鄱陽湖校區”)的信息與工程相關專業,學習電腦維修。
讀大學是他第一次出遠門,從青海來到江西,接觸外面的社會。大學課程相對較少,缺乏自制力的鄭永全網癮越陷越深,直到大三第一學期結束,他累計有十幾門課程“掛科”。
2014年臨近畢業,沒能拿到畢業證的鄭永全打算自己掙錢參加補考,當時學校一門課的補考費是600元。他找了工地的臨時工,然而纔剛幹了幾天活,就不小心被石板砸傷了腳,錢沒賺到,反而受了傷。他只好以生活費和培訓費爲由,向家裏要錢買藥治療。“這也是爲什麼那年我頻繁向家裏要錢。”
那段時間,他在網吧留宿,不小心丟失了身份證和銀行卡,也錯過了補考的機會。2014年7月,鄭永全借了點錢回家,本打算跟父母認錯,但始終不敢說出真相。
“家裏的經濟條件並不好,父母很辛苦,供了我讀書這麼多年,最後我連個大學畢業證都沒拿到,我沒臉說出口。”鄭永全記得,爲了謀生,父親曾在開拖拉機時腿受過傷。
鄭永全萌生過輟學的念頭。他讀高三,哥哥鄭永勝讀大學的那年,原本窘困的家庭要供兩個人讀書。鄭永全爲了減輕家裏的經濟壓力提出退學,父親阻止了他。
在鄭永勝眼裏,弟弟性格較內向,不愛說話,不願與陌生人交流。他總是擔心弟弟會被人欺負。高中軍訓時,鄭永全被太陽曬暈倒地,弄傷了鼻子,哥哥以爲他被人打了,就到宿舍挨個問,“他很關心我”。這次回家,哥哥關注到他的腳傷,他謊稱是被摩托車撞的。
在愧疚中煎熬了三天後,鄭永全離開了家,留下了另一個謊言——與學校簽訂合同去西安某電子廠實習。“所有人都沒有想到,這一次是最後一次見到我。”
離家六年,輾轉多座城市
鄭永全家住青海省西寧市湟中區,離家後,他開始在當地找工作,那通“被陌生女子掐斷的電話”正發生在這段時期。
他回憶,那晚自己還未找到工作便在網吧留宿,無奈手機欠費,只好用網吧的電話打給父親報平安,電話卻被別人無情地掛斷了。
一個念頭一閃而過。鄭永全覺得,他跟家人的牽絆也似乎被硬生生地掐斷了,“之後再也沒臉聯繫了。”
因爲補辦身份證需要戶口本,鄭永全始終沒敢和家人聯繫,只好在西寧市幹了三個月的日結工作。這是份看運氣喫飯的活,他經常是好幾天才能找到活幹,賺一點錢勉強養活自己。即使離家不遠,他還是不敢回家,沒地方住時,就習慣性地睡在網吧。
2014年10月,鄭永全跟隨朋友去了西安,在某中介所的安排下,入職某保安公司,這一干就是6年,輾轉於北京、河北、深圳、西安等地。
他像飄萍一樣,風一刮,又換了一個容身之所。鄭永全所就職的安保公司通常跟甲方公司籤一年或者半年的合同,合同一到期如果續不上,領導就會把他再分配到其他城市。他只好又一次搬家,帶着簡簡單單的行李。
“也沒有很辛苦,反正身邊也沒有親人,在哪都一樣。”在外漂泊,鄭永全也幾乎沒有什麼要好的朋友。下班後,他極少待在宿舍,多是一個人去網吧,或者去KTV跟陌生人一起喝酒。
偶爾深夜回到宿舍,看到室友和家人打電話,他會想回家,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鄭永全記得,2016年的春節,宿舍裏有一位老頭拍了視頻給家裏人看,他的孫子、女兒、兒子都給他送祝福。“我有點羨慕,過年的時候經常想家,但是就是下不了決心回家。”
他也曾想過換其他工作,“想找份更體面的工作或者學習一門手藝,再回家認錯”。但苦於沒有身份證,鄭永全沒有爭取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回家的時間也一拖再拖。

“回家的情景跟想象不大一樣”
鄭永全回家的動車從西安北站出發,到西寧站要五個半小時,他看着窗外天色一點點暗下去,腦海構想了很多種回家的場景:父母可能會很生氣,村裏人會對他指指點點。
“會不會沒有面子”,鄭永全忐忑不安。“回家”這個計劃有點突然,這是一個晚上做下的決定。
一天前,7月27日晚,鄭永全在網頁搜索自己的名字,看到澎湃新聞的報道,得知爺爺已離世以及家人還在苦苦尋找自己。他徹夜難眠,“我哭了一晚上,宿舍的人問我咋了,我說‘我沒事’,第二天早上就下定決心跟家裏人聯繫了。”
他其實一直保留着父親的手機號碼。當晚他鼓起勇氣,通過這個號碼添加了父親的微信,“一直沉默,不敢發消息”。
28日上午,鄭永全將微信名改爲“重新開始”,考慮到父親上了年紀,情緒容易激動,他先加了哥哥鄭永勝的微信,發消息說明身份後,哥哥立刻給他打了微信視頻。鄭永全看到哥哥比以前滄桑了好多,“很內疚”。
失聯多年,兄弟倆好不容易聯繫上,哥哥非常激動,讓他一定要回家。母親得知消息後,打算買張機票飛到西安接他回家。“他們怕我是騙家人的,不回來”,鄭永全用臨時身份證買了當天從西安北站到西寧站的火車票,家人才安心。

回家的情景和鄭永全想象的不大一樣。
家鄉變了。6年前,家裏還沒有冰箱、電腦、洗澡間,現在都有了,許多人也買上小汽車,蓋上樓房了。
鄭永全回家的消息在那個小地方不脛而走。第二天早上十點左右,家裏就開始陸續來人。親朋好友聚在一起,爲他放鞭炮慶祝,炒點菜和肉,喝點小酒。
“大家態度都挺好,都說人回來就好,其他事情都過去了,讓我重新開始,好好努力,找個其他工作,不要再讓家裏傷心了,以後有什麼事都和家裏商量。”鄭永全說。
得知他回家,表哥邀請他過去成都喫飯,鄭永全認真地回了一句,“我暫時不去大城市了,大城市誘惑太多啦,我經不住誘惑。”
他曾打算重新聯絡就讀的大學,補考不及格的科目,然後拿着畢業證去考西藏地區的公務員或者老師。然而,學校給的答覆是,時間太久了,不能再補辦畢業證了。
他只好放棄這個念頭。目前,他計劃參加成人高考拿到專科畢業證,然後報考公務員。
鄭永全回家之前,哥哥本打算暑期去他上大學的地方——江西,繼續尋找。而如今,方向變了。8月3日,鄭永全坐上了火車去拉薩探望在西藏當教師的哥哥鄭永勝。兄弟倆見面,聊了很多關於未來的規劃。
回家是一個新的起點。鄭永全說,雖然感覺前途比較渺茫,但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想對所有擔心我的親朋好友說一聲對不起,我以後會重新開始,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