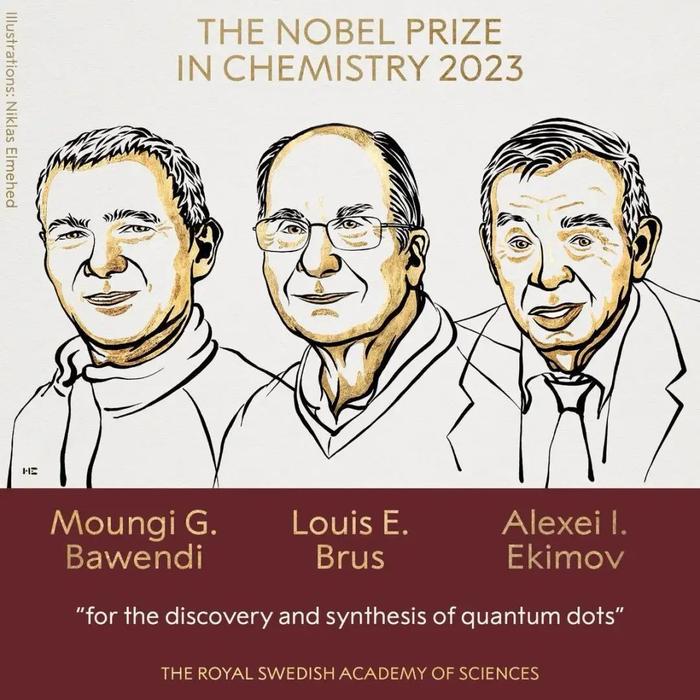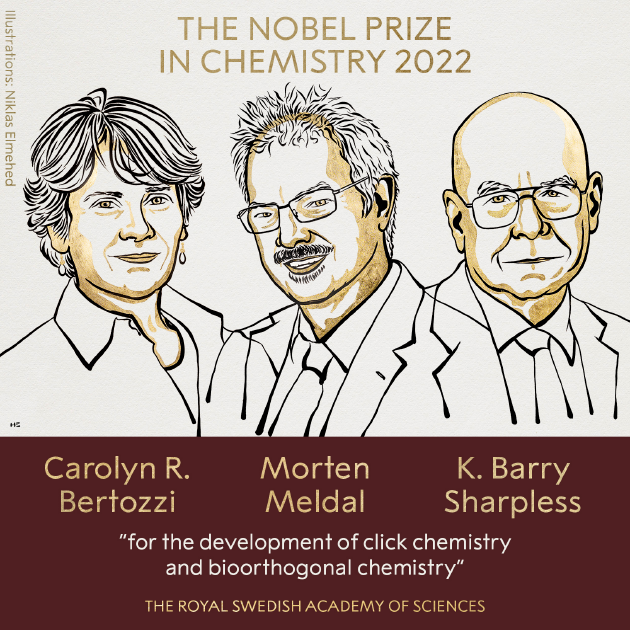CRISPR剪得諾獎!張鋒失之交臂
來源:知社學術圈
北京時間10月7日下午5點45分,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法國生物化學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國生物化學家Jennifer Doudna,以表彰其在基因編輯方面做出的傑出貢獻。
CRISPR技術自問世以來,就一直被諾獎候選的光環所圍繞。爲了CRISPR的專利歸屬權,Doudna和Charpentier曾與華裔科學家張鋒對簿公堂。但本次張鋒卻與諾獎失之交臂,令人唏噓。在這次諾獎的背後,到底又有哪些故事與八卦呢?請看知社爲您獨家整理的深度好文。

詹妮弗 · 杜德納
諾獎得主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看起來並不像一位嚴肅謹慎的女科學家。相反,她金髮碧眼、身材頎長,臉上總是帶着着明媚動人的笑容。

Doudna從小就對科學感興趣,她沉迷於熱帶雨林,對世界萬物充滿好奇。上高中時,她聽了一位女科學家的講座,介紹正常的細胞如何轉變爲癌症細胞,頓時覺得這太偉大了。也是從那一刻起,Doudna立志要成爲像這位女科學家一樣偉大的人。大學畢業後,Doudna就開始潛心鑽研RNA模型,研究RNA對於細胞發揮的不同功能。
也許正是因爲這種獨特和與衆不同,才讓她能遠離人羣,從事孤獨的科研事業。Doudna的丈夫Jamie Cate回憶:“她的成長環境培養了她堅強的性格,她可以應對很大的壓力。”
發現CRISPR之旅
Doudna第一次聽到CRISPR這個詞是2006年。在與加州大學貝克利分校的Jill Banfield教授主動聯繫,Banfield說CRISPR與RNAi之間可能存在着某種共性,而Doudna的課題組當時主要的研究領域正是RNAi。
很長一段時間內,Doudna一直從事RNAi功能的研究,而現在看來CRISPR有着與RNAi相似的功能。對於Doudna來說,CRISPR這一研究課題的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並且她認爲當時的時點對於她來說也非常有利:雖然已經有人提出了關於CRISPR功能的理論,但並沒有人能夠完全驗證並且解析完整的作用機制,而她作爲資深的分子生物學家做這方面的工作自然是得心應手。
2011年初,Doudna在美國微生物學會年會上遇見了Emmanuelle Charpentier。Charpentier從2000年初就一直對CRISPR很感興趣,通過生物信息學分析他們預計編碼該RNA的基因序列與CRISPR位點臨近,並推測其可能影響CRISPR的功能。然而該系統的作用機制她卻並不清楚,與Doudna合作會是她比較明智的選擇。

Doudna和Charpentier
Doudna對這次合作感到非常興奮,此前她並沒有涉足過第二類CRISPR系統的研究,而這次的合作爲她的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詹妮弗大概怎麼也不會想到,正是這一次相逢,改變了她的整個職業生涯。
經過不懈努力,2012年6月8日,Doudna和Charpentier向科學雜誌提交了論文,僅在二十天之後該文章就被接收。Doudna和Charpentier的文章爲CRISPR作爲基因編輯工具的應用奠定了基礎,但該文章僅驗證了該系統剪切遊離GFPDNA的能力,而CRISPR系統能否在細胞內剪切DNA,成了另一個急需驗證的問題。他們一刻也不敢耽誤,馬上又着手展開實驗。
然而早在Doudna和Charpentier的文章發表之前,很多人就已經預計到CRISPR的巨大潛力,這其中就包括張鋒和Geroge Church。出人意料的是,雖然Doudna在2012年5月25日就提交了保護CRISPR技術的專利申請,但七個月後提交專利申請的張鋒卻先拿到了專利授權。
2016年1月,Doudna所在的加州大學要求對張鋒所在的布羅德研究所的最早專利以及另外11項專利進行專利干涉,從而引發了著名的CRISPR專利大戰。但最終這場專利之爭以布羅德研究所的張鋒團隊勝出告終。但是縱使如此,Doudna和Charpentier對CRISPR開創性的工作還是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各類榮譽紛至沓來。

Doudna和Charpentier因CRISPR技術上的貢獻榮獲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
捍衛倫理的科學家
正當CRISPR技術令學界和商界激動不已時,關於該技術的社會倫理問題也引起了廣泛爭議。在負責任地應用基因編輯技術的問題上,Doudna始終有自己的堅持。
“今天科學是無國界的。很顯然不同國家對於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所引起的倫理問題也持有不同的態度。但我總是希望我們科學家能夠以負責任的態度來推進科學的發展。”
關於基因編輯技術在胚胎上的應用,Doudna認爲這離化學有點遠,但她同時也表示,對那些擔憂人類進化的傳言置若罔聞也是不負責任的。“我不希望看到科學家把技術用過頭(比如製造轉基因嬰兒等),以至於引起公衆的抗議,這也是我一直不斷地投身於倫理辯論的原因,我希望公衆參與進來,而不是覺得自己是置身科學技術之外的。”
獲得了巨大榮譽後,Doudna再也沒有時間去打理自家的花園,這曾是她最大的愛好。CRISPR研究中的關鍵合作伙伴Charpentier,也將實驗室搬到了德國,不再與Doudna合作。
不過,對於這種變化,Doudna還是能夠坦然應對。她表示,自己和Charpentier依然保持着朋友關係。而如何學會“在榮譽下生活”,Doudna這樣回答:“這也是不斷學習的過程,我非常辛苦也非常努力地向人們解釋我們所從事的科學,同時也學着瞭解別人的想法,看到不同文化思想的碰撞。同時,女性科學家相比於男性也有獨特的優勢,比如女性更加註重與人的溝通。”

埃馬紐埃爾 · 卡彭蒂耶
諾獎得主埃馬紐埃爾·卡彭蒂耶 (Emmanuelle Charpentier) ,從獨行學霸步步蛻變爲CRISPR女皇,這位法國麗人不動聲色地完成了一場寂靜革命。
精靈古怪,執着而剛強。她的面龐透着法國的浪漫,也流露着北歐的冷峻。她站在全球科學的聚光燈下,卻不忘自己的學者本色;她被推上基因編輯專利之爭的風口浪尖,卻能夠靜守科研之心,再創佳績。這是一場無聲的變革,也是一次激烈的交鋒。

作爲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Cas9) 主要開創者之一,卡彭蒂耶一路如何走來,又怎樣看待取得的成績和未來的發展呢?讓我們走進這位法國麗人。失敗的故事千篇一律,成功的經歷各有不同。她20年間輾轉5個國家、9個研究所,堅守夢想潛心工作。對比我們自己的韓春雨,您會發現有什麼樣的相似,什麼樣的不同呢?
除了電腦,埃馬紐埃爾·卡彭蒂耶的辦公室內並沒有什麼擺設。她的相框依然躺在角落的盒子裏,沒有拆封。旁邊的房間裏堆滿了紙箱子,裝的都是書籍和論文。然而在走廊的另一端卻是不同的景象,她正在實驗室中忙得熱火朝天。
六個月前,卡彭蒂耶幾乎放下了手中的一切,搬到柏林,專攻自己的科研事業。她倚在仍然泛新的座椅上說:“我們下定了決心,要以最快的速度推進我們的研究。”
醫學夢想
卡彭蒂耶在巴黎附近的一個小鎮長大,從很小開始,她就有了清晰的人生目標:做些什麼來推動醫學事業。有一次去修道院拜訪身爲傳教士的姑姑,讓她對未來有了這樣的暢想:在一個可愛的環境裏,獨自做自己的事情。
無論做什麼,父母都完全支持卡彭蒂耶的夢想。她曾學過鋼琴和芭蕾,但最終還是投向了生命科學。從巴黎第六大學畢業後,卡彭蒂耶決定進入巴斯德研究所繼續讀博。在這裏,她在基礎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現爲她贏得了讚譽,同時她還加入了夢寐以求的抗生素抗性研究項目。博士期間,卡彭蒂耶對細菌DNA片段進行了分析,該DNA可在基因和細胞之間移動,並傳遞抗藥性。

巴斯德研究所的時光對卡彭蒂耶非常重要。用她的話說,她所在的部門“年輕而有趣”。她常到巴黎聖母院旁邊的聖日內維耶圖書館去自習,坐在古老的書桌上,映着那溫暖的光影,獨自享受靜謐的科學時光。“我感到這纔是屬於我的環境。”卡彭蒂耶夢想着在研究所裏擁有一間自己的實驗室,她決定到海外接受一段博士後訓練以積累更多經驗。“我是個很典型的90年代法國學生,我覺得經過一些短暫的遊學之後,我會回到家鄉繼續自己的工作與生活。”
兩個博後
卡彭蒂耶往美國投了50來封簡歷,也收到了滿滿一兜子offer。最終她選擇跟隨洛克菲勒大學微生物學家Elaine Tuomanen,進行肺炎鏈球菌相關研究。這種細菌是肺炎、腦膜炎、敗血症的主要致病因素,與可移動遺傳因子具有很特別的自由關聯,可以在基因轉移過程中保持高致病性。Tuomanen的實驗室內擁有最新的基因序列,便於研究那些遺傳因子的着陸地點及其變化。
在這裏,她展開了一連串艱難的實驗,以確定那些致病菌如何追蹤和影響遺傳因子,並分析致病菌怎樣獲得了對萬古黴素的抗性。前往紐約後,卡彭蒂耶一心專注於工作,驚異地發現自己並不那麼想家。當Tuomanen把實驗室遷往田納西孟菲斯時,卡彭蒂耶想留下來,於是跟隨紐約大學醫學院皮膚細胞生物學家Pamela Cowin,用小白鼠做實驗,繼續研究哺乳動物基因。

Cowin回憶起來,覺得卡彭蒂耶作爲博士後完全不需要別人督促。“她積極主動,心思縝密,簡直就是在主導項目。”同時,她也是個安靜內向的人。很快,卡彭蒂耶發現對老鼠進行基因改造與操控細菌相比要困難很多。她在項目上花了兩年時間,發表了一篇關於毛髮生長機制的文章。對卡彭蒂耶來講,這是一次就哺乳動物基因的堅實訓練,同時也引起了她在基因工程上進一步探索的強烈渴望。
獨立研究
兩段博士後經歷後,卡彭蒂耶明白,下一步是完全獨立的時候了,她選擇回到歐洲。美國的日子讓她感受到自己不僅是一個法國人,更是一個歐洲人。2002年,她去了維也納。在不太穩定的短期資助下,她的小實驗室運行了七年。卡彭蒂耶回憶:“我不得不靠自己生存下去,不過我心裏也一直牽掛着細菌每個生化路徑的調節方式。”這是一段令人興奮的科研時光,小分子RNA在基因調控中的重要性被揭示,卡彭蒂耶也在諸多不同項目中對各種細菌進行研究。期間,她發現了對化膿性鏈球菌的毒性具有重要作用的RNA。
正是在維也納的時候,卡彭蒂耶第一次開始思考CRISPR。當時,這還是一個鮮有人觸及的領域。只有那麼少數幾位微生物學家在關注着這一最新動向。在某些細菌的基因中,那一撮樣式奇異的DNA起着抗擊病毒的作用,這就是所謂的Clustered regularly-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這些病菌將侵入病毒的DNA片段複製並嵌入自身基因組,從而能夠在病毒再度入侵時對其識別並切斷其DNA。不同的CRISPR系統擁有不同的攻擊方式,不過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所有這些系統都涉及到CRISPR RNA分子。

卡彭蒂耶對確定化膿性鏈球菌基因組中製造這種RNA的區域非常感興趣,於是在她的推動下,與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分子微生物學家Jörg Vogel達成合作。當時Vogel正在開發大規模繪製基因組RNA的方法。到了2008年,他已經測定了該細菌所能產生的所有RNA分子序列。
研究組最先注意到一種全新的極爲豐富的小型RNA,並稱之爲反式激活CRISPR RNA (tracrRNA)。其序列和在基因組中的位置,與卡彭蒂耶的生物信息學研究結果相一致。研究組認識到這可能涉及到一個以前從未描述過的CRISPR系統。在大量的實驗基礎上,卡彭蒂耶確定這隻包含三個組成部分——tracrRNA,CRISPR RNA和Cas9蛋白。這很奇怪,因爲“其他CRISPR系統一般只涉及一種RNA和多種蛋白,沒有人會考慮到兩種RNA”。而這一系統又極其簡單,卡彭蒂耶已經意識到,終有一天它會被人類馴服,成爲一種強大的基因工程工具。如果其成分可以被控制,它很可能會提供我們尋覓已久的能力:對基因組中精確選擇的位置,進行定位、剪切和編輯。
“啊哈”時刻
CRISPR系統具體又是如何工作的呢?卡彭蒂耶懷疑那兩種RNA會相互作用從而引導Cas9蛋白到達病毒特定的DNA序列位置。這一理念頗具革命性,這樣的“團隊協作”對蛋白質來說司空見慣,對RNA來說卻不是這樣。不過,用Tuomanen的話說,“卡彭蒂耶總會在基因組中尋找那些出乎意料的東西。她是個非常反傳統的人。”據卡彭蒂耶自己回憶,當時她很難說服手下那些年輕學生按照她的直覺去開展關鍵性實驗,以驗證兩種RNA是否相互作用。但最終,維也納大學的碩士生Elitza Deltcheva自告奮勇。
2009年6月,卡彭蒂耶再一次搬家。維也納那些浮誇的建築令她感到壓抑,在這裏她從未能讓心靈放飛。她明白,自己需要更多的支持,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在我事業的那個時段,我需要奢侈一把,全心去完成一個重大的課題。”這一次,她選擇了位於瑞典北部的于默奧微生物研究中心。那裏剛剛成立,裝備精良。北歐的人性化環境令她感到舒適,她甚至開始喜歡上那漫長而黑暗的冬夜。那讓她忘卻了時間,更加專注於工作。
那年夏天,卡彭蒂耶還在奧地利和瑞典之間奔波。當研究所的Deltcheva在晚上8點告訴她實驗成功的時候,她簡直太開心了。不過她沒有把消息告訴任何人。用Vogel的話說,那是個“非常緊張的時期”。八月的一個夜晚,他曾接到卡彭蒂耶打來的電話,當時他正在柏林外的鄉村路上開車,“當時我就站在路邊,和她討論發表的最佳時機。我彷彿在那站了好幾年,因爲我們真真正正地做成了這件事。”
他們都知道這一發現將帶來巨大變革,但兩人也都害怕這件事的任何信息被搶先報道出去。爲了確保論文評審不被拖太長時間,他們安靜低調地作了一年多準備,在提交給Nature前儘可能考慮周全。
惺惺相惜
儘管那時的CRISPR圈子很小,但卡彭蒂耶並不爲人所瞭解。直到2010年10月,他們纔在荷蘭瓦赫寧根的學術會議上首次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會議主辦人,瓦赫寧根大學微生物學家John vander Oost說:“那絕對是會議的亮點,人們突然看到這樣一個美麗而又出乎意料的故事。”不過,卡彭蒂耶並不介意作一個局外人。“我從沒有設想過要成爲這活躍的科研圈的一部分。”那時,她已經在琢磨下一步工作,思考這種雙引導RNA系統是如何切開DNA的。

Charpentier與Doudna
2011年,在美國聖胡安的微生物學會議上,卡彭蒂耶遇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學結構生物學家詹妮弗·刀娜 (Jennifer Doudna)。也許是惺惺相惜,刀娜很快被卡彭蒂耶的氣質所吸引。“從見到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歡上了她那種專注。”兩人一拍即應,展開合作,很快發現了Cas9蛋白切斷DNA的機理。此後,她們進一步展示了該系統確實可以對基因定點剪切,並進行序列編輯。如今,這項技術已經在全世界的實驗室中廣泛應用。
就在這一舉成名的時刻,卡彭蒂耶作了兩個決定。首先,她決定繼續追尋那最初的理想,從事能夠推動醫學的工作。她聯繫了當時在巴黎醫藥公司Sanofi工作的諾瓦克,籌劃聯合創辦公司以開拓人類基因療法。CRISPR Therapeutics在2013年11月成立,位於馬薩諸塞洲劍橋和瑞士巴塞爾。卡彭蒂耶任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
她的第二個決定是要將全部精力用於基因調控的基礎研究。爲此,她需要一個永久職位,需要更多的機構支持。
2013年,卡彭蒂耶來到德國,擔任漢諾威醫學院教授以及德國亥姆霍茲聯合會傳染研究中心部門主任。在這裏,她終於發揮出了自己的技術,建起了擁有16名博士生和博士後的實驗室。兩年後,她又應邀來到柏林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如今,她已經掌握了豐富的技術和機構資源,她的實驗室也遷到了古老而優雅的夏利特 (Charité) 教學醫院。卡彭蒂耶大概已經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地方,正如她所講,也許過上幾年,她會有閒心讀一讀哲學。
諾獎熱門
卡彭蒂耶的工作環境可以說就是她科研生活的完美縮影。伴隨事業的進步,她也在不停地換着地方。在過去的20多年中,她曾在五個國家的九個研究所工作。已經50歲的卡彭蒂耶回首從前,不禁這樣說:“我總是從頭做起,依靠自己組建起新的實驗室。”她的博導,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帕特里斯·庫爾瓦蘭 (Patrice Courvalin) 介紹:“她是如此足智多謀,她能夠白手起家,憑空建起一間實驗室。”在依靠短期項目基金支持了多年之後,卡彭蒂耶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啊哈”時刻。直到45歲,她纔有實力僱一個自己的技術員。
四處奔波的生活方式並沒有給這位微生物學家的工作帶來阻礙。她對細菌如何調節染色體進行了認真仔細的研究。如今,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Cas9) 已經徹底改變了生物醫學研究人員理解和操控基因的能力,而卡彭蒂耶正是該技術的核心發明者之一。

今年,卡彭蒂耶已經收穫了十項科學大獎,並正式接受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傳染生物學的負責人職務。她在2013年創建的基因治療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也已成爲世界上獲得最多投資的臨牀前生物科技公司之一。而她本人也牽扯進備註關注的基因編輯專利糾紛當中。去年9月,卡彭蒂耶的電話就沒有斷過,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在練習她,認爲即將揭曉的2015年諾貝爾獎有她的位置。
對卡彭蒂耶來說,成爲大衆的焦點並不那麼舒服,這也是爲什麼在那個諾獎大熱門的“基因編輯國際名單”中,人們對她的瞭解最少。用她自己的話說,“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曾提醒過世人,獲獎將使你成爲人物。而我只想腳踏實地保持我的工作。”卡彭蒂耶確實一點沒有鬆懈,近日她在Nature發表的文章中揭示了比CRISPR-Cas9更爲高效的機制。
在同事們眼裏,卡彭蒂耶謙和而又充滿幹勁。羅傑·諾瓦克 (Rodger Novak)說:“別看她小巧玲瓏,心志可極爲遠大——有時候她會非常固執。”諾瓦克在上世紀90年代博士後期間曾與卡彭蒂耶一同工作,現在擔任CRISPR Therapeutics總裁。庫爾瓦蘭則做了這樣的比喻:“她這個人做事就像狗看見了骨頭——絕不放手。”
面對榮譽
眼下,撲面而來的榮譽和獎項已經佔用了卡彭蒂耶很多精力。她很珍惜這些褒獎,也積極參與那些必要的公衆活動。不過平均來說,每一次應酬都會佔去她兩個整天的工作時間。她拒絕評論目前備受世人關注也錯綜複雜的基因編輯專利之爭。她把這些事都交給了專利律師。
作爲一名科研人員,卡彭蒂耶並沒有過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在最新發表的論文中展示了一個比CRISPR-Cas9更爲精緻的系統。這一成果也是在遷移實驗室的過程中完成的,令人讚歎。該研究指出蛋白質Cpf1兼具tracrRNA和Cas9蛋白的功能。用Van der Oost的話說,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貢獻”。
CRISPR研究順風順水,而卡彭蒂耶的熱情並未侷限於此,這只是她實驗室中五大主題之一。其他研究還包括病原體與宿主免疫細胞的作用機制,以及調節細菌染色體行爲的分子配合物。
回首過往,卡彭蒂耶覺得從前的生活比現在要更難一些。現在的項目資金源要更加豐富,這對一些試圖建立自己獨立實驗室的青年研究人員來說更爲便利。她那推動醫學發展,促進基因工程的目標已經實現,她的理想卻始終沒有淡去。“我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卡彭蒂耶說道,“身爲一個科學工作者才讓我走到今天,那也正是我希望繼續扮演下去的角色。”

談到CRISPR技術,有一個人是註定繞不開的。他證實了CRISPR能夠在真核細胞中起作用,從而揭示了它的巨大潛力,震撼了整個學術界;但他也同時陷入了CRISPR技術的專利爭奪風波,而跟上面兩位諾獎得主對簿公堂。本次諾獎並沒有頒給張鋒,在某種意義上,或許是一個缺憾。
他、張鋒,是華人生物學界最耀眼的新星,風投競相追逐的對象,諾貝爾獎的大熱門。今天,CRISPR正因諾貝獎而風光無限,而他卻沒能收到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電話。。。

張鋒履歷:
-
1983年出生中國石家莊
-
200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化學物理專業
-
2009年取得斯坦福大學化學與生物工程博士
-
2011年加入麻省理工學院
-
2013年發現CRISPR/Cas系統可用來編輯DNA,使基因療法成爲可能。獲得美國瓦利基金青年研究家獎(Vallee Foundation YoungInvestigator Award)。
-
2014年被《Nature》雜誌評爲2013年年度十大科學人物之一;獲得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最高榮譽Alan T。 Waterman Award,Jacob Heskel Gabbay Award in Biotechnology and Medicine,和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獲得美國首個CRISPR專利;設立Editas Medicine公司,該旨在利用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開發出直接更改致病基因的療法,獲得4300萬美元風投。
-
2015年獲Tsuneko & Reiji Okazaki Award。
-
2016年7月1日,被MIT理學院(School of Science)晉升爲爲終身教授,打破錢學森的記錄,成爲MIT史上最年輕華人終身教授。
-
2016年9月21日,入選湯森路透旗下的2016年引文桂冠獎(Citation Laureates)名單。
-
2017年8月15日,張鋒獲阿爾伯尼生物醫學獎,成爲歷史上第二名獲得此獎項的華人學者。
-
2018年4月,獲選美國科學院院士。
研究生涯:
中學時代的緣起
張鋒1983年出生於中國河北石家莊,93年隨父母移民美國愛荷華州Des Moines。1994年,他12歲的時候,在一堂禮拜六的分子生物學課上觀看了電影《侏羅紀公園》。老師觀察到他對恐龍及生物工程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奮和興趣。不久以後,這位老師幫張鋒在當地的the Human Gene Therapy Research Institute實驗室找到了一份志願者的工作。從此以後,張鋒每天放學以後都會到實驗室來參與一些分子生物學的工作。

張鋒16歲時獲得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 獎第三名照片
當時,他的實驗室導師經常提出的一些“瘋狂的點子”,例如綠色熒光蛋白(GFP)能夠吸收紫外線,因此可以用作防曬霜。而當張鋒將GFP厚厚地塗在一層DNA之上時,他發現GFP真的能夠防止DNA受到紫外線的損傷。這段經歷加深了他在生物學方面的興趣,而中學時代參與的一些科研項目也幫他贏得了很多科學活動的大獎,特別是在2000年的 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張鋒獲得第三名。要知道這項享有盛譽的科學大賽起源於1942年,已經有8名獲獎者後來榮獲諾貝爾獎,其中就包括錢學森的堂侄,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錢永健教授(見圖),在1968年15歲時獲得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獎。

錢永健教授獲得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獎以及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照片
博士期間牛刀小試
高中以後張鋒順利考取了哈佛化學及物理專業。他後來解釋爲什麼選擇這個專業而不是他已經有所成就的分子生物學。雖然分子生物學每天都有令人振奮的新進展,物理和化學的基本原理卻是比較穩定的,他想要打好基礎,讓自己在今後的學術道路具有堅固的基石。在哈佛大學的本科學習期間,他受到莊曉薇的賞識,進入了她的實驗室。
2004 年,張鋒來到斯坦福大學申請就讀研究生。他原本想要拜訪諾獎得主朱棣文(StevenChu),卻陰差陽錯地碰到了剛剛擁有自己實驗室的 Karl Deisseroth。經過短暫溝通之後,Zhang 對 Deisseroth 的課題非常感興趣,Deisseroth 也對張鋒在化學和物理方面的堅實基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盡力說服張鋒加入在自己新建的實驗室。他們的合作促成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光遺傳技術(optogenetics),利用光學刺激和來自水藻的光敏感蛋白精密控制大腦神經元活動。這爲最終理解大腦如何工作,如何產生意識和情感,又如何在神經退行性疾病中發生故障提供了阿拉丁神燈一般的強有力工具,也使得他們在腦科學(brain science)的發展史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並因此榮獲了2012Perl-UNC Neuroscience Prize 和 2014 Alan T。 Waterman Award 。
獨立的巔峯之作
博士畢業後,張鋒離開了Deisseroth 的實驗室,回到了麻省,作爲研究員入職麻省理工學院(MIT)。此後,他先後進入了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和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 這兩所頂級研究機構,並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在履新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後,張鋒偶然聽到一位傳染病生物學家談論細菌中天然免疫系統的組件-CRISPR/Cas。張鋒敏銳地感覺到它的非凡潛力,於是在維基百科(Wikipedia)和其他所有他能找到的資料上學習它。在當時的2011年,已有少數的研究團隊開始利用CRISPR/Cas來靶向基因組的一些精確區域,但卻沒有人想到或者把它用作調整人類基因組的工具。而張鋒在短時間內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改進了CRISPR/Cas,證實它能夠在人類細胞中起到基因剪裁的作用。自從張鋒捅破這層窗戶紙以後,迎來了基因組編輯領域許多的進展和應用。
由於在CRISPR/Cas用於基因編輯方面的突破性成就,張鋒在2013年以後贏得了巨大的聲譽與關注。而CRISPR/Cas作爲最可能廣泛實用的基因編輯工具,有着數百億美元的商業前景,幾個CRISPR/Cas研究的開拓者都着手商業化準備。張鋒創立了Editas Medicine公司,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歐洲創立了CRISPR Therapeutics,Jennifer Doudna之前與張鋒共同創立了Editas Medicine,離開Editas Medicine後她現在創立了一家小公司Caribou Biosciences。而張鋒在2014年4月搶先獲得CRISPR相關的首個專利。

CRISPR-Cas9技術的專利申請表
潛力、爭議及期待
CRISPR/Cas是一種在大多數細菌和古細菌中存在的天然免疫系統,利用了插入到基因組中的病毒DNA(CRISPR)作爲引導序列,通過CRISPR相關酶(Cas)來切割入侵病毒基因組物質。2012年,Jennifer Doudna 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領導的研究小組在Science發表了一篇關鍵文章。文章中揭示了天然免疫系統是如何變成編輯工具的。至少,它可以在試管中切斷任何的DNA鏈。
然而這種充滿魔法的工具是否能運用到人類細胞的基因組上,最終達到剪裁編輯人類基因的效果呢。張鋒在2013年1月搶先發現了這種可能和所需的方法。Jennifer Doudna在幾周後,也發表了她自己的獨立結果。

到這個時候,科學界普遍承認,CRISPR可能是自20世紀70年代生物技術時代開啓以來發現的最重要的基因工程技術。CRISPR系統具有搜索和替換DNA的雙重功能,可以讓科學們通過替換鹼基,輕鬆的改變DNA的功能。在接下來的時間裏,科學家們已經證實,利用CRISPR可以治療小鼠的肌肉萎縮、罕見肝臟疾病,甚至使人類細胞具有免疫HIV等驚人的功能。
2014年4月15日,美國專利局將CRISPR-Cas9技術的專利頒發給張鋒所在的Broad研究所,而張鋒博士就是該專利的發明者。專利權限包括在真核細胞或者任何細胞有細胞核的物種中使用CRISPR。這就意味着,他們擁有在除細菌外的任何生物中使用CRISPR的權益,包括老鼠、豬、牛和人。這使得他和他的研究所幾乎可以控制所有與CRISPR相關的重要商業應用。
2014年11月在美國硅谷,Jennifer Doudna 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獲得了獎金爲300萬美元的The Breakthrough Prizes of Life Sciences,兩位學界高顏值女神身穿華麗黑色禮服,在好萊塢明星的簇擁下接過了The Breakthrough Prizes獎盃和獎金。她們在CRISPR-Cas9開拓性的工作獲得了極大的認可。而張鋒作爲另一位在這個領域開拓性的人物卻並沒有被列爲共同發明人共享這一獎項。

在2015年的路透社引文桂冠獎將CRISPR基因編輯技術作爲當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的大熱門,但是這項技術的發明人卻只列了Jennifer Doudna 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張鋒又一次落在了世人的視線外。外界一度認爲,張鋒在CRISPR上的成就將錯過諾貝爾獎的認可。

路透社引文桂冠獎對Charpentier和Doudna以及她們工作成就的介紹
至於到底誰才最應該擁有CRISPR基因編輯發明人和榮譽和利益,學界的普遍看法是,Charpentier和Doudna推動了CRISPR編輯的發展,張鋒則是通過證實它能夠在真核細胞中起作用而揭示了它的巨大潛力,來自哈佛醫學院的George Church則又獨立證實了張鋒的這一研究發現。
張鋒聲稱,他開拓了這一領域的研究風潮:在這一技術得到廣泛報道之前他一直在開展研究,並且由於他的實驗室過去曾經微調ZFNs和TALENs來編輯DNA,擁有了一些適當完善CRISPRs的經驗,使得他們在CRISPRs的基因編輯研究上搶佔了先機。
雖然張鋒獲得了關於CRISPRs的第一個專利,但實際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Jennifer Doudna以及當前任職於德國Helmholtz感染研究中心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提交專利申請的時間要比張鋒早了七個月。但張鋒卻被首先授予專利,這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張鋒申請了快通道專利(fast-trackpatent),他遞交申請短短6個月後就被授予了知識產權(IP)。
爲了證明自己是第一個發明者,即第一個在人體細胞中使用CRISPR-Cas的人,張鋒提供了他的實驗室筆記本的快照,以此證明他在2012年年初就創建並運行了CRISPR-Cas系統。這早於Jennifer Doudna 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的專利申請的提交時間,甚至也早於她們在Science上發佈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時間。而且根據張鋒表示,Jennifer Doudna在她早期專利申請中的預測CRISPR將會對人類細胞有用只是一種泛泛的猜想,而他是第一個證明CRISPR驚人作用的人。
2016年1月,加州大學相關組織要求對博德研究所的最早專利以及另外多項專利進行專利干涉,這個請求很快得到了相關部門的受理。不過經過一系列的專利爭奪戰之後,美國專利局在2017年2月15日判定:CRISPR關鍵專利仍然歸張鋒團隊所有。
作爲華人生物學界最具潛力的黑馬之一,張鋒此次與諾獎失之交臂實在令人扼腕。世人會記住這位爲CRISPR做出了傑出貢獻的科學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