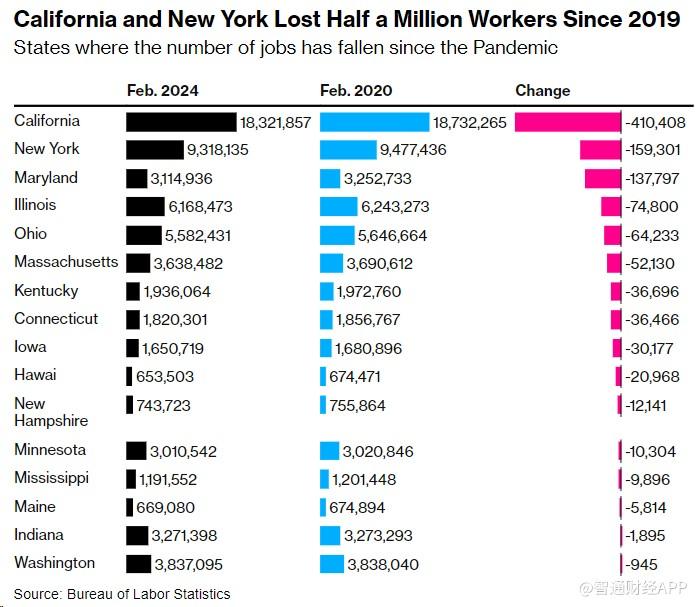“雙面”吳曉波:寫無止境
原標題:慧見| “雙面”吳曉波:寫無止境
 慧見| “雙面”吳曉波:寫無止境
慧見| “雙面”吳曉波:寫無止境
作爲中國身價最高的財經作家之一,吳曉波是個矛盾的雙面體,一方面他坦誠他這代人“對財富有天生的不安全感”,多次在採訪中直言不諱自己“愛錢”;另一方面,他又對現在以作家富豪榜的位次評價作家嗤之以鼻,他在現實中又是個不重視物質生活的人,寫作之外的所有事情都一切從簡。
吳曉波曾經的理想是像李普曼用一支雄渾的筆引領輿論。他也做到了,2007年他的《激盪三十年》被評爲“年度最佳商業圖書”,累計銷售超過100萬冊。2009年《跌蕩一百年》同樣熱賣。也是在2009年,吳曉波以750萬元年度版稅收入,位列“中國作家富豪榜”第五。他的“吳曉波頻道”在2018年末月均關注用戶已超過345萬人。
除了財經作家,公衆對於吳曉波的關注點還在於其企業家的身份,他的知識付費公司巴九靈正處於上市輔導期。吳曉波在2013年創辦的藍獅子出版已策劃出版騰訊、華爲、阿里巴巴、招商銀行等100多家知名企業的圖書。
12月5日,財經作家、890新商學、藍獅子出版創始人吳曉波在杭州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慧見》欄目的獨家專訪,詳解了他對中國製造和知識賽道發展趨勢的預判,以及他個人雙面人生的最大焦慮。
“2020是勇敢者的年份”
“爲什麼你們就要把我叫自媒體呢?就因爲你們有一張牌照?無非我沒有辦報紙,但現在我不需要報紙了。”——吳曉波
《慧見》:2020年吳曉波年終秀的主題是“勇敢者的心”,這是什麼含義?
吳曉波:今年新冠疫情來得太突然,每個人對2021年的預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產業經濟來看,今年表現比較好的或者說僥倖活下來的企業都是勇於挑戰自我的,所以我覺得今年是勇敢者的年份。
《慧見》:前兩年你提出了新國貨運動,跟雙循環是不是異曲同工?怎麼看新中國製造跟雙循環之間的關係?
吳曉波:就算沒有新冠疫情,這兩件事情都一定會發生。第一件是中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金後新中產的崛起,新中產會爲本國文化買單,傳統文化復興是必然的,新國貨會崛起,國產文化會成爲重要的商業賣點。第二件是中國發展到今天,內需比例一定會提高。今年雙循環是被動的決策,因爲外部巨大壓力和新冠疫情造成的,這是個偶然性事件,但推動國內的居民消費來拉動經濟發展,這是中長期戰略目標。
《慧見》:最近你發起了中國製造業領域的首個大學中德製造業大學,做什麼的?
吳曉波:我30年前當工業記者出身,一直跑工業,對製造業有感情。過去十多年互聯網對各行各業造成衝擊,製造業有種被革命的恐懼感和焦慮感。在經歷了互聯網革命、信息化革命後,中國製造業的智能化進程非常快,2015年在服裝行業和傢俱行業就能看到定製化生產,機器增加,黑燈車間增多,從企業家到基層的技工都產生了能力提高的訴求。
一個合作機構在全國有90個工業園區,每個園區近200家企業,他們提出能不能幫這近2萬家製造業企業做培訓。而我2015年就帶企業家去德國參加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德國製造業很多能力值得學習,所以我們聯繫了德國企業、大學和科研資源,就有了中德製造業大學。
《慧見》:你跟這麼多製造業接觸來看,中國製造最需要提升的能力是什麼?
吳曉波:首先是認知能力。比如說生產線,德國完成了複合式技工,一個技工管一整條生產線,能做電器,能操作機械,能操控計算機,還能編程,但中國可能需要4個技術工人。第二是生產線的精密化程度,從零部件的供應鏈到生產製造,德國在精密化程度上、在自動化程度上和智能化程度上都遙遙領先於中國。
《慧見》:今年疫情衝擊下很多實體企業對市場前景不是特別看好,智能製造的資金投入很大,錢從哪裏來?
吳曉波:投入還好,一個智能生產線花不了多少錢,關鍵不是錢,關鍵是認知水平。現在對很多企業來講反而是智能化改造的一個好時間點,因爲疫情大量企業倒閉,這對存活下來的企業是好事。智能化改造關鍵是幫助企業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賺到更多錢,能做到這兩點,再困難企業家也願意投入。
《慧見》:你覺得未來中國經濟發展5到10年的長期趨勢性機會是什麼?
吳曉波:分成供給端和需求端來看,從需求端講內需不斷繁榮和爲中國文化買單的意識崛起都會成爲一個長期的趨勢性機會。需求決定了供給,同時技術也在變革,一個傳感器,一個聲納技術,一個芯片,一個機器手都在讓各行各業發生巨大的革命和迭代。
需求和技術的這兩個變化讓中國產業經濟告別了過去野蠻和外延式發展的時代。過去中國供給端是過剩的,從襪子、鞋子到書都過剩,現在人們需要更好的書,更好的媒體,更好的思想,更好的機器,更好的飲料,供給端是優勝劣汰的過程。互聯網也一樣,流量成本越來越高,產品越來越同質化,面臨的也是優勝劣汰。
《慧見》:你成立了一支26億規模的人民幣基金做投資,怎麼挑選投資標的?
吳曉波:我們偏向投早期,投新制造、新消費和文化,投了100多家企業。比如鍾薛高,雪糕行業不是很好的賽道,但他對行業有不同理解,別的雪糕加添加劑兩三塊錢放冰櫃賣,他的雪糕零添加、低卡路里十幾塊錢放到網上賣,抓住了雪糕消費者消費升級的需求。
《慧見》:你怎麼看知識付費賽道的發展趨勢?
吳曉波:890新商學現在主要做商學教育。從知識付費升級到教育培訓,知識付費仍然佔很大營收比例。大部分知識付費公司都沒做成平臺,無非是用流量完成不同模式的商業變現。比如說我們都有投的10點讀書做線上知識付費,一條做電商,靈魂有香氣的女子做女性社羣。但890很快從線上切到線下了,我們2015年就開始做企業家培訓,做社羣。
其實你們也有自媒體公衆號,也做知識付費,爲什麼你們就要把我叫自媒體呢?就因爲你們有一張牌照?無非我沒有辦報紙,但現在我不需要報紙了。
寫作者任何經歷都不會浪費
今年吳曉波最佩服的企業家是梁建章,因爲他的改變最勇敢。
雖然吳曉波“新國貨首發”直播翻車,但寫作者的任何經歷都不會被浪費,他本人依然在加註直播賽道。他投資了直播學院,還計劃在成都和杭州打造兩個直播基地。
《慧見》:你說2020年最佩服的人是梁建章先生,因爲你直播翻車而他直播成功了?
吳曉波:不是因爲直播成功,我最佩服他是因爲我覺得他今年是變化最大的企業家。直播成功與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爲董事長衝到一線後把整個攜程士氣帶起來了,同時讓攜程完成了一次企業文化和品牌的再塑造再輸出的過程,我覺得價值在這,而並不在於說他一場賣多少貨。他在直播中賣的訂單在整個攜程佔比就千分之一或不到百分之一。攜程所在的旅遊行業今年受疫情衝擊最大,如果梁建章沒那麼早就開始直播,攜程可能士氣就很低下。
《慧見》:現在回過頭來看,你後悔走進那間“熱鬧而危險”的直播間了嗎?
吳曉波:我應該沒有後悔。但確實還是魯莽了,雖然做了很多準備還是不適應。我就是在今天在這個地方(杭州線索電影片場)做第二場直播的。事後總結這不是我該做的賽道,還是要聚焦於知識供給,但自己下水試一下,比我光站在岸上看體會更多。
《慧見》:李普曼說過一個人不能同時既看戲又演戲,你對此怎麼看?
吳曉波:我覺得做企業和做財經評論者在今天並沒有太大的矛盾,我知道自己要什麼就可以了。李普曼其實也辦過雜誌,也當過董事長。
《慧見》:兩種身份間有沒有衝突,在不同身份轉化時有困惑和焦慮嗎?
吳曉波:你們提問題的人比我更困惑,你們把自己的焦慮投射在我身上了。我2003年就創辦了藍獅子,我已經當了17年企業家了,這個問題我已經被問了17年,哈哈(大笑)。我身上所有的你認爲的矛盾或者質疑都來自於這方面,你一個文人怎麼能賺那麼多錢,一個文人怎麼能去辦企業,公司還上市還去搞併購,還做直播?我個人覺得沒有衝突。
《慧見》:在財經作家、企業家和記者這三個身份當中,更鐘愛哪個角色?哪個是短期的職務,哪個是終生的人生使命?
吳曉波:我覺得可能都是我的終身使命。
《慧見》:在墓碑上只能選一個標籤,會選什麼?
吳曉波:如果只能選一個,那就是財經作家。如果能選兩個,財經作家和890創始人。
《慧見》:寫作和經營企業對你而言分別意味着什麼?
吳曉波:寫作是我熱愛的事情,是我最大的價值呈現。我希望當下和未來,別人尊重我或者想到我,不是因爲我做了個特別大的文化公司,而是我寫的某些書。但做企業是幫助我堅持寫作的,如果這些年不是在一線做企業,我的財經寫作可能早就停掉了,我會離時代很遠。
《慧見》:從時間分配來看,現在你的寫作和經營企業是怎麼樣的比例?
吳曉波:我缺乏時間管理能力,一直都不善於短期時間規劃,比如今天時間安排就亂糟糟的,弄得大家都不太開心。但我一直有很好的長期規劃能力,我很早就決定每年寫一本書,過了50歲爭取兩年寫一本。我會給自己一個較長時間段,在其中完成一件事情。其他時間該打麻將打麻將,該看電影看電影,該旅遊旅遊。
《慧見》:時勢造英雄,中國經濟的發展造就了你過去30年財經寫作的成功。回首這30年來有沒有犯過什麼錯,錯過什麼?
吳曉波:我覺得時代對我挺好,也沒錯過什麼,如果有也是應該錯過的。我還在做我喜歡的事情,比如寫作,我還在做我喜歡的工作,比如昨天在看蘇寧的轉型。
一個人能一直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可以了,我喜歡的東西很少,我幸運的是開始工作就找到了喜歡的領域。剛畢業去新華社做記者有兩個選擇,跑工業,跑文教線。很多人不願意當工業記者,因爲1990年中國幾乎還沒什麼工業,跑工業很苦,跑文教那時圍棋、電影都很火,稿子可以上很好的版面,工業就很難。我是文科生,光看懂財務報表都花了兩年。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還是選最難走的路是正確的。
沒人想到92年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迅猛發展,讓我的選擇變成時代的選擇。也沒想到中國會變得那麼世俗和商業,現在我們評價一個作家都用富豪榜去評價,評價經濟學家也是看出場費,你出場費30萬,他20萬,所以你比他更好。多麼扯淡,但大家似乎覺得還挺好。
《慧見》:你剛纔說回首過去沒犯過什麼錯,2010年《吳敬璉傳》陷抄襲官司不是?
吳曉波:這事當時對我傷害特別大,我無法辯駁。雖然官司勝訴,但法律層面上花了兩年,道德層面上還不止。我的第一根白頭髮就是在那兩年起來的。當時很痛苦,但現在很感謝那場官司,因爲那會我寫完企業三部曲,自我最膨脹,甚至覺得我已經完成了大部分人生使命,官司讓我重新審視了我的寫作。
寫《跌蕩100年》查了很多資料,我在後記說史料查太多就不再一一註明出處了。後來就害了我,因爲不嚴謹。到今天我也很後悔,比如說我現在看當年寫的書,也找不到出處,自己也忘了,當年就多寫幾行字都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最大的焦慮是無法超越過去的自己
2020年的吳曉波還在爲無法超越2008年的吳曉波而感到沮喪。
《慧見》:所有作品中你最喜歡哪一本?
吳曉波:《跌蕩100年》。
《慧見》:賣的最火的並不是這一本,爲什麼?
吳曉波:因爲我覺得那是我寫作最成熟的一本書。《大敗局》是一個個的企業案例寫作,這對記者出身的我來講不是太大的挑戰,但《激盪30年》挑戰挺大,大量案例並行,你看到的是個無數匹馬在奔跑的跑馬場,是特別複雜的寫作,我戰戰兢兢寫了四五年,但當我把這套寫作方法摸熟以後,再寫《跌蕩100年》就特別愉快了。
《慧見》: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最大的危機感是不是害怕江郎才盡,永遠無法超越過去最鍾愛的作品?
吳曉波:對,你講的是對的。我現在不焦慮我的企業,你講的纔是我最焦慮的。比如說我寫《激盪十年,水大魚大》的時候,想換一種寫法,用詞典的方式用關鍵詞來寫,或者用紀傳體,試了三四個月還是覺得完成不了,工作量太大,還是回到《激盪30年》的寫法,那一刻我挺沮喪的。
《慧見》:爲什麼沮喪?
吳曉波:沒辦法突破原來的自己。這兩本書差了10年,2018年的我沒辦法幹掉2008年的吳曉波。第二個挑戰是如何找到當代最能夠激發大家思考的、最有價值的那個議題,所有的寫作都是爲當代寫作。或者是你有沒有勇氣去寫那個議題,這對我來講是焦慮的事情。其它都是扯淡。
《慧見》:你怎麼緩解這種焦慮?
吳曉波:沒辦法緩解。要麼你挑戰它,要麼你放棄它,我現在還不願意放棄它。所以對我來講是挺難的。我寫下一本書能不能寫成跟我之前所有書都完全不一樣的書。
《慧見》:所以你現在還在挑戰2008年的吳曉波的過程當中?
吳曉波:對。我這12年幾乎沒啥進步,從寫作角度來講。
《慧見》:是不是放在企業上面的精力和時間太多?
吳曉波:有可能。但也可能你放的少你還是寫不出來。
預測未來:中國階層固化還不嚴重
對於後浪,吳曉波說你們還有機會。對於前浪,吳曉波說好好活着。
《慧見》:回首從1990年做新華社記者到現在,你對自己的人生滿意嗎,你會給自己打多少分?
吳曉波:我挺滿意的。我得到了大學畢業時完全沒有想到的。我沒有想到我會辦企業,會在物質上那麼富有,其實也是沒想到中國會變成今天。每個人都是時代的。時代給了你很多機會,你去挑戰它,去適應它。非要打分就80分。我從小學到現在都不是班裏成績最好的,都是80來分的人。
《慧見》:有做過什麼改變自己的事情嗎?
吳曉波:沒有,其實我很少變化。這30年來都沒什麼變化,不管是從寫作者還是從企業經營者角度。我挺膽小的,我到現在還在我讀中學的城市,我沒離開過杭州,跟我打麻將的還是25年前就認識的人。
人一生能幹的事情很少,對我來講就是財經寫作,需要不斷挑戰自我。所以寫作之外能簡單就簡單,不想太佔用時間。我到現在不會開車,音樂聽最簡單的,就聽羅大佑、beyond,也不聽古典音樂,不打高爾夫,美劇英劇我都嫌太燒腦,我寧可看韓劇。
《慧見》:你不打高爾夫跟企業家怎麼交流?
吳曉波:我們要看的是他的企業,他有話跟你說就會跟你說,我跟企業家很少面臨說跟他怎麼交流的問題,沒事別見面。
《慧見》:所以你不是喜歡交際的人,不會跟企業家們打成一片?
吳曉波:我過年主動發“新年好”的除了親戚外,就沒幾個人。中國有那麼多企業家,會主動問候我“新年快樂”的也不超過三位。很多人認爲我和企業家們很熟,其實沒那麼熟。
《慧見》:你覺得外界對你最大的誤解是什麼,你最怕被定義爲什麼?
吳曉波:我真的不是很care,不可能討好所有讀者,不喜歡我的書可以不買。我寫文章也不是爲某個人寫,爲某個利益集團寫,我是爲自己而寫。財務自由支撐了我的寫作自由。
作者最大的裁判是時間,多少年後還有人在討論你這本書,我最開心的是在一個人家裏的書架上看到我的書。有人帶着我的書來讓我籤個名字,書是全新的我就寫自己的名字。書上有他做過的很多筆記,我還會寫上他的名字。
《慧見》:你曾說你這一代人對於財富天生有一種不安全感,你怎麼看待財富?
吳曉波:從小對貧窮和飢餓有記憶,我們家三個小孩,我是老大,我很早就會做飯。讀大學要學費都有三天開不了口,知道爸媽也沒錢,要麼被打一頓,要麼離家出走,那個時代很艱難。所以我們這代人對財富本身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但隨着財富多起來以後就沒了。現在怎麼找到有意義的事情就難了,我自己不怎麼花錢,從手錶到衣服都是企業送的,這些對我來講都不是重要的事。
《慧見》:那你覺得什麼是有意義的事情?
吳曉波:寫字讓自己快樂,這就是有意義的事。辦個公司讓員工們快樂,讓他們能夠在杭州買得起房子,給政府合法納稅,都有意義。
《慧見》:可以談一下家庭嗎?
吳曉波:公司是我太太管的,她負責日常管理。我管公司很少,會看週報,有問題我會直接打電話跟部門總說。業務、財務、後勤都太太管,股權上我跟她也是一半對一半。
《慧見》:萬維剛在《智識分子》裏說大多數人的人生都在大數據預測的模型裏,你是少數可以跳脫出大數據模型的異類之一,對於後浪實現不被大數據預測的人生自由有什麼建議?
吳曉波:其實每個人都在被大數據管控,但我認爲中國現在的階層固化相對還沒那麼嚴重的,雖然比我讀大學的90年代要剛性很多了,但還沒到日本歐洲這麼嚴重。判斷一個國家有沒有階層固化,就看一點,有沒有人敢創業。日本就沒人敢創業,階層就固化了,歐洲也是。中國每年還是有層出不窮的創業者前赴後繼。
《慧見》:對創業者有什麼建議?
吳曉波:所有創業者從第一天就要知道創業九死一生,要向死而生。因爲創業成功概率太低了。我們做過調查,中國現在每天1萬個創業企業,97%會在18個月內死掉。創業者大都是想改變世界,有了向死而生的終局思維,心態就會好。
《慧見》:對於今年沒有死的成熟企業家,你有什麼建議?
吳曉波:好好活着。善待自己的消費者。
(作者:包慧編輯:周鵬峯,視頻,鄭迪坤)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