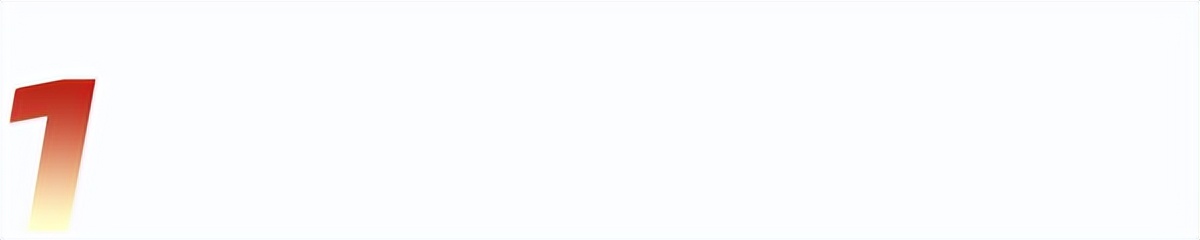漫过蒲草芦苇的目光(童年往事)
牟维列:漫过蒲草芦苇的目光——童年往事之十五
表弟和白露妹,杵在窗前的夕辉里,俺虽没陪着罚站,但也没少挨二姑的数落。
饭桌上的篮子,爷爷瞧着里面黑不溜秋的泥巴蛋问这是啥东西?烤焖的野鸭蛋,是外甥狗孝敬您的。二姑没好气地说罢,端上几碟菜,其中就有昨儿用鱼篓捉回的鱼虾。

爷爷背着手,走到表弟跟前,你这种让俺今晚少吃点,就是留着肚子吃你烤焖的野鸭蛋啊!哈哈,你可真行。嘿嘿笑的表弟,边笑边扭屁股,陪绑的白露妹眼里噙着泪。
领情的爷爷,一手紧着一个围桌入座,说着人是铁饭是钢,不让吃饭可不成。赶紧给你老爷剥几个野鸭蛋尝尝,焖不熟,还得扭你腚。白露妹趁二姑没留意她,翻了娘一眼。表弟剥着野鸭蛋上的泥皮说,个个熟,老爷尽管吃。
二姑给爷爷斟上酒,今儿着实编了一天席,吃过饭走走,早点睡。爷爷说,明儿上午就能编完席,下晌就和列儿回永安。二姑应着给爷爷夹菜,表弟桌下紧紧俺的衣,咬着俺的耳朵说:表哥,求老爷再住几天,等俺爹回来后,陪着老爷一块走不成吗? 俺明白啥意思,却无奈地摇摇头,表弟哀叹地说着,这顿胖揍早晚躲不过。
爷爷确实累了,从院外溜达回来,洗过脚,上炕不多会就鼾声如雷。然而,倒在炕上的表弟,翻来覆去摊起煎饼,啥时睡着的,梦中的俺不知道。
翌日晨,一觉酲来,昨儿作的业,全忘在脑后。刚从炕上蹦起的表弟,就嚷着饭后去粘知了。慢腾腾起来的白露妹,当头就是一盆冷水,能不能出院子,娘说问问你的腚。于是,表弟下意识地摸摸挨扭的屁股,还隐约有点疼。

天井里,爷爷趁着凉爽又编起席,这让俺突想起雨过天晴的翻地瓜秧。黎明前的钟当当当地响过,还在熟睡中的小叔,揉着眼爬起来,脸都顾不上洗,就匆匆下地干上一个时辰的活,再回家洗脸吃早饭。
列儿,那俩种咋还不出来?才刚起。盯着他俩洗脸,谁不洗就不让谁吃饭。快到院门时,突又转回身,要紧是你表弟,不听话,等俺回来,非把他的腚扭成青紫蓝不可。听着二姑恶狠狠的话,颜乐心语的俺,和善的二姑为何这样? 二十年后,表弟立业成家,辛勤地掌管着一个鱼、苇、鸭牧业,还在县城购置了益养福年的父母房,这才晓得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道理。
漂浮在塘面的几捆芦苇,干望着够不着。
不见俺拖芦苇回去,二姑匆忙来看是咋回事,见此情景,扯起嗓子喊表弟。被禁足在屋里的他,听到娘的喊叫声,像颇听话的小狗,嗖地跑到娘身边。没等二姑发话,扫一眼就知晓的他,扔下上衣扑进塘里,吓得几只白鹅忽闪着翅膀,躲到塘西的蒲草里。
将功补过的表弟,按理说应该禁足解除,可二姑把衣服甩给表弟,又指指屋,弟瞅了瞅俺,悻悻地回了房。
爷爷解开一捆芦苇,逐个用刀从尾削到梢,待到数捆芦苇削完,平摊在地上,用脚使劲反复地踩。踩完的芦苇,弧形逐个顿失,柔软的像刚擀出的面条。
削芦苇瓤是个仔细活,巧劲巧使,削过瓤的芦苇薄如纸,编起席,特好用。而用笨劲,削过苇瓤的芦苇,不仅不好用,还时不时地断; 编出的苇席,只能自己凑合着用,公家是不会收的。

削着芦苇瓤的动夫,爷爷对二姑说,小孩们哪有不作业的,骂也骂了,扭也扭了,关住人关不住心。俺连骂带扭,总比您女婿的打好,手下没轻重。上回打的您外甥,好几天都不能仰着睡,腚蛋子上一道道伤痕,伤疙疤十多天都没掉。俺看着心疼,可您外甥咋就没记性呢?小孩们都这样,拿起棍子吓煞,放下棍子自煞。
爷爷放下削完芦苇瓤的小扁刀,掏出烟荷包,边卷喇叭烟,边仰望行云匆移的天空,今晚无雨,也是个阴沉夜。
二姑听罢,也仰望了会儿天,又扯起嗓子喊。闻声奔出屋的表弟,叫着娘做啥。二姑冷冷地说,帮你老爷把削好的席子捆好,泡回水塘里,话落影儿走,去了饭棚。爷爷瞧着表弟泪溢满脸,心疼语暖地用老茧手,抹着他的泪,不哭不哭,俺说你娘了,她不会告状。
得知二姑不告他的状,表弟抹着鼻涕笑,抢着捆绑席子。午饭后的茶水是送行的酒,院门口的二姑挥手致远,却不知表弟躲在柴火垛的后面,正漫过篱笆,越过蒲草,目送挽留不住的老爷。

作者简介:牟维列,山东济南市人,生于1956年,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中区作协会员。已在报刊、网络平台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首)篇。
编辑:李勋修《青烟威文学创作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