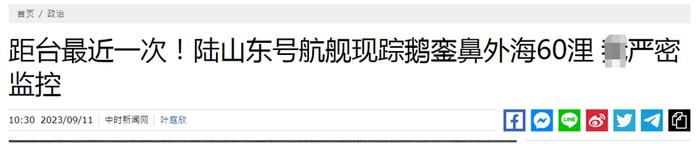解放軍着眼高原協同作戰駐訓練兵 克服了哪些困難?
來源:解放軍報
隨着越來越多的官兵頭腦開始 “越過雪線”,大家對於“體系作戰”有了更深的理解
演兵高原,同樣的戰鬥,不同的戰法,結果卻是一樣——

一次協同訓練,陸航部隊飛行員駕駛直升機搭載10餘名特戰隊員“深入敵後”。飛行員選好機降地點,特戰隊員離機後發現,周圍地勢平坦開闊,根本無法有效隱蔽。最終,因過早暴露行蹤導致行動失敗。
翌日再次協同,飛行員考慮到機降地勢的隱蔽性,選擇雪山中一處山谷進行機降,卻因山谷氣流紊亂險些造成安全問題,導致行動中止失敗。
覆盤檢討會上,特戰隊員歸咎於空中力量,空中力量則抱怨特戰隊員,雙方各執一詞:“選擇在地勢相對平坦、開闊的野外地域着陸,是出於對機降安全的考慮……”“選擇複雜的地勢,是爲了特戰行動的隱蔽……”

兩次協同,在每一方看來,都有本兵種本專業對勝算的考量。但因爲雙方都取了“極值”,沒有取公約數,均導致行動失敗。
“這個公約數,其實就是體系作戰思維。”此次覆盤檢討,兩支部隊的官兵都明白了同一個道理:雪線練兵,體系思維須臾不可或缺。
某特戰旅官兵談道:走上高原沒有現成訓練經驗參考,只好依據海拔由低到高循序漸進開展,把平原地區已成熟的訓練模式搬上高原。這一做法曾助推了戰鬥力的生成。那一年,該特戰旅傘降崑崙之巔,人員無一傷亡,裝備無一損壞,無論是跳傘人數還是訓練課目內容,都創造了歷史紀錄。

可訓練日久,他們發現雪線之上,各要素的戰鬥力都會因爲海拔因素打折扣——滲透速度會受限、火炮射角會縮小、飛行條件會更復雜……旅傘訓教員、一級軍士長王富強說:“高原高寒環境壓制了單打獨鬥的能力,倘若不能樹起體系思維、打通各個節點,打起仗來要喫苦頭。”
“訓練經驗就像圓圈的面積,經驗越多面積越大,圓的周長也就越大,觸碰到的未知領域也就越大。”該特戰旅旅長尚保雨說:“隨着訓練深入,原有作戰體系的瓶頸慢慢凸顯。”

“雪線之上,各作戰要素間的協同配合屢屢被‘絆住手腳’。發現這些問題,我們首先應當感到的是欣喜。”該集團軍領導介紹。他們連續4年深化高原練兵,首長機關帶各級指揮員反覆討論總結,梳理出一系列深層次問題,促使各兵種各專業摒棄老觀念、融成新體系。
隨着越來越多的官兵頭腦開始 “越過雪線”,大家對於“體系作戰”有了更深的理解:過去談體系,大多是力量的峯值之和,能夠達成“1+1>2”就是成功,現在看到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形成“1+1>N”的效應。
某陸航旅一級飛行員張尚年,帶領所在機組潛心研究高原條件下的體系戰法:逐一與指控控制要素、偵察情報要素、火力打擊要素、綜合保障要素展開極限條件下的協同、融合訓練,消滅體系盲區,打通了要素與要素之間的“結合部”。
“每個環節不再是單一獨立的個體,沒有高低、大小之分,都是體系作戰力量的一部分。”走下訓練場,張尚年告訴記者,儘管訓練難度大、要求高,但這種訓練方法更適應未來的打仗要求。
雪線之上,體系之變一點一滴發生,其目的是由量變引起質變。去年8月,該集團軍合成、炮兵、防空、特戰、陸航“五類火力”會師高原協同演兵,對體系作戰有了切膚的、更深的理解。
雪線之上的考場,逼着指揮員進一步實現頭腦的“跨界”,圍繞體系作戰隨機應變
對於某合成旅營長簡春來說,指揮步坦炮協同是他的拿手好戲——坦克以火力摧毀敵前沿工事、炮兵壓制敵火掃清障礙、步兵突進消滅有生力量,這一戰法在過去的演練中屢屢建功。

可第一次跨越雪線參加合成部隊實兵對抗,簡春驚出一身冷汗——步兵分隊體力下降,拖慢了進攻節奏;炮兵分隊由於高原特殊環境導致射表失靈,丟了準頭。倘若不是簡春臨機指揮坦克突入“敵方”前沿,爲炮兵分隊重新爭取了射擊時間,這一仗只怕凶多吉少。
“平原地區屢試不爽的體系戰法搬上高原卻‘水土不服’……”覆盤檢討會上,指揮員們感慨頗多:防空火力羣在地表荒蕪的高原環境不便僞裝,按平原地區的要求佈設陣地,勢必成爲顯而易見的“活靶子”;各型車輛裝備動力下降、故障率增加,機動不力常常延誤戰機……
在平原地區磨合已久、無縫鏈接的各單元各要素,在高原暴露出了新的體系“縫隙”。雪線之上的考場,逼着指揮員進一步實現頭腦的“跨界”,圍繞體系作戰隨機應變。
某重型合成部隊指揮員王慶波回憶起一場合成演練,大呼過癮:那次,王慶波率領縱深攻擊羣突進,遭遇“敵方”火力打擊後,他直接呼叫己方陸航力量提供空中火力壓制,同時調遣特戰分隊滲透敵後引導精準打擊“敵方”火力單元。

“不通曉雪線之上的體系之變,本已攥緊的拳頭,也會慢慢鬆開。”王慶波介紹說,集團軍領導帶領各級指揮員深入高原研戰研訓,根據戰場要求,不斷壓縮高原作戰指揮層級。如今,一線指揮員可將戰場情況直接上報集團軍“中軍帳”,即時協調、按需配屬作戰要素。
上山“找茬”,下山補短。這幾年,該集團軍組織十幾場高原指揮能力培訓,內容涉及高原機動指揮要點、兵種高原作戰特點等,堅決消除高原版的“五個不會”問題。
指揮員個人能力素質的提高,成爲作戰體系化建設的關鍵點。調整改革以後,集團軍編制體制重組,形成了以合成部隊爲主戰力量、兵種單元爲功能性作戰單元的作戰體系。諸兵種要素之間要攥指成拳,迫切需要指揮員深研高原體系作戰之要。

“山高人爲峯。在高原練兵,指揮員站得更高,就要看得更遠。”某旅火力單元指揮員賈俊輝舉例說明:高原作戰行動中,火力分隊需抽調小單元配屬到特戰分隊提供火力支援。而在更大的作戰體系中,特戰分隊又會配屬到合成兵團作戰,執行偵察引導、滲透潛伏、破壞襲擾等任務。“全新的作戰體系,全新的作戰地形,不僅需要指揮員精通本專業本崗位,還需要靈活應對不同環境、條件下的體系作戰要求。”
仗在高原打,能力在高原練。2017年,該集團軍首次將戰役指揮所設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域。2018年以後,集團軍訓練指導組常駐高海拔地區,帶動各旅首長機關整建制奔赴高原。集團軍領導說,戰役指揮機關駐紮海拔的變化,加速了實戰觀念的增強、作戰理念的更新、協同意識的萌生。去年,他們組織高原綜合演練,合成力量與特戰力量互爲要素協同、防空力量與陸航力量互爲條件對抗,各級指揮員帶部隊自主偵察、自主打擊、自主協同,一幕幕精彩戰鬥在高原輪番上演。
極端環境下,戰爭的勝敗更依賴於末端的“寸土之爭”,班長這個“兵頭將尾”成爲了重中之重
“再宏偉的藍圖,沒有一磚一瓦堆砌,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同樣,再強大的作戰體系,沒有一兵一卒落實,也不過是虛有其表。”在該集團軍,不少官兵都提到了這樣一個觀點。
一次演練,某旅火力支援連班長寶壽富帶領班組配屬特戰小隊行動時,因炮手“減員”無法及時提供火力支援,致使行動陷入僵局。而特戰小隊行動的遲滯,則引發了作戰體系的連鎖反應,致使後續作戰計劃被打亂……

演兵雪線之上,該集團軍領導敏銳地發現:在高寒缺氧的極端環境下,戰爭的勝敗更依賴於末端的“寸土之爭”,班長這個“兵頭將尾”成爲了重中之重。
爲此,他們針對這個“兵頭將尾”成立研究小組,引導班長們學習“跨界”知識,延伸體系作戰思維,而不只是打造一個簡單聽令執行的“模塊”。
在此之前,對於“戰法”“戰術”,班長們有些陌生:“堅決執行命令就好,自主發揮的空間並不多。”
對此,該集團軍區分戰術層次,對接完善行動方案,形成了多項戰法成果,構建起“軍-旅-營-連-班”五級戰法體系,釋放戰法創新的最大效能。

那一年,爲了克服雪地行軍難、射擊難、僞裝難等訓練難題,某旅“陽廷安班”第39任班長肖攀,帶着全班埋頭研究雪地環境下班戰術行動要點,填補了高原雨雪天氣班進攻戰術的空白。
風起青萍之末。某旅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線展開作戰行動,末端指揮員臨機接收指令、臨機搜索目標、臨機判斷性質、臨機選擇打擊方式,首次完成高原多彈種綜合攻擊和精確打擊。去年雪線之上第一仗,“陽廷安班”在體系對抗中擔負尖刀角色,不僅快速撕開“敵”防線,還伺機完成了目標定位引導火力打擊任務,爲最終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高原抬高了保障標準,雪線拉長了保障線路,必須探索既能獨立支撐又可互相支援的保障格局
翻過雪山、蹚過冰川、穿過河谷,突擊分隊在複雜地形上穿梭行進。
演練開始沒多久,負責伴隨保障的某旅工兵連連長陳文理就感覺有些力不從心。他坦言:“伴隨保障,不但要有十八般武藝,還得跟得上高原作戰節奏。”
氣溫驟降,河水湍急。面對接踵而至的“敵情”,陳文理率領官兵操作器材迅速架設浮橋,幫助突擊分隊搶先佔領陣地。

“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該集團軍領導說,高原抬高了保障標準,雪線拉長了保障線路,必須探索既能獨立支撐又可互相支援的保障格局。
近年來,爲破解高原寒區飲食保障難題,該集團軍研製和配發了摺疊“野營竈”、多功能副食平臺、野戰快餐生成系統等保障器材。他們還依託地方餐飲企業對食材進行粗加工,經分類、定量、整裝等流程後運送至配送點,由炊事分隊使用野戰炊事單元進行後續烹調。
高原戰傷快速救治有着很高的時間要求,他們緊貼前沿陣地優化保障,配備輕型救護車、器械、藥品等,不經補充即可獨立執行戰救任務;也可依託直升機,將衛勤力量投送到戰場急需的地方,完成相關急救任務。目前,他們已與各兵種進行了多次對接演練。

去年,某旅在高原參加演練,利用上級配發的軟件採集、甄別了大量一手數據,爲科學制訂保障方案計劃提供了可靠參考。集團軍保障部的參謀人員告訴記者,高原地形環境複雜,每一處都相差較大,臨機蒐集費時費力。“我們每打一仗、每到一地就完成一次數據擴充,數據的充實使得集團軍部隊的保障路徑更加精準,保障力量投入作戰的時間也相應壓縮。”
保障體系的優化,對作戰體系的釋能提供了有力支撐。一次高原應急救援行動,某旅在大距離機動中,每個梯隊配全要素、伴隨保障,連續機動近兩晝夜,翻越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隘口,成功完成救援任務。

(本文刊於《解放軍報》3月25日 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