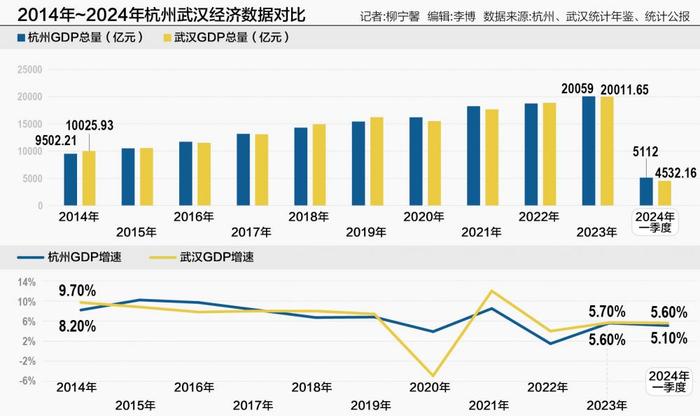蔡昉:伴隨人口紅利消失 高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的聯繫將不再緊密
原標題:蔡昉:伴隨人口紅利消失,高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的聯繫將不再緊密
“十四五”時期中國儲蓄率變化趨勢
世界各國平均國民儲蓄率水平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達到高點,隨後開始下降。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儲蓄率水平差異明顯:高收入國家的國民儲蓄率較世界平均水平低3至4個百分點左右;中上收入國家2018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8個百分點。東亞經濟體普遍較其他地區經濟體具有更高的儲蓄率,2018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0.1個百分點。
儲蓄的構成體現出如下特徵:其一,居民和企業等私人部門所產生的儲蓄是國民儲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約佔國民儲蓄的五分之四。私人部門的儲蓄相對更加穩定,尤其是2000年以後,公共部門儲蓄是總儲蓄波動的主要來源;其二,不同類型經濟體的儲蓄行爲表現出巨大的差異性;第三,近年來公司儲蓄率上升是一個國際性趨勢,居民儲蓄在私人部門的儲蓄份額相對下降。
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2008年達到52.3%的高點後處於下降趨勢。2017年國民儲蓄率仍然高達46.2%,較2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一倍有餘,也高於其他高儲蓄的東亞經濟體。
國民儲蓄率下行是經濟結構向更加均衡的狀態變化的過程,包含了積極因素。
政府儲蓄下降是自2008年曆史高點以來國民儲蓄下降的主要來源,但由於私人部門儲蓄在國民儲蓄中的比重更大,未來國民儲蓄率進一步下降將主要來自於私人儲蓄率的下降,尤其是居民儲蓄率的下行。
2017年居民儲蓄佔國民儲蓄比重達47%,“十四五”時期居民儲蓄的變化趨勢將對國民儲蓄的總體變動產生決定性影響。
由於工資性收入在過去十年已經經歷快速增長,且增速快於勞動生產率,預期“十四五”期間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並引起居民儲蓄率的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延續或出現反覆,將在“十四五”初期對疫情的衝擊產生消費平滑效應,降低儲蓄率。
“十四五”期間企業儲蓄率可能保持小幅上升勢頭。隨着行業集中度提升,大企業的儲蓄行爲推動企業總體的儲蓄水平,這些趨勢在“十四五”期間仍然延續。此外,中美經貿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產生的不確定性,將增加企業的儲蓄動機,以應對可能面臨的經營風險。
“十四五”期間的公共儲蓄率將繼續下降。人口老齡化所推動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支出持續增加,減稅降費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推動公共部門的儲蓄率持續下降;此外,疫情的影響將持續多長時間,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疫情後的經濟復甦伴隨着大量的公共支出,也會降低公共儲蓄。但隨着公共儲蓄在國民儲蓄中比重的下降,對國民儲蓄變化的邊際貢獻會越來越小。
人口結構變化或決定未來儲蓄率下降
中國2017年私人部門儲蓄率佔國民儲蓄的92.7%,其中45.4個百分點爲公司儲蓄,47.3個百分點爲居民儲蓄。人口撫養比上升及一系列結構因素的變化是居民儲蓄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勞動年齡人口的快速減少,成爲推動撫養比上升的主要因素,也是導致儲蓄率下行的重要推手。
我們將20~59歲的人口定義爲勞動年齡人口,人口撫養比將從2020年的0.68上升到2030年的0.88;如果按照國際上較爲通用的定義,將20~64歲定義爲勞動年齡人口,則人口撫養比將從2020年的0.54,上升到2030年的0.63。迴歸分析的結果表明,人口結構變化將可能成爲未來儲蓄率下降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除了人口結構以外,工資性收入的增長速度將有可能放緩。收入增速下降的預期,可能成爲儲蓄率下行越來越重要的推動因素。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既是擴大就業、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動力,也會刺激和擴大消費。因此,中國城市化對儲蓄率的影響可能與改革進程緊密相關,但很難判斷其對儲蓄率變化的影響方向;由於人口老齡化壓力越來越明顯,降低或至少不提高養老金的替代率是必然趨勢,這必然對人們當期儲蓄行爲產生影響,對儲蓄率具體的影響方向和程度,將取決於改革的內容和力度。
儲蓄率變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在中國表現出了一定的個性特徵。
首先,儲蓄率是經濟增長的促進因素,因此中國長期以來保持的高增長與高儲蓄率有着必然的關聯;
其次,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私人部門儲蓄對經濟增長具有更明顯的促進作用,政府儲蓄則不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這意味着,近年來政府儲蓄水平的下降,以及國民儲蓄中私人部門儲蓄率的上升,對於經濟增長有積極意義;
第三,經濟增長只對政府儲蓄產生影響,而對私人部門的儲蓄率沒有影響。更高的經濟增長容易產生更高的政府儲蓄。相形之下,私人部門的儲蓄行爲則取決於更長期的結構性因素,對短期的經濟增長並不敏感。
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儲蓄-投資之間存在穩健的相關性,而且越大的經濟體,投資和儲蓄的相關性越高。實證結果顯示,投資對儲蓄行爲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可能是通過高投資回報率而增加對資本品的需求,從而刺激儲蓄。不過,滯後的國民儲蓄率並沒有對當前投資率產生很強的影響,只有滯後一期的政府儲蓄對當期的投資有顯著影響,體現了在中國政府在投資行爲決定中的主動作用。
滯後的企業儲蓄率影響了企業投資,表明公司儲蓄在企業投資行爲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滯後的居民儲蓄率對企業投資也產生了影響,但有着4年的較長滯後期。這意味着未來仍然要通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使居民儲蓄更有效、迅速地轉化成企業投資。
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及時改變人口政策
儲蓄率的高低及其組成部分的變化取決於諸多因素,儲蓄率本身也並不必然要成爲政策干預的直接目標。但由於儲蓄率與諸多結構性指標相互關聯,可以通過儲蓄率的變化趨勢與決定管窺相關領域政策的改革方向。
第一,要形成與儲蓄率變化趨勢相吻合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以往的高儲蓄率與特定發展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人口紅利豐裕、投資回報率相對較高,必然誘導出以要素積累爲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而高投資回報率又會引發儲蓄的動機。然而,在人口紅利消失、要素積累推動的增長模式難以爲繼的情況下,高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的聯繫將不再緊密。相反,高儲蓄率可能通過擠壓消費,給經濟增長動力帶來不利影響。
第二,中國的高儲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支持政策的不足。
中國行將跨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但相較於高收入國家,中國社會保護的水平還遠遠不夠。較低的社會保護水平,必然需要居民通過提高個人儲蓄,以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加大向低收入羣體和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力度,提高社會保障的一體化水平,加大對公共衛生、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的支持力度,將有助於形成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儲蓄-消費關係。
第三,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將成爲導致儲蓄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但及時改變人口政策,實現家庭對生育政策的自主決策,有助於在未來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結構,減少儲蓄率波動。
第四,給中小企業與民營企業提供正規的金融服務。消除信貸等金融服務對不同類型企業的差別對待,有助於提高企業資金配置效率。
(蔡昉系CF40學術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都陽系CF40特邀成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