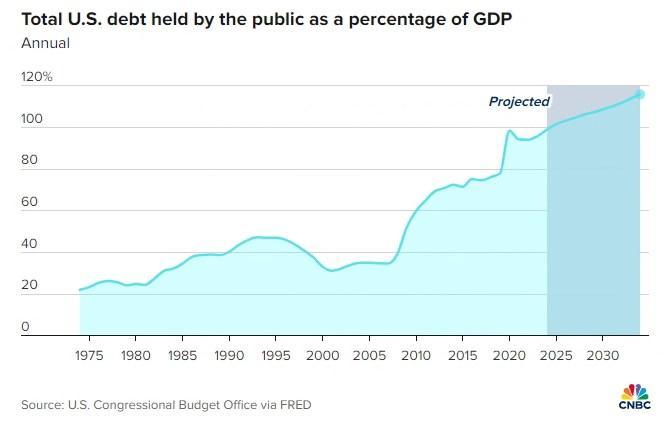GDP十強城市競逐國際消費中心:國家試點名單公佈進程加快
原標題:GDP十強城市競逐國際消費中心:國家試點名單公佈進程加快
4月30日,上海正式對外發布《關於加快建設上海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持續促進消費擴容提質的若干措施》(簡稱“上海《措施》”),引發外界格外關注。
不唯上海,今年以來長三角地區多個城市,例如杭州、南京也均已發佈各自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相關政策文件。同時,北京也有動向,4月28日北京市委常委會議專門研究了《北京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實施方案(2021-2025 年)》。
當前,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已呈“潮起”之勢。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包括上述4市在內,2020年全國GDP前十強城市均已提出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並且天津、青島、鄭州、長沙等萬億GDP城市也都有過提及,成爲多地方提升城市能級的“標配”。
各地熱情高漲,根本上與經濟發展格局優化相關,但也在頂層設計上獲得鼓舞。2019年國家發佈《關於培育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和2020年商務部啓動申報工作並“吹風”試點方向,均吸引了衆多城市的戰略眼光和行動。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也獲悉,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試點名單確定和公佈的進程正加快,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與近期多個城市陸續出臺建設方案或行動計劃形成呼應。
作爲各地眼中的“香餑餑”,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究竟意味着什麼?未來建設哪些將成爲重點?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注意到一點,目前,社會各界在討論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時,更多強調消費,但對“國際”和“中心”的討論較少。這或是解題關鍵。
發展國際化消費是長期命題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至少約有22座城市提及要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其中,2020年GDP前十強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武漢、南京全員“標配”,同時還有天津、西安、青島等12個經濟強市。
不過,各地“官宣”方式和推動進度不一。其中,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城市已在近期先後出臺了專門的政策規劃,例如《南京市創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三年行動計劃》《杭州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三年行動計劃(2021年-2023年)》等。
這些城市申報國家試點的可能性均較高。2020年3月商務部有關通知曾表示,要進一步指導相關城市編制完善實施方案,並要求申報城市要按3年左右時間安排相關工作。
此外,蘇州、鄭州、寧波等城市則有所不同。例如,蘇州尚未發佈有關方案,但在2021政府工作報告以及2020年有關消費政策中提及加快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鄭州類似,該市在答覆市人大代表及有關開放、消費的政策中提及要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需要指出的是,從蘇州、鄭州來看,當前兩市更多指向於從文化和旅遊消費示範引領的角度提升其城市消費勢能。此外,寧波提出的還暫爲“國際消費城市”,尚未升級加入“中心”概念,但精準明確要打造全國重要的進口消費品集散中心、配送中心和交易中心,從資源稟賦來看,寧波擁有全球貨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寧波舟山港。
“所謂‘中心城市’是有排它性的,多了就不是中心城市了。”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中心城市需要相關區域有相當的聚集力,沿海地區城市“強手如雲”,雖然發展程度高,但也不能都做“中心”。
白明認爲,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從國際化消費城市演變而來的,而對於有發展基礎的大城市來說,發展國際化消費是要長期推進的命題,不必特別執着於稱謂。
一場國際能級比拼賽
細看各地行動,提升步行街區及商圈品質、打造有地方特色的消費節、圍繞衣食住行遊等方面打造消費場景等,成爲了不約而同的舉措。對地方而言,如何通過有效改進消費環境、營造消費氛圍來促進消費,成爲了最直接、最現實的命題。
不過,多位受訪學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對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而言,促消費確實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絕不是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全部內涵。
以香港、新加坡等國際消費中心爲例,本地消費體量並不大,更多來自於開放型經濟下對人流、物流的集聚。“這些申報城市中有的是物流(消費品)集散地,有的是人流特別大,但國際消費中心要求人流物流能疊加,並有買賣全球的雙向性。”白明表示。
這也是對城市能級的綜合考驗。陸銘也認爲,商品和服務消費的“中心”城市,不僅流量規模大,也要有中心節點作用,吸引來自全國全球的消費流量。無論東京、新加坡還是香港、上海,每天吞吐大量商務人羣、旅遊人羣,這些都支撐着城市的消費市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最新發布的《措施》也提到,要打造全球新品首發地。
事實上,上述2019年發佈的《指導意見》也明確,申報試點城市時需說明本市在國際知名度、城市繁榮度、商業活躍度、到達便利度和消費舒適度等五方面的發展現狀。
根據目前被諸多城市用以衡量自身國際能級的GaWC榜單,中國大陸城市進入全球百強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重慶、武漢。
進一步來看,陸銘認爲,針對“國際”這一維度的理解,往往強調商品國際化,比如國際購物中心,這也是比較狹隘的理解,更關鍵的是要考慮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包括醫療教育文化等,是否都有具有服務於全世界的特徵。
陸銘還認爲,若要真正稱得上“國際消費中心城市”,還應在某些消費場景上能引領世界前沿,比如設計時尚、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消費品質在全世界具有影響力。
要看到消費的真正短板
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具體應該如何建設?按照商務部等14部門發佈的《指導意見》的思路,六大任務將成爲各個城市的“必修課”,具體包括髮展品牌經濟,吸引國內外知名品牌新品首發;發展博覽會、購物節、時尚週、消費展等國際產品和服務消費新平臺;促進傳統百貨店、閒置工業廠區向消費體驗中心、休閒娛樂中心等新型發展載體轉變等。
從已公佈方案的地方來看,對上述六大任務均有所承接。例如,上海《措施》提出,要支持首發經濟引領性品牌進商場、上平臺、進免稅店等。
同時,上海、成都、青島等多地都將購物節作爲一項重要舉措,包括以此延長商場營業時間,組織開展夜市、集市活動等,但從效果來看,各地存在一定差異性。
“在理解什麼是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之後,需要仔細考量,步行街等硬件場景和消費節等軟性場景裏到底要承載什麼東西?”陸銘表示,“我們提出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但對消費理解仍停留在普通的購物環節,沒有看到發展消費真正的短板在哪裏”。
事實上,上述《指導意見》也明確提出,圍繞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從原則角度要“把握我國主要城市在消費領域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破除體制機制障礙”。
陸銘指出,從我國來看,日常消費品市場隨着發展日漸飽和,消費面臨突出短板其實是文化、教育、醫療等方面,“這些在通常在購物節中是沒有的,也存在一定供給制約”。
此外,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也不僅侷限於經濟範疇,還伴有較強的社會關聯性。根據陸銘研究,排除了其他因素(如年齡、收入、教育水平)的影響後,沒有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的消費比本地城鎮戶籍人口低16%-20%,表明戶籍制度也會對特大城市的消費帶來制約。同時,一些城市“寬馬路、大街區”的空間結構也不利用人的來往,從而影響服務業的發展;一些希望用會展經濟撬動消費的城市,其會展中心周圍也還欠缺相關商業佈局。
(作者:朱玫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