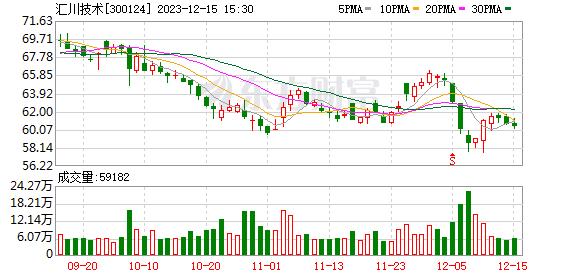柯達:從膠捲大王到破產重整
 還記得柯達嗎?哪個曾破產的老牌攝影公司,現要靠區塊鏈起死回生
還記得柯達嗎?哪個曾破產的老牌攝影公司,現要靠區塊鏈起死回生
柯達:從膠捲大王到破產重整
本報記者/吳清
編者按/ 這是一家百年巨頭企業,巔峯時期全球有近15萬名員工,業務遍及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佔據着全球相機和膠捲市場的半壁江山。但卻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短短10多年間迅速從巔峯滑落,留下無盡的錯愕和遺憾,它正是曾經的相機、影像的代名詞——柯達。
雖然已經遠離公衆視線焦點很久,但在2013年破產重整後,柯達一直還在努力轉型,先後嘗試跨界數位影像、手機、雜誌等多個領域,並在去年7月底又徹底火了一把,獲得了美國政府7.65億美元的國家貸款以創建柯達製藥公司。受該消息刺激,柯達股價三個交易日累計飆漲1480%,向上觸發熔斷達10多次,這重新引發了全球公衆對這家創造了無數第一的百年科技巨頭的高度關注和遐思。
如今,柯達依然在默默深耕中國及全球業務,《中國經營報》記者登錄柯達官網發現,柯達目前是一家專注於影像業務的高科技公司,主營業務包括印刷、噴墨、包裝、打印技術等,當然還有帶給柯達無盡榮耀的膠片業務。
柯達何以崛起並長盛不衰100多年?又爲何在進入新世紀的短短10餘年間迅速巔峯滑落?破產重整後的柯達還有機會重塑輝煌嗎?作爲全球經典的商業案例,關於柯達的故事依然值得細細解讀和深深回味。
1。歷史
堅持創新和簡單
柯達全名爲伊斯曼柯達公司,1888年由喬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創立,這位紐約銀行職員此前發明了一種幹明膠膠片,能極大降低拍攝門檻,當時感光底片都是溼片,拍照所需設備笨重而龐大,伊斯曼意識到他的發明有可能成爲當時最具創新力的變革。
伊斯曼從小就喜歡旅遊,還曾花了94美元買了一套照相器材,但令伊斯曼苦惱的是,當時照相機太笨重,相機像微波爐那樣大,還需要一個沉重的三腳架,全套裝備下來就是“整整一馬車”,而且機器操作起來也十分繁瑣。當時伊斯曼就暗自立誓:讓使用照相機像使用鉛筆一樣方便,讓每個人都能享受攝影的歡樂。
沿着這種思路,7年後,伊斯曼公司推出了第一部傻瓜型膠捲相機——柯達口袋式相機,一起誕生的還有那句著名的口號:“你只需要按動快門,剩下的都交給我們。”
1900年,柯達更是直接推出一款名爲Brownie的廉價簡易相機,成爲照相機小型化的革命性產品。其不到1美元的售價也使得相機真正走向了大衆消費者,當年銷量就高達15萬臺。
回顧柯達的崛起,無論是發明幹明膠膠片,還是推出傻瓜型照相機,都可以清晰地發現,正是準確順應和把握了攝影攝像的大衆化變革趨勢,滿足了消費者便宜、簡潔、好用的攝影需求,纔開啓了個人攝影革命的浪潮,也成爲柯達公司騰飛的起點。
對於化學,伊斯曼其實是一個門外漢,但實踐出真知,通過各種實驗,許多奧祕被他一一揭開。有一次實驗,伊斯曼從星期三一直做到星期六晚上,正好女朋友來電話約會,兩個人約定第二天上午10點鐘在車站會合。掛了電話後,伊斯曼又開始搞自己的實驗,結果因爲太專注,等他想起約會時早已錯過了時間。這樣的情況不勝枚舉,女友再也無法忍受,就跟他分手了。雖然伊斯曼心中很痛苦,但他依然堅持把發明繼續下去。
不過也正是這種專注和堅持,以及不斷試驗創新,伊斯曼研製出了卷式感光膠捲、口袋式相機等劃時代產品。
公司創始人這種對創新和科研的重視,也內化成了柯達的基因,柯達不惜重金招聘許多一流人才,鼓勵他們去探索、研製新產品。當時柯達的科研預算長期位列美國企業界前列,僅總公司就僱用了約2000名工程師和科學家從事各種研究工作,這也保障了柯達的產品技術在此後半個多世紀裏,長期保持行業領先。
公司剛起步的時候,柯達就曾召回一批有瑕疵的感光材料,並且向客戶全額退款,雖然當時並沒有法律規定必須這麼做,但是伊斯曼堅信,失去客戶的信任將給柯達造成更嚴重的損失。直到今天,這個理念還被公司嚴格地執行着。
另外,柯達在公司管理上也首創了很多有意思的管理制度,比如建議獎勵制。1889年,伊斯曼收到了一份普通工人的建議書,呼籲生產部門將玻璃窗擦乾淨。這雖然是很小的事情,但伊斯曼卻看出了其中的意義,他認爲這是員工積極性的表現,便立即公開表彰,並從此設立“柯達建議制度”。這個制度也一直保留至今並不斷完善,柯達職工因提出建議而得到的獎金,每年都達數百萬美元。
涓涓細流匯成大海,當1930年公司進入道瓊斯指數的成分股時,柯達已然佔據了世界攝影器材市場75%的份額,獨攬了超過90%的利潤。
柯達的這種興盛持續了整整半個多世紀,並在上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達到了巔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柯達,年銷售額超100億美元,長期位列全球最具價值榜單。
手握着最先發明的膠捲、相機等一系列領先技術,伴隨着一戰後美國成爲超級大國的長期國運,以及攝影普及進入千家萬戶的滾滾浪潮,佔據着天時地利人和的柯達,在影像拍攝、分享、輸出和顯示領域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開啓了膠片機時代的百年“柯達王朝”。
2。失敗
先行者的自我限制
時代拋棄你,連一聲再見都不會說。如果說,柯達的崛起是經歷了百年的深厚積澱和有跡可循的,柯達的墜落則十分迅速和突然,突然到可能連柯達自己都是懵圈的。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柯達的經營情況急轉而下,2012年初,柯達及其子公司在紐約提交了破產申請保護。從巔峯到破產邊緣,這家百年巨頭只用了短短10餘年時間,中間到底經歷了什麼?
目前,大多數的分析都指向了柯達在數碼時代轉型的落伍和失敗。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柯達本身還是數碼相機的發明者。1975年,柯達應用電子研究中心工程師史蒂芬·沙森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臺數碼相機,但也僅限於此。後來,沙森還曾爆料稱,當時公司內部的人對這個新發明的反應是:“它很可愛,但不要告訴任何人。”最終沙森未能讓公司相信自己的發明擁有巨大潛力。很快,它的競爭對手就推出了廉價的數碼相機,“柯達時刻”漸行漸遠。
13年後的1988年,柯達的老對手富士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商用數碼相機。本來佔據着技術、市場、資金特別是時間優勢的柯達,卻遠遠落在了後面。
是柯達缺少對即將到來的數碼浪潮的認知嗎?其實柯達早已認知並準確預測數碼相機終將取代傳統相機的趨勢甚至時間。當時柯達曾出過一份報告,表示數碼相機從商用逐步轉向民用,最終會在2006年前後取代傳統相機。這個時點與實際替代時間相差不過3年。
不過數碼相機並沒有得到柯達高層的高度重視。與此相反,他們擔心的是,這項新技術會蠶食傳統膠捲和膠片相機的利潤空間,所以他們對這項代表未來的技術做的是遏制甚至封鎖。1999年,時任柯達CEO喬治·費舍爾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坦承,柯達將數碼攝影視爲敵人,這個惡魔可能抹殺以化學爲基礎的膠片、相紙行業,而這正是柯達數十年來的盈利基礎。
當時的柯達內部充斥着唯利是圖、擁抱過時技術的想法,他們忘了消費者。爲此,消費者開始轉投向其競爭對手,因爲後者的技術讓消費者的生活變得更加方便。所以直到二十世紀90年代,尼康、佳能等後起之秀紛紛介入數碼相機領域並開始風生水起的時候,柯達依然在想着如何繼續延續其在膠片相機時代的榮光。
正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應時代成就了柯達的百年傳奇,逆時代潮流而動也能讓百年傳奇一瀉千里,傳統膠片行業時代的輝煌反而成爲埋葬這個百年巨頭的“溫柔冢”。
面對老對手富士和新玩家們的強勢崛起和自己每況愈下的業績,柯達並不是沒有嘗試過向數碼相機的轉型,並試圖扭轉不斷下滑的業績頹勢。
1995年,柯達公司做出發展數碼相機的戰略決策。1996年,柯達與尼康聯合推出DCS-460和DCS-620X型數碼相機,與佳能合作推出DCS-420專業級數碼相機。2000年,柯達立誓成爲數碼相機行業的領導者,並立下雄心壯志,到2005年,柯達數碼產品佔其銷售額的45%,佔其利潤額的27%。
2003年,柯達正式宣佈全面向數碼相機轉型。爲加速開拓數碼產品市場,還重組業務部門,將內部業務整合爲五大板塊:數字及膠片影像、商務印刷、顯示及零部件、醫療影像和商業成像。
但姍姍來遲的決策和猶疑不定的執行,讓柯達早已錯失了進軍數碼相機領域的最好時機,當時數碼相機市場基本已被富士、佳能、尼康等瓜分,且競爭十分激烈,而且柯達的數碼相機還採用代工模式,難以創造差異價值。
2000年以來,由於傳統相機市場被數碼相機快速搶佔,傳統膠捲市場開始迅速萎縮,每年以20%~30%的幅度銳減,2003年,柯達影像部門的利潤從2000年的143億美元暴跌至42億美元。柯達在數碼相機領域的發力,遠不能彌補傳統相機和膠捲兩塊主營業務的“坍塌”。
同時,即使是在向數碼相機轉型的過程中,柯達依然想固守傳統相機和膠捲市場的優勢,腳踏兩隻船。在歐美市場,大力拓展數碼產品;而將中國作爲傳統膠捲着力拓展的新市場。1998年,柯達先是通過著名的“九八”協議,將除樂凱外的中國傳統膠捲廠商拿下,幾年後更是直接入股樂凱完成對中國膠捲市場的整體收購。
其實,柯達對傳統膠捲時代的戀戀不捨也可以理解,這既來源於其在這個傳統市場的強勢和高利潤,也根植於其對“剃鬚刀與刀片模式”的依賴。
“剃鬚刀與刀片模式”最早源於剃鬚刀品牌吉列,主要指通過相對廉價的剃鬚刀架來吸引消費者,再通過持續地銷售高利潤的剃鬚刀片來實現高額回報。這個商業模式也被廣泛應用到了膠片相機、飲水機等諸多領域。
柯達出售低價的照相機,卻依靠高額利潤的膠捲、相紙和化學處理品來實現盈利,而彩色膠捲的高技術門檻,一直讓柯達舒服地享受着高利潤。而膠捲的高利潤正是數碼相機所缺失的,這也成爲柯達在數碼轉型過程中游移不定甚至一度想遏制數碼浪潮的根源。正如《福布斯》雜誌指出的那樣,柯達員工過於依賴這樣的理念,即他們的薪水與膠片、化學品以及相紙等耗材的銷量息息相關。他們認爲,賣不出去耗材,他們就沒有利潤。
自2004年後,柯達幾乎每年都在虧損,哈佛商學院曾在一份案例中測算,柯達每賣一臺數碼相機就會虧損60美元。相關數據顯示,柯達只有2007年是盈利的,因爲那年它出售了大量資產。
2009年,柯達停售歷經74年的35毫米彩色膠片;2011年,柯達僅能勉強維持市場份額,並艱難爲職工發放鉅額撫卹金,柯達股價跌幅超過80%;2012年,柯達向紐約一家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3。 轉型
總爲他人做嫁衣
這種猶疑不定也延續到了柯達後來的多元化轉型。
膠片行業的化學屬性與醫藥存在天然的聯繫,柯達也曾多次向醫藥行業轉型。早在1988年,柯達就耗資 51 億美元收購了斯特林(Sterling)製藥公司,時任柯達CEO錢德勒表示,“這次收購將加速我們進入1100億美元的全球製藥市場。”不過僅過6年,柯達就意識到自己的戰略可能錯了。本以爲藥品利潤高,自己多年生產化學品,二者可以產生協同效應,但柯達並不具備研製創新藥的能力,此外,也無法低成本生產仿製藥。
柯達再一次戰略轉型開始是在1994年。公司先是將作價 16.75 億美元,斯特林的處方藥業務賣給了賽諾菲;接着繼續將斯特林剩餘股份和非處方藥業務以29.25億美元打包出售給了史克必成公司,後者與葛蘭素威康合併成爲了葛蘭素史克。此後葛蘭素史克將斯特林的部分非處方藥業務轉手給了德國拜耳公司,成就了後來大名鼎鼎的拜耳阿司匹林。
結果很富戲劇性,柯達這一路出售轉型卻促成諸多製藥巨頭的崛起,總歸是爲他人做了嫁衣裳。如今賽諾菲是全球第五大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更是全球前三的製藥公司。拜耳則成爲了阿司匹林的代名詞,據統計現在全球每年生產約合 1000 億片阿司匹林。
拜耳公司、3M公司和富士等巨頭也都曾經歷過像柯達那樣的轉型,不過它們如今都成功地從精細化學品行業轉型到醫藥業。自1986年起,富士陸續收購了幾家醫學診斷成像公司、生物醫藥公司。財報顯示,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富士在醫療保健及高性能材料業務上全年營收爲93.96億美元,佔總營收的44.2%,成爲公司新的盈利支柱。
2013年,柯達脫離破產保護,重組爲一家小型數位影像公司,重新融資上市。或許是重新審視了過去自身發展的侷限之處,柯達開始不斷嘗試跨界轉型。
2015年初,柯達推出了SP360運動攝像機,對標GoPro。而且率先使用了VR技術,是市面上僅有的360度全景攝像機,但由於當時VR概念尚未受追捧,柯達的技術也不成熟,最終口碑、銷量都不盡如人意。反觀GoPro在運動相機的領域,猶如當年的柯達,基本已經做成了這個品類的代名詞。
2016年,柯達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智能手機,2017年又推出了第二款,不過此後再沒推出新產品,手機業務如今早已退出柯達的主營業務範疇。
此後,柯達還曾做過藝術雜誌,進軍時尚圈,推出柯達聯名服裝和滑板品牌,不過這些更像是玩票性質和宣傳噱頭,後來多以不了了之收場。
在經歷眼花繚亂的轉型嘗試後,柯達最終還是迴歸自己的老本行,並聚焦印刷影像領域,2019年,柯達淨收入12.42億美元,其中近70%來自柯達的打印系統業務;研發投入爲4200萬美元,同比減少12.5%。2020年柯達營收10.29億美元,淨虧損5.41億美元,此外,公司的鉅額債務將在2021年底到期。這樣的業績表現也被業內指出,一定意義上已喪失商業想象空間。
而它的老對手,富士膠片經過市場摸索尋求多元化的發展,將其最早的傳統膠捲、數碼相機、數碼影像等業務板塊調整爲醫療生命科學、高性能材料、光學元器件、電子影像、文件處理和印刷六大重點發展事業,傳統膠捲業務在公司整體收入中的佔比僅2%。醫藥、高性能材料等成爲富士新的盈利增長點,公司也名列世界五百強第287位。
經歷了那麼多,柯達還活着嗎?可能很多人聽到這個久違的品牌會有這種反應。
柯達確實還活着。其實柯達在2013年重組後一直在謀求轉型,2020年7月底還傳出獲得美國政府7.65億美元的貸款,用於生產“已長期陷入國家性短缺的藥物原料”,而讓長期沉寂的股價出現飆漲,也讓外界開始期待,這家百年巨頭在歷經7年多的坎坷跨界路後,能否實現華麗轉身,再續“柯達王朝”的輝煌?
柯達首席執行長康丁尼扎還表示,在獲得美國政府貸款後,未來原料藥業務預計將佔到公司營收30%~40%,不過這個暢想很快被緊接着的一則消息打斷,由於貸款協議受到“不法行爲的指控”,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2020年8月初發表聲明稱,暫停授予貸款,直到相關監管機構有明確的調查結果爲止。去年12月初,美媒消息曾稱,監管未發現柯達有不當貸款交易。
對相關審覈及醫藥業務進展,柯達方面並沒有回應記者。不過記者查閱柯達官網發現,柯達目前的主營業務聚焦影像印刷,並未涉足醫藥。記者在電商平臺上搜索“柯達”發現,柯達目前的產品主要包括膠捲、數碼相機、照片打印機、掃描儀、沖印服務等攝影類;存儲卡、U盤等數據存儲類;無線耳機、藍牙音箱等影音類,也未發現醫藥相關產品,且其中的數碼相機等多爲代工生產。
1997年2月柯達市值最高達310億美元,如今股價常年徘徊在1美元左右,市值也只有巔峯時期的百分之一。雖然近期股價有所反彈,但總市值依然在6億美元附近徘徊,與巔峯時期相去甚遠。
從目前看,柯達依然在積極探索謀求轉型,能否成功依然有待市場檢驗和消費者的認可。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從體量、業務等來說,柯達早已不是原先的那個柯達了。
觀察
百年巨人的倒下
歷史上,成功多年的巨頭往往會沉醉於過往的輝煌,對過往成功的模式和經驗會有很多依賴,面對行業危機需要轉型時,總有更多的牽絆和瞻前顧後,乃至抗拒。
但時代和科技的發展必然會帶來新的技術和產業模式,固步自封往往意味着落後甚至出局。“剃鬚刀與刀片模式”曾給柯達帶來巨大成功。由於彩色膠捲的高技術含量,柯達也一直舒服地享受着膠捲時代的高利潤。
對於最早發明數碼相機的柯達來說,雖早已認識到數碼相機的重要性,也多次努力向數碼相機轉型,但結果不盡如人意,這裏有柯達對“剃鬚刀與刀片模式”的高度依賴,也有源自公司對轉型認知策略的偏差。
儘管嘗試過多次轉型,但是柯達始終留戀於膠捲時代的“高利潤”,在這場席捲全球的數碼革命面前左右搖擺、猶疑不定。它既未能斬釘截鐵義無反顧地全速駛向數碼時代,也未明晰多元化方向並堅持到底。它始終像在玩蹺蹺板,試圖在傳統膠片和新興數碼產品的發展中保持平衡。
同時,由於缺少清晰的戰略方向,柯達在多元化業務上也搖擺不定,即使1990年代以來,柯達每年約投資800億日元於醫藥、手機、噴墨打印機、Photo CD等諸多領域,但一直未能在新業務上真正實現突破,最終導致柯達的日薄西山。
柯達不是沒有看到行業的變化,而是長期居於膠捲行業領軍企業的地位成爲其經營改革的羈絆,阻礙了它的轉型。同樣的危機,截然不同的結局,或許柯達相比富士,只是缺少了背水一戰、壯士斷腕式的決絕。
柯達直到破產的那一天,生產的膠捲質量都是最好的,但那又怎樣,世界不再需要它了。正如當年,柯達順時應勢的崛起。
(本版文章均由本報記者吳清採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