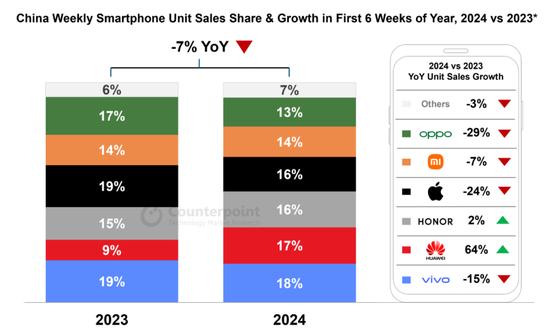吳孟超院士的肝膽人生
原標題:吳孟超院士的肝膽人生
(健康時報記者 張赫 尹薇 趙苑旨)“過了今天,我就再也看不見他了。”吳孟超的接班人、著名肝膽外科專家、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教授沈鋒在雨裏一一送別親友,說完這句,眼睛就溼潤了。他說,跟在老師身邊,已經37年了。
告別廳裏,吳老的親人站在遺體的左側,和悼念的人一一握手互致哀思,幾個女兒的眼睛已經哭得紅腫。
5月26日,上海小雨。鮮花鋪滿送別的路。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肝臟外科的開拓者和主要創始人、原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吳孟超身蓋黨旗,穿着愛了一生的軍裝,和思念的人做最後的告別。

上海市民自發來給吳孟超院士獻花,很多人駐足緬懷。健康時報記者張赫攝
不捨得放棄任何一個病人
從北京趕來的徐富榮拿着一張和吳孟超院士的合影,在遺像面前久久駐足。
很多年前,徐富榮因工作認識了吳孟超。他認真看着每一束花上的留言,轉頭告訴健康時報記者,他曾把身邊很多肝癌患者“推”給吳老,起初戰戰兢兢,怕大牌專家嫌麻煩。但沒想到,幾十年來他推給吳老近100個患者,硬是一個都沒拒絕過。
“不管是農民還是工人,越貧困的患者,他越是心疼。”徐富榮說。
吳孟超對患者的好,就像他眼睛裏的光一樣堅定且不容挑戰。他從不捨得放棄任何一個病人的決心,容不得半點“勸說”。
今年快60歲的王仁華在提起吳孟超時,瞬間哭了起來。退休前,王仁華是上海青浦醫院的管教員。
“2012年,一個病情很嚴重的服刑患者在上海做了手術,但預後一直不好,就幫忙輾轉找到了吳老。”王仁華告訴健康時報記者,那天她帶着保外就醫的服刑男孩,帶着術後檢查結果找到了吳孟超,在辦公室裏,吳孟超用滿是皺紋的手一行行的指着結果,一個字一個字的去看、一點點解釋病症的原理和預後,然後告訴患者,你要做一個“三好學生”。
看到王仁華和男孩滿臉錯愕,吳老笑着說,你要做我的“好學生”,聽我的話,就會健康。
講到快50分鐘的時候,護士推門提醒,時間久了,要注意休息了。看到倆人不好意思的起身要走,吳老馬上提醒護士關門出去,然後繼續耐心講完。
在王仁華帶着服刑男孩告別後走到走廊轉彎時,二人聽到吳孟超很嚴肅地和護士說了一句:犯人也是人,也有好好活下去的權利。
“聽完那句,小夥子眼淚就掉下來了,手裏攥着吳大夫手寫的預後方案,邊走邊哭。”王仁華說,那一年, 吳老90歲。
出了名的能爲患者省錢,也是吳孟超的一大特點。 “醫生應該想怎樣解決好患者的病,讓全家人都高興,不能再給病人添麻煩,再從患者口袋掏錢。”他對科室醫生說:“我們要多用腦和手爲患者服務,器械用一次,‘咔嚓’一聲1000多塊,我吳孟超用手縫線,分文不要。”
如果病人帶來的片子已經能夠診斷清楚,絕不會讓他們做第二次檢查;同樣如果B超能夠解決問題,絕不建議他們做費用更高的CT或核磁共振;給病人開藥,在確保診療效果的前提下,儘量給病人用便宜的藥。不僅如此,他總要趕在病人麻醉前,意識尚清楚時去問候,幾句寒暄就會讓病人更安心地在麻醉中睡去。
對於吳孟超和患者之間的故事,編寫《吳孟超傳》的上海教育出版社編審方鴻輝先生曾在多個場合講過這樣一個細節:
2018年2月6日,他去看望吳孟超院士,聊到肝癌的外科手術、建立病人隨訪制度以及病友俱樂部等話題時,吳老興致勃勃地講了一個很有意味的故事:
大海退潮後,海邊的沙灘上留下很多被擱淺的小魚,在烈日下等待它們的似乎只有死亡。但有一個孩子彎下腰一條一條地撿起這些小魚,重新扔進大海。旁觀的一位大人對這個孩子說:“那麼多小魚你撿得過來嗎?一條小魚而已,有誰會在乎呢?”孩子一邊不停地往海里扔魚,一邊說:“你看,這一條在乎,那一條也在乎。”
在吳孟超看來,這些小魚如同患了肝癌的病人,被擱淺的小魚,太陽一曬,難逃死亡。而吳孟超的手,總有一種改變命運的力量,一個都捨不得丟。
幾十年來,病人的來信,吳老一定親自拆閱、親自處理,連諮詢信和感謝信,他也從不讓家人和祕書拆,他說這是對病人的尊重。收到的感謝信,凡是感謝他的,就悄悄地放在一邊,表揚和感謝其他醫生護士的,他一定會在信封上寫明:予以表揚。
2012年,吳孟超被評爲年度感動中國人物,頒獎詞上這樣寫道:
60年前,吳孟超搭建了第一張手術檯
到今天也沒有離開
手中一把刀,遊刃肝膽,依然精準
心中一團火,守着誓言,從未熄滅
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馬
要把病人一個一個馱過河
99歲的吳孟超,就這樣,用近一個世紀的風霜,馱起了1萬6千個患者的命和家,更扛起了中國肝膽事業生生不息的希望。
“我不就是個吳孟超嘛!”
5月25日晚上10點半,連斌剛剛從醫院爲吳孟超設置的悼念廳回到家。對他來說,吳老是一種精神,更是一股力量。
連斌跟吳老交集甚多。2005年到2013年,連斌是海軍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副院長,在那期間,吳孟超擔任院長。
在20世紀90年代,連斌是原第二軍醫大學校辦校長祕書,吳孟超是時任副校長。在連斌的記憶裏,那時吳老70多歲,好像和現在沒什麼兩樣,總是精力過人。
“有一次學校統計,吳老一年出差60多次,平均一個星期1-2次。”連斌告訴健康時報記者,這個數字,一時間在學校引起熱議。
後來他碰到吳孟超的助理,聊起高頻率的出差後回來直奔手術檯,老人會不會身體喫不消,助理笑着說,每次有人提醒,吳老都要說一句:“我不就是這樣一個吳孟超嘛,就是愛手術,有什麼大不了的?”

2017年1月28日,大年初一,吳孟超院士照例前往醫院病房看望患者,同時送上新春祝福。這是他長期以來每年大年初一的習慣,也成了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的傳統。中新社殷立勤攝
5月26日這一天,已經77歲的上海東方肝膽醫院肝膽醫院護理部原主任陸翠玉一早就冒雨來到了告別廳。滿頭白髮的陸翠玉和老同事一起,小心翼翼的整理着衣衫,她想和吳老的最後一次合影裏,留下最乾淨的樣子:吳老是愛乾淨的。
陸翠玉回憶,吳老一直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無論手術難易,吳孟超都要陪病人查看實時超聲波,仔細琢磨腫瘤位置,制定各種預案,不放心的病例還要召集弟子們會診後方才上臺。很多人會說,這樣太累了,身體喫不消,吳老會馬上生氣的抬頭:“我瞭解我自己的身體,有什麼大不了?”
2010年那一年,88歲的吳孟超主刀完成的手術就有190臺。有人記錄過他和護士之間這樣一段對話——
吳孟超:明天有什麼手術?沒有人排我。
護士:休息休息吧。
吳孟超:排吧!怎麼搞的一個都沒排。你去找一個。
所有學生都知道,吳孟超愛手術,也急着在有限的時間裏,多救人。
在2018年7月14日播出的《朗讀者》中,96歲的吳孟超如此自白:“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職。”直到2018年,96歲高齡的吳孟超依舊保持着每週門診、每年約200臺手術的驚人工作量。
把吳孟超請進演播室,董卿的感慨是從一雙手開始的。這雙手天賦異秉,它在肝臟的方寸之地創造生的希望;這雙手又異常細膩,它以截然不同於同齡人的敏銳與穩定,將萬千病患托出病魔的沼澤地。
當鏡頭給到吳孟超雙手的時候,這位老人還是下意識的侷促了起來:一雙手放在膝蓋上,右手食指、無名指的關節,因經年累月與手術刀並肩戰鬥,它們都異於常人。其實,觀衆看不見的還有吳老的腳趾,因爲長時間站立,它們也變形了。
節目中,吳孟超用一句話帶過自己在肝臟方面的60餘年時光,“因爲中國也是肝病大國,死亡率很高。那個時候,肝臟沒人敢開。所以我就攻肝臟,做標本研究,然後慢慢做臨牀,以後建立起來了肝膽外科。”
節目現場請來了吳老曾經的病人甜甜。當時她肚子裏的肝臟腫瘤足有一個籃球大小,許多醫生給她建議肝移植,但肝移植費用高昂,走投無路之時,姑娘和家裏人來到上海,吳老發現,姑娘的腫瘤可以切除,肝不用換。
2004年,吳老已經82歲了。有些年輕同事勸他:這麼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了,萬一出了事,你的名譽就沒有了。吳孟超回答:“名譽算什麼,我不過就是一個吳孟超嘛!”
2021年5月26日,在吳孟超遺體告別上,甜甜母女在看到吳老後痛哭到不能自已。如今,甜甜也是一個醫護工作者。
就是這樣一個吳孟超,創造了中國醫學界乃至是世界醫學肝膽外科領域的無數個第一;他翻譯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臟外科入門專著;他製作了中國第一具肝臟血管的鑄型標本;他創造了間歇性肝門阻斷切肝法和常溫下無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葉切除手術;他切除了迄今爲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綿狀血管瘤;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鏡下直接摘除肝臟腫瘤的手術。
他不僅僅只是一個吳孟超。
最對的3個選擇和2個遺憾
在連斌的記憶裏,吳老很少提起自己的私事兒,但時常把“三件事兒”放在嘴邊。
“第一件事兒是抗日期間回國,第二件事兒是入黨,第三件事兒是當一個軍人。”連斌告訴健康時報記者,吳老每次說起這三個最對的選擇時,都仰着頭擺着手,這不僅是三個選擇,更是他一生的驕傲。
戰亂期回國,他看到了一個滿目瘡痍需要自己去守護的故土,所以堅定了守護一輩子的心願;黨旗前宣誓,所以從艱難到手術檯都需要自己搭的日子走到後來21世紀的繁華時,他一直牢牢守着初心,他經常說,共產黨人,要喫得了苦,要時刻懂得讓,把好的,留給人民;入伍從軍,一身戎裝。這以後,吳孟超對患者的愛,更“名正言順”了,他說,軍人生來就是保護人民的,軍醫本來就是來救人的。
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不上手術,白大褂裏,他穿的保準兒是軍裝。
99歲的人生,很難百分百的圓滿。
如果說,吳孟超負過哪位病人,有且僅有一位——那就是他的父親。
“父親是膽囊結石、膽管結石,後來黃疸去世了。我自己是學這一行,不能給我父親醫治,所以我很痛心。”在央視《朗讀者》節目中,96的吳孟超提到父親時,滿眼遺憾和愧疚。
後來,吳孟超向組織請示,回了一趟馬來西亞。
吳孟超院士是馬來西亞歸僑,在十八歲時爲了抗日毅然回國參加戰鬥,從那之後就沒能再見過父母。
“那次我到墳上去看他們,就在爸媽的墓前,我說:媽媽爸爸,我已經爲國家做了一點事情,現在工作還是很好。”然後哭了起來。
吳孟超的接班人、得意的弟子沈鋒告訴健康時報記者,這是吳老畢生的遺憾之一。
除了這個心願,另一個吳老在晚年經常掛在嘴邊的就是:想徹底消滅肝癌。
爲了這個願望,吳孟超整整奮鬥了一生。
1997年,吳孟超親自到德國,想把一位他八年前送走的學生找回來。這個人就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國家肝癌科學中心主任王紅陽。
5月25日深夜,王紅陽遲遲不能入睡。因爲再過幾個小時,親手把她培養起來的老師吳孟超就真的“走了”。那天晚上,她告訴健康時報記者,自己永遠忘不了吳老到德國的那天:漫天大雪,吳老162的身高,喫力地走向她,見面後只說了一句:回到肝膽醫院(上海東方肝膽醫院)吧,以後我還要在中國建肝癌中心。
王紅陽後來毅然決定回國。因爲對肝膽事業的一致狂熱,王紅陽在德國科學院的導師、諾貝爾醫學獎6次提名的獲得者也和吳孟超成爲了摯友。後來長期和中國保持學術研究的合作。
“這條路太遠了,等到肝癌能治癒的那一天,我相信吳老看得到。”王紅陽堅定地說,她會和吳老的全部學生、和自己的學生一起,一直走下去。
“讓他生氣的事兒,太多了”
“那時候我們都是小孩子,吳老每次出差都會給我們帶很多好喫的,但後來去到他家裏才知道,一個大院長的家裏,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陸翠玉回憶,吳孟超最容忍不了的幾件事兒之一,就是收紅包,吳老一生清貧,從未對錢有過任何慾望。
學生嚴以羣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追憶,在他看來,這就是真實的老師,生氣的事兒很多,可愛而又偶爾可“怕”。比如手術室的空調溫度過低過高,他一定會不高興,怕費電也怕患者不舒服;洗手間的洗手液盛得太滿會流出來,他也要指出;下班走廊裏燈火通明,他要自己巡視一圈,挨個關掉,動不動還要扣責任人“敗家”的帽子;此外,還有開會不讓用一次性紙杯喝水,打印會議材料只用半張紙的要求。。。。。。
吳老除了愛不釋手的軍裝,很少買自己的衣服,那兩套西裝,也是穿了十幾年。每天只喫食堂,基本上每天都要喫半根玉米,喫不完的飯菜絕不多打一兩。如果看到周圍有人浪費,他一定嚴厲的呵斥。
96歲那年,吳孟超在央視的節目上借讀本寄語後輩:“孩子們,讓別人去享受‘人上人’的榮耀,我只祈求你們善盡‘人中人’的天職。某些醫生永遠只能收到醫療費。我願你們收到的更多——別人的感念。”
吳老的多位學生告訴記者,每天晚上深夜,都是老師處理信件和論文的時間,他對論文看得十分細緻,哪怕是標點符號也不放過。從雲南特意趕到上海的陳訓如告訴記者,老師發過的最大的火兒,就是因爲論文數據不準確,也是因爲如此的嚴格要求,吳老的學生,如今才能支撐起半個中國肝膽外科。
這個世界,他是留戀的
“2020年1月18日,我像往常一樣起給吳老拜年,不一樣的是,去年這最後一次見,是在長海醫院的病房裏。”徐富榮指着懷裏捧着的和吳老的合影說,也是在那天,他突然意識到,這個從不怕死的老人,開始留戀了。
徐富榮回憶,那天上午,他帶着鮮花來到病房,像往常一樣陪吳老聊天,說說這一年都幹了啥。
但是就要起身告別的時候,吳孟超突然拽住了徐富榮的胳膊,滿眼都是不捨得說,富榮,你坐下來,我們合張影吧。
聽完這句,徐富榮愣了幾秒,他知道,已經98歲的吳孟超開始留戀去看他的每一個人了。後來,吳孟超的大女兒爲兩人合影,照片中,吳老穿着病號服坐在病牀上,手挽着徐富榮的胳膊,笑的像個孩子。
在很多場合,吳孟超經常笑着說:人嘛,都有人生終點的,每一天都過得有意義就夠了。但也許是心裏還有未完成的願望,晚年的吳孟超,越來越留戀了,留戀每一個人,留戀這個世界。
連斌也回憶,自從2016年他退休,見到吳孟超的機會就變得少了。2018年,他被蘇州一家公立醫院返聘繼續當院長,會定期從蘇州回上海專程看吳老。吳老總會說:“小連,等我去蘇州看你。”
2020年最後一次看望吳老的時候,臨走前,吳老又說了一句:小連,等我去蘇州看你。
“我連忙說好,拽着他說,希望他快點去。但一出門眼淚就掉下來了。”連斌說,他知道,吳老舍不得他了。
在告別儀式開始後,沈鋒一直站在大門外的甬路盡頭,和每一個悼念完的親友一一拜別。
間隙,說起吳老生前讓他最心疼的畫面,沈鋒的眼圈瞬間紅了:“握着我的手說100,我明白是說百歲,他在世上每一天都想着工作,痛惜的是距百歲差了99天。”說完這句,淚水夾着雨水順着臉頰流了下來。看到有兩位老人被攙扶着走出告別廳,沈鋒彎着腰,急忙淋着雨跑去扶起了他們。
上午10點28分,家人抱着吳孟超遺像緩緩走出告別廳。靈柩被海軍儀仗戰士抬進了靈車,衆人哭喊着:吳老一路走好。
而此時,吳孟超的幾百個學生均圍繞在靈車前後,他們從海內外回家,爲了見吳老最後一面。
時光回到幾年前,一次手術後,疲憊的吳孟超告訴護士長:“如果我有一天倒在手術室,不要慌張,記住幫我擦一下。你知道我是愛乾淨的,別讓人看見我一臉汗水的樣子。”
國際歌的旋律依然迴盪在雨裏。中國肝膽事業,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