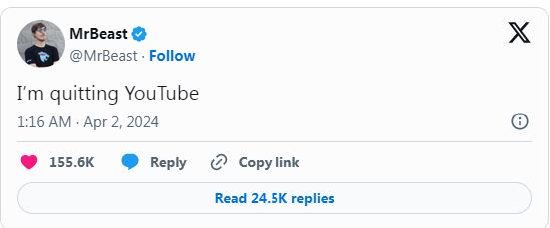全球每天傳播30億張圖片帶動經濟也暗藏危機
作者: 吳丹
[ 2019年,Youtube上每分鐘上傳的視頻超過500個小時,每天是72萬小時,超過80年。 ]
每天,你有多少時間在刷手機看電腦?每天,你會在網站上傳播或是瀏覽多少圖片?
在北京紅磚美術館5月28日開幕的“圖像超市”展覽現場,你會得到一個具象的答案——令人窒息的圖像鋪天蓋地充斥視線。從腳底到頭頂,直至天花板,密密麻麻的圖片堆疊出一個無法喘息的空間,站近了,仔細看,裏面有藝術家的家庭照片、廣告橫幅,以及他看過的各種屏幕截圖、訪問過的網站信息等。
這是美國藝術家伊萬·羅斯的作品。從二女兒出生以來,三年時間裏,藝術家瀏覽過的所有圖像,一次性累積爲這件名叫《自你出生》的龐大作品。
這些海量圖像不僅是藝術家個人所見,也是互聯網時代每個普通人日常能見到的圖片數量。
“社交網絡每小時傳播的圖片超過1億張,每天超過30億張。”該展主策展人、布朗大學比較文學和人文科學教授彼得·桑迪說,數字圖片正以連續且超高速率的方式傳播,“2019年,Youtube上每分鐘上傳的視頻超過500個小時,每天是72萬小時,超過80年。相當於每天我們產生的圖像,超過了一個人一輩子的時間。”
桑迪認爲,世界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圖像流動”的時代,一個圖像生產過剩的時代。尤其在疫情蔓延的這一年,圖像的大肆氾濫更是呈幾何級增長。
千萬“點贊”背後的雙手
紅磚美術館入口處的下沉廣場,一輛閃亮的鍍金購物車在轉檯上不停旋轉。上方一塊與互聯網相連的巨型顯示屏上,計算機ASCII碼組成一隻手,實時對應世界各地股票市場指數變化。
購物車是消費社會最顯著的標誌,瑞士藝術家西爾維·弗勒裏用頗具諷刺的手法,讓普通的購物車享受了藝術品般的尊貴待遇。
與此相呼應的,是德國攝影師安德烈斯·古斯基的巨幅攝影作品《萬德城》。作爲歐洲頭號電子產品零售商,萬德城在鏡頭裏呈現出一種工廠式的標準化,五彩斑斕的熨斗、咖啡機、吸塵器擺放得整整齊齊,堆積出豐富而眩暈的視覺感受。
展覽中,包括“電影之父”盧米埃爾和正處於風口浪尖的NFT藝術家凱文·艾博施在內,39位/組藝術家的50餘件作品通過攝影、繪畫、雕塑、影像、裝置等不同媒介,展示出一個包羅萬象的圖像世界。
“圖像超市”所要呈現的,既是當下最熱點的話題,也是我們身處的真實世界。
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巨頭、消費主義盛行、圖片氾濫、個人信息保護、“微工作”和數字勞工、加密貨幣,這些熱門話題以“庫存、原材料、勞作、價值、交換”五個角度,重新審視圖像在人們生活中的意義。
“這次展覽呈現了許多令人矚目的畫面,尤其是馬丁·勒·舍瓦利耶創作的名爲《點擊工人》的視頻,令人震驚。”桑迪說,這段視頻解釋了人們最熟悉的“點贊”“訂閱”背後,發生了什麼。
在《點擊工人》中,來自波蘭、孟加拉國等國家的婦女受僱於Liker、Taguer等公司,日以繼夜地刪除、查禁不需要的圖片,獲取低廉報酬。她們每天面對電腦屏幕,看到色情或違禁圖片就迅速打標籤,或者聽從掌控者的指令,爲某一條社交網絡上的信息點出成千上萬的“贊”。人們熟悉的千萬點贊背後,很可能就出自一雙雙這樣的手。
在瑪麗–若澤·孟讚的著作《圖像會殺人嗎?》中,作者將圖像與毒品相比較,描述了圖像的依賴機制,“消費者被消耗殆盡,成爲圖像的奴隸”。
“毫無疑問,圖像經濟會引起一定的‘奴化’。”桑迪認爲,當我們討論當代人的網絡依賴症時,更應該關注這些日復一日參與影響信息傳播工作的工人。
氾濫的圖像,藝術家的反思
爲什麼叫“圖像超市”?桑迪解釋,這個主題來源於他2017年的著作《可見物超市:圖像的普遍經濟》。
身爲哲學家,桑迪面對空前氾濫的圖像,一直在思考這些圖像背後,其存儲、流通速度、構成材料和價值波動是怎樣的,圖像如何成爲一種新的資本形式?在這種思考下,圖像經濟概念被明確提出。
他將海量的圖像比喻爲人們最熟悉的超市,圖像的傳輸、存儲、管理、價值,以及一系列因圖像而發生的工作、產生的交流等,都可以通過“圖像超市”來呈現。
人們一邊傳播圖像,同時也透露了身份信息。他認爲,正因如此,圖像經濟問題成了政治問題。比如Facebook泄露用戶的信息給數據公司,妨礙美國大選進程的事件,就是圖像傳播對政治決策的影響。
儘管展覽具備嚴謹的學術性,甚至很難懂,但每一位觀衆都能感受到自己正置身圖像的洪流中,也能體會每一位藝術家對時代的反思。
展覽中,美國攝影師特雷弗·帕格倫在北太平洋海底拍攝的《被美國國安局監聽的海底線纜》告訴人們,互聯網線路依然沿用着1902年就投入使用的皇家通信線路。世界上大約有380條海底電纜,跨度超過120萬公里,但人們幾乎意識不到它們的存在。這些傳輸計算機數據的海底電纜,支撐着每一幅圖像的傳輸,同時也涉及美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如果我們認爲圖像經濟的關鍵是圖像的傳播速率,那麼藝術就能讓其放慢腳步,或者讓人意識到這種速率,而意識到正是抵抗的第一步。”桑迪說,他無意對此進行指責,而是希望人們看到圖像背後被遺忘的活動和故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紅磚美術館館長閆士傑相信,對於每天沉浸在海量圖像裏的個人而言,將會在這場展覽後,“重新思考我們與圖像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