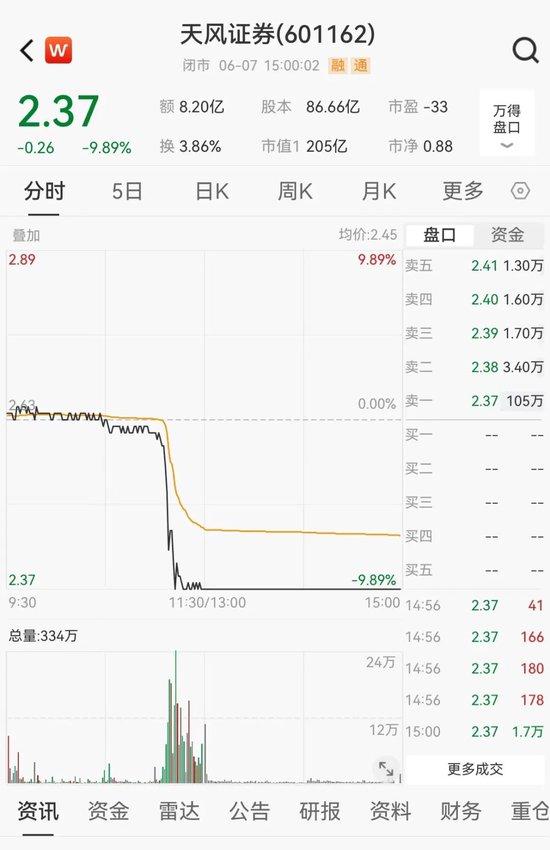電影《失孤》導演彭三源:郭剛堂曾包場去看電影,坐在影院門口哭
“這中間有N種可能
但現在出現了最好的那個”

郭剛堂和郭新振認親現場。圖/聊城公安
電影《失孤》原型一家的團聚成爲7月13日公安部新聞發佈會最牽動人心的焦點。這部電影中的被拐兒童原型郭新振已被找到,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獲。
1997年9月21日,山東聊城郭剛堂(男,現年51歲)夫婦時年2歲半的兒子郭新振,在家門口玩耍時被一陌生女子抱走,下落不明。
24年間,郭剛堂報廢了10輛摩托車,騎行約50萬公里,在全國進行“拉網式”尋親。2021年7月11日,山東、河南兩地公安機關在山東省聊城市,爲郭剛堂、郭新振一家人舉行了認親儀式,離散24年的家庭團聚。
“就像人生幾大樂事達成的心情一樣,無法形容的複雜、高興。”7月13日,中國新聞週刊專訪電影《失孤》導演彭三源。作爲郭剛堂一家的長期關注者,她談及得知郭剛堂找到郭新振的心情時如是表達。
在爲電影《失孤》做準備的過程中,彭三源採訪了大量的“破碎”家庭,衆多悲劇讓她不敢做出樂觀的想象。
“我覺得不會有比這更好的結局了。這是一個很百感交集的事,是一萬句高興都不能說出的那種複雜心情,因爲這中間有N種可能,但現在出現了最好的那個。”在彭三源看來,平安健康又得到良好教育的郭新振找回親生父母,是命運對郭剛堂24年尋子之路的回覆。
中國新聞週刊:你是什麼時候得知郭剛堂找到郭新振的?
彭三源:我大概比媒體早知道四五天。他們DNA比對結束之後,因爲我們有一個羣,包括郭家、公安部打拐辦、寶貝回家網站和我們,我們一直都是有交流的。
中國新聞週刊:當時心情是怎麼樣的?
彭三源:我當時覺得,像金榜題名一樣高興,一下子就熱淚盈眶,就覺得終於塵埃落定了。就像人生幾大樂事達成的心情一樣,無法形容的複雜、高興。
中國新聞週刊:電影拍攝之後,郭剛堂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
彭三源:我從第一次關注他到現在,已經11年了。一開始瞭解這個人,是知道他在路上找孩子,找了13年,時間之久、路程之遠,讓我非常震撼。當時我就有一個念頭,這個人是公路尋子,所以一定是適合拍攝的,我就通過寶貝回家的網站找到了郭剛堂,去了他的聊城老家,那時候是春節前,家家都在籌備過年,只有他家裏是冷清的,沒有生機的樣子。
後來我們一邊準備拍電影,一邊像姐弟一樣相處。我就跟他說,你要生活。你的生活裏不僅僅只有找孩子這一件事,家裏還有老人、愛人。後來,我們時不時通電話,他會給我寄山東的桃木劍、寶葫蘆。後來他會打電話告訴我,今年春節家裏買了年貨、貼了春聯,他這些年也有一些調整。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聊城的農村老家要拆遷,他說擔心以後郭新振回來就不會認得這個家了,怕孩子如果自己找回來不是以前的樣子。我說你拍一些照片、視頻,留下來給孩子看。因爲孩子丟時才2歲,不太可能自己找回來的。不過這些對他來說都不是最重要的,郭剛堂心心念唸的就是要找到郭新振,現在他的心願實現了。
中國新聞週刊:之前有預想過會有這一家人團聚的一天嗎?
彭三源:說實話,沒敢想。因爲我之前採訪過的家庭,不止郭剛堂一家,有的家庭孩子找到了,父母過世了;有的家庭,終於找到線索了,孩子去世了;還有母親絕望,然後就自殺了。
郭剛堂的事媒體報道不止一次了,我們也拍了電影,鋪天蓋地的報道,所以我們拍電影的時候心裏有過一個疑問,就是劇中劉德華問高僧的那句“他還活着嗎?”,這是我們誰都不敢說出口的疑問和擔憂。
這也就是爲什麼郭新振被找到了我們這麼高興——這是最圓滿的結局。第一,孩子活着;第二,孩子很健康;第三,他正常長大,接受了高等教育。我覺得不會有比這更好的結局了。這是一個很百感交集的事,是一萬句高興都不能表達的複雜心情,因爲這中間有N種可能,但現在出現了最好的那個。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這個電影當時對郭家意味着什麼?
彭三源:電影上映的時候,郭剛堂包場去看,然後他坐在電影院門口哭,這些我都知道。當時我們電影宣傳也是不遺餘力的,我們都希望通過電影的影響,讓這個事情更廣爲人知。我們都盼着一個奇蹟出現,就是那個孩子懷疑自己不是親生的,然後主動找公安機關要求做DNA比對,因爲孩子“往回找”比父母找他要快多了,父母找是大海撈針,所以我們盼着奇蹟出現,不過這個奇蹟沒出現。最後還是公安機關的執行力度大,持續不斷尋找,實現的。
中國新聞週刊:郭剛堂尋子的故事哪個瞬間打動了你,讓你決定把它拍成電影的?
彭三源:在我第一次採訪郭剛堂的時候,聽他講路上的遭遇。他有兩種遭遇,一種是殘酷的,一種是溫暖的。他曾經被人打劫,那人打劫完看到尋子旗,又覺得不合適,把錢還給他了。你看人性,可以有這種瞬間的兩極反轉。郭剛堂那有一個厚厚的記事本,本上記着他的行程,哪些人幫助過他,某年某月某日,誰幫助了他多少錢的一頓飯,這些東西是當時打動我特別重要的一個點。
因爲我覺得一個人在苦旅中,如果一直是苦的,他會堅持不下去的。這太殘忍了,即使拍了觀衆都不會接受,恰好是有這些溫暖的存在纔有可能支撐一個父親十餘年的尋子。
還有郭剛堂給我看他去過的地方標註的地圖,他用紅筆密密麻麻標上了紅點,那些紅點又像血跡又像眼淚,我當時覺得我如果不拍這個故事,我對不起我的職業。
中國新聞週刊:你的很多作品都是現實題材。在你看來,現實題材作品的吸引力在哪裏?
彭三源:我覺得人生百態本身就是一臺戲,我們任何編劇都編不過命運的安排,我們能把現實中的東西表現出萬分之一我們就是偉大的編劇了,我們再努力寫出的東西都比不上命運的翻雲覆雨手。
中國新聞週刊:你認爲現實題材的電影作品對公衆的意義在哪裏?
彭三源:比如打拐,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的電影能引起公衆對這個事情的重視。有孩子的家長更看護好自己的孩子,我們能提醒一個人都是功德無量,我們要能提醒100個人、10萬人,那我們就沒白拍這個電影。
另外我認爲這個世界能正常運行下去,人們在面臨苦難的時候還有勇氣活下去,一定是那些暖的東西、善的東西,在人最絕望的時候給了一點溫暖,所以我希望無論什麼作品,都能向人傳達善意的東西,給人盼頭。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