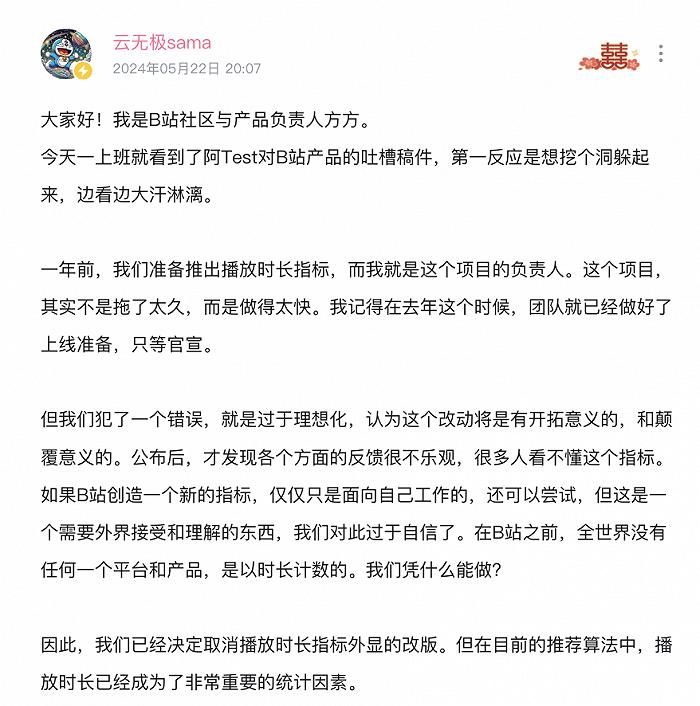真火熱還是炒概念?當我們談虛擬偶像時,在談些什麼?
來源:獵雲網(ID:ilieyun)
文/子璇
虛擬偶像的開發和運營,在疫情時期,被日本娛樂行業稱爲獻給世界的“新娛樂”。
近日,對YouTube進行各類數據分析的網站Playboard發佈了一項統計顯示,2020年獲得Superchat(類似於“粉絲打賞”)收入最多的YouTube Channel前十位中,有九位來自日本,其中七位都是虛擬偶像。
這樣的新娛樂之風儼然已經吹到了中國。
6月12日,在B站進行生日直播的虛擬主播——向晚(Ava)直播時長2.8個小時,直播中的付費人數達1.17萬人,讓她營收125萬元。
今年,在B站十二週年演講時,CEO陳睿提到過去一年有超過3.2萬名虛擬主播在B站開播,同比增長40%。在B站直播領域,虛擬主播是增長最快的品類。
數據也顯示,過去5年,虛擬偶像市場規模的年均複合增長率超過了44%,而2020年的增速超過了70%。隨着越來越多的虛擬偶像出圈,受虛擬偶像帶動的相關產業商業價值也在不斷被髮掘,2020年虛擬偶像帶動產業規模爲645.6億元,預計2021年將達到1074.9億元,產值增幅高達66.49%。
在這股熱潮之後,我們採訪了洛天依、迪麗熱巴的虛擬形象虛擬冷巴創作方——次世文化、以及現在正火的虛擬IP直播現象級產品《我不是白喫》背後的團隊人員,希望探討這個行業的現狀、錢景和未來。
但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他們都否認了虛擬偶像這個定義。
或許說,他們在外界的定義中,和虛擬偶像有着不小的關係,但是對於他們而言,這個定義並不太準確。
於是,新的問題又在採訪中產生。什麼是虛擬偶像?當我們在討論虛擬偶像時,我們實際上在討論些什麼?而當我們對虛擬偶像報以期望時,又是在期望些什麼?
讓我們從世界第一的公主殿下說起
2019年夏天,我在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看完了一場虛擬偶像演唱會。

在初音未來壓軸出場時,全場迎來了整齊劃一的熒光綠應援色以及應援call。
在那個時候,虛擬偶像的概念還沒有現在這麼氾濫,回家後,我還需要和身邊的人解釋什麼是虛擬偶像,以及他們是怎麼通過VR技術出現在舞臺上,又是如何讓現場的人迸發出這麼大的激情的。
最後,千言萬語,面對別人的不理解,我只能匯成一句:“宅男力量大”。
那個時候,虛擬偶像還是一個專屬於二次元的詞彙。
初音未來的來源是一款語音合成引擎VOCALOID。日本的Crypton公司,原本是一家以電子音樂軟件、彩鈴及音效庫爲主要事業。在做音樂開發的期間,在接觸到VOCALOID,隱約的看到了這個領域發展的新方向,於是,這家企業通過VOCALOID爲基礎開發出了一個音源庫,音源數據資料採樣於日本聲優藤田咲。
2007年8月31日,基於改良升級的VOCALOID2引擎上開發的新的軟件——初音未來,誕生了。初音未來要比之前所有的虛擬偶像更來得成功,僅在發售的前兩週便有了將近四千套的發售成績,在之後的一年中,初音未來創下一年4萬多套的銷售記錄。
不少用戶通過這個軟件創造出了優質的作品,一系列如《世界第一的公主殿下》、《甩蔥歌》這樣的優質歌曲都由這個音源演唱後,初音未來和她的作品一起火了。CD、演唱會,讓這個虛擬偶像越來越火併成功出圈。
而在國內,另一個擁有同樣路徑的則是洛天依。

曾被李宇春演唱的《普通DISCO》、周深演唱的《達拉崩吧》都是源於這位虛擬歌手。而國內,這位歌手的出圈之路不僅於此:2016年2月2日,洛天依與楊鈺瑩登上湖南衛視小年夜春晚合唱《花兒納吉》,成爲首位登上中國主流電視媒體的虛擬歌手;2021年2月11日,這位虛擬偶像在《2021年中央廣播電視總檯春節聯歡晚會》與月亮姐姐、王源共同表演少年歌舞《聽我說》。
在洛天依的帶領之下,虛擬偶像之風已經儼然正在國內興起。
而除了洛天依這樣的虛擬偶像,在海外,還有多種形式的虛擬偶像存在。
網紅少女Miquela是一個虛擬網紅,她是CGI(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就是計算機生成圖像,她有着可愛雀斑,設定是長期定居在洛杉磯,是一位擁有西班牙裔、巴西裔和美國血統的模特及音樂人。不僅被拍到與多位名人在一起,出了自己的專輯,還被許多出版物採訪介紹過,也爲街頭服飾和Calvin Klein,Prada等多個奢侈品牌代言。
在她最早更新的動態中,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她是虛擬偶像,而是將她視爲真實存在的網紅。
另一位在今年火起來的CodeMiko則是活躍在Twich平臺上的虛擬主播,在CodeMiko每天5小時左右的直播中,用戶可以讓她“當場去世”或者“付費形象diy”,你可以讓她閉嘴、改變她的身體參數、甚至炸掉她。逐漸出名後,她也開始與衆多平臺大佬連線,以主持人身份採訪對方。而因爲刁蠻的語言風格與美國深夜政治諷刺脫口秀類似,她被美國科技新聞the verge稱其爲“最新一代的虛擬脫口秀主持人”。
在過去,我們定義虛擬偶像時,認爲“他”應該有作品,能夠登上舞臺,像一個真人偶像一樣表演,並且發表自己的專輯。而現在,一個事實是,從虛擬主播、虛擬網紅再到抖音上的虛擬IP帶貨,都開始被我們稱之爲虛擬偶像。
那麼,那些虛擬偶像行業從業者,又是怎麼看待虛擬偶像的呢?
“虛擬偶像對我們的定義,或許不太準確”
洛天依所屬虛擬偶像品牌Vsigner相關負責人告訴獵雲網,他們對自己的定義,其實是虛擬歌手。
不瞭解虛擬偶像的人,會認爲洛天依的價值,是在於歌曲的產出,以及出現在觀衆面前的演唱會。但是對於洛天依的團隊而言,洛天依背後的生態及創作者,纔是洛天依的意義所在。
“偶像的所有動作,其實都是從上而下的官方行爲,沒有用戶能夠通過技術參與到偶像的內容中去,這是洛天依和偶像的區別”。
在Vsinger團隊看來,洛天依本質上是一個技術來驅動的虛擬歌手,將用戶容納進她的歌曲作品創作中來,纔是最爲核心的部分。
“洛天依的很多粉絲,其實也是洛天依內容的創作者,他可以將自己的情感基於洛天依的軟件創作出來。”
相比於選秀,洛天依的故事才更像“養成”。
而另一位創業者陳燕,也表示,團隊不會使用“虛擬偶像”這個標籤,雖然,這個團隊不僅開發出了演員迪麗熱巴的虛擬形象“迪麗冷巴”和黃子韜的虛擬形象“韜斯曼”,還打造了參與央視主辦的選秀節目《上線吧!華彩少年》的翎。如今,翎更是登上了《VOGUE服飾與美容》的年輕衍生刊物VOGUEme2021開年刊,獲得許多時尚媒體及博主的背書。

在陳燕看來,團隊做的,是virtual beings(虛擬人)。虛擬偶像其實更像是一個娛樂圈的產物,難免自動趨向粉絲經濟的特點。在陳燕看來,前期產品的應用場景及場景所對應的垂直用戶羣體更應該被重視。
因此,次世文化更像行業中特殊的翻譯官,化解了讓娛樂行業懂得技術呈現方式與讓技術公司瞭解藝人需求市場之間的溝通鴻溝。
所以,便有了次世文化與嘉行文化嘗試開發的演員迪麗熱巴的虛擬形象“迪麗冷巴”,與龍韜娛樂合作的黃子韜的虛擬形象“韜斯曼”。
而在這個人人皆直播的時代,在提起虛擬偶像的時候,我們還會將目光關注到一羣以帶貨爲目的的虛擬IP。
2019年5月,一個頭戴熊貓髮卡,有着異色瞳的短髮少女“伊拾七”在抖音誕生,記錄着她和男友的日常生活的視頻迅速得到了那些喜歡溫馨治癒向作品的網友們的關注。兩年之後,“伊拾七”光在抖音上就已經有了超過1200萬的粉絲和2億個贊,全網粉絲以及突破1700萬,這個形象也從日常生活領域逐漸轉向了虛擬偶像,成爲抖音平臺上的爆款品牌。
另一個“我是不白喫”則也成爲了經典案例,這一個動畫形象在視頻中以食物科普的形式出現,介紹諸多美食,今年3月7日,我是不白喫首次開啓直播帶貨,當天便實現了超過12萬的粉絲增長,一週內更是漲粉126萬,並在首播後的一個半月內完成了粉絲規模翻倍。
優質內容+優質產品,這成就了“我是不白喫”的內容+消費目標。2020年內,“我是不白喫”榮獲了“抖音KOL綜合價值排行榜NO.1”、“年度最具商業價值網絡達人”獎、“年度直播領域最具影響力創新企業”、“克勞銳年度新銳”獎等等。
但是,談及外界的“虛擬偶像”定義時,創始人朱宇辰則表示,自己做的是虛擬IP,這個動畫公司同時擁有一個極其專業的選品和行業採購團隊,因此走出瞭如今的成績,但是論及虛擬偶像,我是不白喫則真的完全不沾邊。
一定程度上,相比於其他企業打造出來的虛擬唱跳女團,這些企業確實走的不是偶像的發展路徑,正如Vsinger團隊所說,偶像的行爲應該是自上而下的。同時,這些企業也有着各自的差異化發展路徑,虛擬偶像的定義對於他們而言,略顯狹隘。
但是,隨着資本的湧入和媒體的報道,關於虛擬偶像的定義正在泛化也是事實。那麼,這個賽道的價值又在哪裏呢?
展現價值和選擇場景
在過往的媒體報道中,我們看到虛擬偶像時,最常提到的一個詞,便是“永不塌房”。
無論是近日華晨宇的緋聞,還是吳亦凡的熱搜,每一次偶像的負面,都讓粉絲和品牌方焦頭爛額。
在這個粉絲經濟時代,“永不塌房”成爲了虛擬偶像的巨大賣點。去年11月,樂華娛樂CEO杜華宣佈歷經兩年打磨的虛擬女團A-SOUL即將上線,並做出“永不塌房”的豪邁宣言。
但是,正如洛天依的價值所在一樣,永不塌房展示的不過是虛擬偶像真正意義的冰山一角。
從洛天依的角度來說,粉絲曾如此表示,“我給虛擬偶像寫歌,實際上是通過虛擬偶像實現我自己的旋律。”在粉絲的眼中,隨着入坑時間越來越長,相比虛擬偶像,他更喜歡的反而是那些賦予虛擬偶像靈魂的創作者,特別是那些優秀的獨立音樂人。
在介紹洛天依的粉絲心態時,Vsinger團隊提到了購買BJD娃娃的“娃媽”,認爲或許可以作爲理解參考。BJD是Ball-jointed Doll的英文縮寫,外形看起來是一個球型關節人偶,但是卻造價昂貴。而消費者和BJD的鏈接,並不在於單純地購買,而是在購買之後,爲其換衣服、化妝、搭配、拍照、拍視頻等長時間的後續投入。而如今,BJD這個十分小衆的圈子,也擁有着小小的產業鏈:娃娃設計、生產、乃至服裝的設計銷售等。
在Vsinger團隊看來,作品產生的連接,和單純的喜歡明星之間有一些區別。他既有用戶的這種喜歡偶像的心態,他也有這種把自己強烈的情感投入到了一個作品裏面去的這種表達慾望上的心態,而這被稱爲虛擬偶像的共鳴能力。
同時,Vsinger團隊提到,虛擬偶像並非是大衆無門檻的東西,因此,年輕人也會需要虛擬偶像這樣的亞文化來表達自己的個性。
而次世文化創始人陳燕則對虛擬偶像的場景進行了更多的思考。在他看來,迪麗冷巴、韜斯曼其實是在作爲明星的衍生線,創造出明星更好的人設以及可輸出的內容,是爲了滿足於明星粉絲。

在陳燕看來,明星的存在是難以複製的,在單位之間裏能夠輸出的內容是有限的。例如一位頂流明星,在一定的時間裏也只能固定釋放出一定的合作權益。但是明星的虛擬形象則變成了一個更高性價比去輸出內容的方式,可以在明星的固定時間之外,通過運營虛擬偶像去滿足粉絲的需求。對應的,也可以滿足藝人合作商業合作品牌及項目訴求。
在陳燕看來,這樣從“場景倒推出解決方案”的思路是這個行業更需要的。包括在談到翎的創作思路時,陳燕也認爲,這樣的產生是因爲在海外已經有了成功的案例,所以對這樣的案例進行復刻、再加上中國文化,打造了翎。
“某種意義上我發現了這個場景,我才最終選擇了一個具體方案而已”。
伴隨着這樣的探討,我們又會產生出這樣的疑問,那麼,如今的虛擬偶像的場景下,能否容納更多的入局者呢?
虛擬偶像真的永不塌房嗎?
在媒體報道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數據:洛天依在淘寶直播的坑位費達90萬元,遠超薇婭、李佳琦。
但是Vsinger團隊對此的回應則是,假的。
她介紹了洛天依的商業變現路徑,一是和明星一樣進行代言合作,二是產品的IP衍生,三則是內容的分發。洛天依也試水過直播帶貨,但是這樣的帶貨更多地是在做合作品牌的推廣,和外界所稱的高價坑位費有較大的出入。
雖然行業或許並沒有外界所言那麼地賺錢,但是這個行業正在變得火熱也是一個事實。
根據愛奇藝《2019虛擬偶像觀察報告》,全國有近4億人正在關注或走在關注虛擬偶像的路上,2020年,虛擬偶像市場據估計達到2000億。
本月19日,樂華娛樂發生工商變更,新增浙江東陽阿里巴巴影業有限公司、字節跳動關聯公司北京量子躍動科技有限公司等爲股東。而樂華在去年推出的A-SOUL正是和字節跳動聯合企劃。
在此之前,《王者榮耀》也依託自己的IP推出了虛擬偶像男團無限王者團“白、亮、信、雲、守約”;愛奇藝則推出虛擬樂隊“RichBoom”……
上個月,國產彩妝品牌“花西子”也推出了同名虛擬代言人,之前屈臣氏也推出“服務大使”屈晨曦,這樣的形式主要用於幫助合作品牌做產品推廣,參加公關活動的虛擬直播等工作,更多品牌的虛擬代言人及新合作形式即將登場。

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的是,過去的不少虛擬偶像都已經進入了尷尬的發展境地。
2018年,巨人網絡與日本JOYNET株式會社達成合作,獲得旗下動漫作品Menhera Chan全部品類的全球獨家代理授權,並宣佈將其手機遊戲化,開發手遊《胡桃日記》。隨後推出虛擬主播“七瀨胡桃”,正式進軍虛擬偶像市場,將虛擬偶像的細分領域作爲重點研發項目,力圖打造超級虛擬偶像IP生態。
然而,今年3月,七瀨胡桃的中之人宣佈終止合作;到了4月份,七瀨胡桃的官方微博則轉發了一條肖戰工作室的微博,又引發粉絲不滿,而相關的道歉微博的互動量,則是七瀨胡桃近半年來的互動數最高。
而RiCHBOOM曾經登上了《樂隊的夏天2》,也在今年接連發布了幾張專輯,但是反響只能算平平。RiCHBOOM也在4月接下了蒙牛隨變冰淇淋的代言,但是在外界的視角中,知名度着實較低。
所以,虛擬偶像或許不會塌房,但是可能會出現運營失誤,而最大的問題,可能還是不一定能火。
畢竟,要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面對有穩定的作品產出、資源露面的真人偶像,虛擬偶像背後的團隊,如何去獲取粉絲呢?又如何保持穩定的內容輸出呢?
除此以外,在虛擬歌手這個領域,國內沒有出現像洛天依這樣出圈的,那麼,在虛擬網紅領域,能出現多少個頭部IP呢?
CodeMiko的舉動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思路,在現場互動中,通過技術炸掉自己、換裝,都是無法在真人偶像身上獲取的。
一些品牌在宣傳的過程中,選擇一個自己可以完全控制、又能夠打造人設虛擬偶像作爲出口,也無可厚非。
但是,是否有一些企業只是在單純地蹭熱度呢?運營一個虛擬偶像,除了技術以外,更重要的是內容的產出,而又有多少入局的企業擁有這樣的能力呢?
當我打開抖音時,發現不少打着虛擬偶像標籤的視頻,其實只是一個動畫短視頻,不過是將人物做得更加仿真而已,在這些視頻中,有的只是在抖音上用最火的歌曲跳着宅舞,有的實則是在用賣肉的形式通過視頻爲自己的充氣娃娃產品引流。隨着我們對虛擬偶像定義的越來越泛化,對行業帶來的影響是完全正向的嗎?還是說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
毋庸置疑的是,隨着技術的發展,虛擬偶像的興起是必然,但是如今的我們,或許已經可以換一個思路去思考行業的未來:虛擬偶像,還有新的可能性和表現形式嗎?
虛擬偶像需要新的發展土壤
2020年4月,美國饒舌歌手Travis Scott,用其虛擬人身份在Epic Games的遊戲《堡壘之夜》裏舉辦了一場名叫“天文學”的直播演唱會,有1200多萬玩家同時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在線蹦迪,相關視頻引發了超過2億次的觀看。
在這個世界裏,Travis Scott的虛擬人作爲他“延伸自我的邊界”,嚴格按照其本人的身材比例和細節來做,精確到他腳上所穿的鞋子型號。
在現實中不能實現的是,隨着演唱的進行,世界也發生驟變,玩家們或在星火燎原的地上奔跑,或突然沉入海底,之後又瞬間被拋入外太空。人們驚呼這是“一場超現實的、瘋狂的壯麗體驗”。
據統計,Travis Scott本人從這場演唱會里賺到了2000萬美元,相關周邊已經賣爆。相較而言,從2018年到2019年,他每場真人演出的收入大約爲100萬美元。
Travis Scott無疑給虛擬偶像的發展帶來了一種思路,那便是在遊戲中,通過現實中無法實現的技術,帶給用戶全新的演唱會體驗。
同時,我也認爲,如果我們談虛擬偶像,僅僅只談虛擬的偶像,或許對於行業的發展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或許,思路可以進一步擴展。
在電視劇《黑鏡》第二季第一集中,女主角未婚夫因車禍逝世,悲痛中,她授權一家公司,以逝者生前的社交網絡信息爲素材,生成了一個可與她對話的虛擬 “未婚夫”,並最終,將這個虛擬角色下載到樣貌和他未婚夫一模一樣的人造身體裏。
而另一個可以關注的海外App則爲Replika,這是一個聊天機器人生成的AI朋友,正在承載着數十萬用戶的喜怒哀樂。
在美國,2015 年 11 月,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奪走了一位名爲 Mazurenko Roman 年輕人的生命。而他的好朋友則在他離世後,通過好友的聊天喜好,打造了一個像Mazurenko 一樣的聊天機器人,讓Mazurenko的親友可以通過這個軟件與其交流,獲得慰藉。
後來,他則在這個思路下,打造了一個聊天機器人Replika,基於一套名爲“序列到序列”的深度學習模型,Replika會通過不斷與人交談,來模擬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並推進二者的聊天,從而與用戶達成更爲深度的關係。
而這樣定製類的情感機器人,則讓不少用戶減少了孤獨感,甚至產生了依賴感。
虛擬偶像,其實可以通過技術解決人們對於陪伴和互動的情感需求以及單純的娛樂需求。除此以外,陳燕也在採訪中提出,虛擬人可以在醫療、虛擬健身教練等多個角度,來協同大家的生活方式。
毋庸置疑的是,在技術的發展之下,虛擬偶像已經有了足夠的硬件土壤;而在多個虛擬偶像破圈之下,這個行業也正在面臨着更好的市場,但是,運用場景,或許是我們接下來應該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