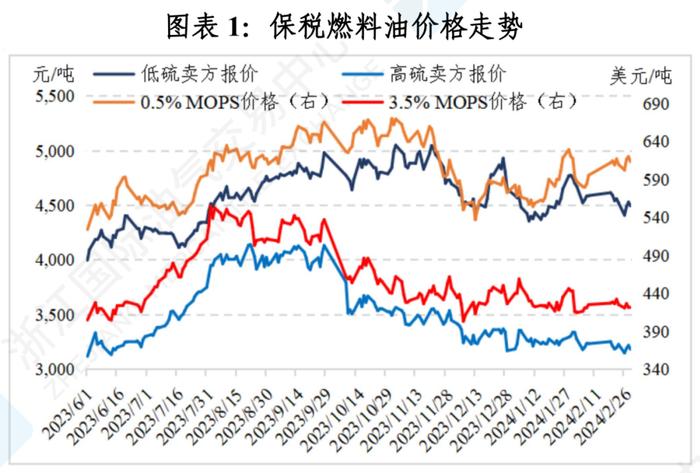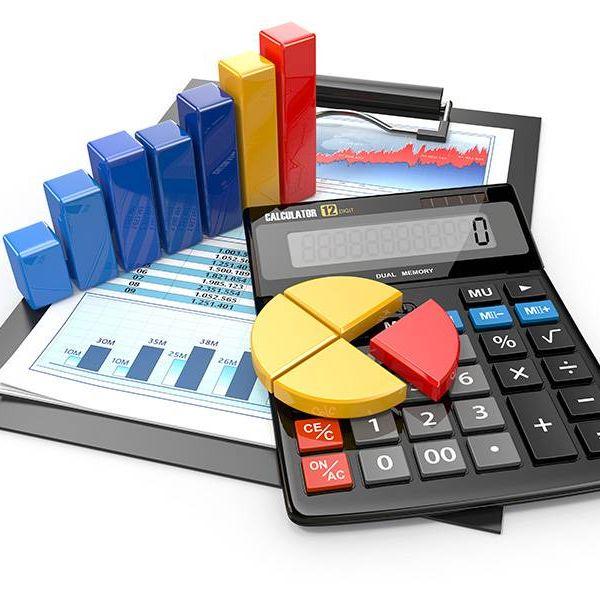“弘進輪”舟山獲救背後:國際航運船員"下船難"困局
原標題:“弘進輪”舟山獲救背後:國際航運船員“下船難”困局

8月11日,東悅輪船員舉牌求助。受訪者供圖
8月12日,“弘進輪”(GRAND PROGRESS)的最後9名船員還在做着下船前的準備。從7月30日開始,船上20名船員裏,陸續有13人先後出現發燒等症狀。有的人反覆發燒,嚴重者還出現嘔吐、失去味覺嗅覺等情況。
弘進輪最終在舟山港獲救。8月9日,舟山方面確認16名船員核酸檢測陽性。當天晚上,11名船員被點對點閉環接至定點醫療機構救治,其餘症狀較輕和無症狀船員暫留船治療等待,待船員管理公司後續換班船員到崗後輪換。
在航運界人士看來,弘進輪在被困幾天後就能獲救、短期內實現人員順利下船,在疫情肆虐的當下,這就是“最好的結局”,是一個“罕有的成功案例”。
與之相對照的,是國際航運的船員難下船、難換班的問題,從疫情開始後存在至今。

8月13日,弘進輪船員將部分待銷燬物品清理到甲板上。受訪者供圖
一天清理出十餘噸需銷燬物品
第一批11人下船後,弘進輪留下了9名海員進行清理、消殺等工作。16名替換人員則在就位待命,等船上準備就緒,即可換班。
8月11日上午,周念安和留在船上的船員們開始對整船進行打掃。留在船上的9人裏仍有5人核酸檢測陽性。不工作的時候,船員們各自呆在艙房,工作的時候仍然需共處一室。11日這一天,他們一起做了大半天消殺工作,清理出來十餘噸需要送到岸上銷燬處理的物品。
周念安已經兩天沒有好好喫東西,雖然船上米麪油都有,但他不會做飯,艙房裏最後一包方便麪,是他備下的應急口糧。快要下船了——他這麼盼望着,下船之前,這一包應該夠了。
作爲一艘巴拿馬籍貨輪的最低配備,弘進輪此次需要至少招聘共計16名海員接替工作,但由於20名船員16名核酸檢測陽性的消息在航運圈裏人人皆知,在船舶管理方發出招聘廣告後,應者寥寥,弘進輪船員證實,目前船方開出高價招聘新船員。8月11日,弘進輪的船管方、天津跨洋國際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在接受採訪時稱,已招到十五六名船員,正在待命。

8月11日,弘進輪船員對船隻進行消殺。受訪者供圖
開不進的港口
弘進輪不是第一艘被困住的船。就在周念安目送同事們下船時,300公里外的東悅輪(EASTERN DELIGHT)正在求助。
東悅輪是利比里亞籍,輪上19名船員中12人是中國籍。包括二副劉騰在內的5名中國船員,原計劃要在某港口下船換員。“船東和船員公司都同意,但被船舶代理告知該港口目前無法安排船員休假。”東悅輪發出的求助信裏稱,諮詢多家當地船舶代理尋求換班方案,“均因疫情期間手續無法辦理爲由遭到拒絕。”
這不是第一次遭拒。劉騰說,他們5名船員最初準備於七月底八月初在廣東某港口換班,但被代理告知,由於疫情形勢緊張,無法辦理船員換班手續。
根據《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海員服務一般不得超過11個月。通常情況下,國際航運的船員連續工作8個月左右會下船休息。疫情前,港口如果發現有船員超過勞工公約規定的期限,可以強制遣返讓公司換人。
但疫情改變了一切。據中新社報道,直到2021年1月,全球仍有超40萬海員滯留海上,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已經連續工作達17個月,遠遠超過業內及監管限制工作時間。
船員們習慣把在海上航行的日子叫做“坐水牢”。動輒在海上漂泊數月,極考驗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疫情前還能在靠岸的時候下船走走,疫情後全球沒有任何一個港口會允許船員上岸。”劉騰說,這意味着從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船員就開始面臨合同期內的至少8個月的“刑期”。隨着疫情帶來的各種變數,曾經可以估算的“有期徒刑”,現在變成了“無期徒刑”。
劉騰的船員已經開始出現失眠的狀況。長期在船無法上岸帶來的焦慮,以及不知道期限的“水牢”帶來的壓力,讓他們感覺煎熬。
8月13日,東悅輪獲得確定消息,船上的5名船員可以在南通港下船換班。
碼頭困境
困局中,港口方直接成爲船員的對立面。
“是真的,現在(大部分港口)不讓外輪船員下船。”某國企碼頭生產作業負責人王天平和舟山港某碼頭生產作業管理人員鄭泛都明確承認這個現象的存在。鄭泛表示,自己所在的碼頭“從來不讓(外輪船員)下船”。王天平說,內貿輪船的管理相對比較寬鬆,船員只要持有檢測報告等港口當地政府要求的手續,大部分情況下還是可以辦理換員手續,但外輪基本不允許上下人員。
“對碼頭企業來說,換員跟碼頭關係不大,可防疫的主體責任卻在碼頭身上。”王天平說,“碼頭只要發生一個確診病例,立刻封鎖,然後全員核酸檢查3次以上,直接接觸確診病例的三班人員拉到指定隔離地點隔離14+7天。我們隔壁碼頭遇到一艘外輪卸貨,離開後發現船上有船員新冠陽性,整個碼頭都封了,到現在還沒開。”
王天平認爲,對於疫情防控來說,這樣的嚴管“無可厚非”:“有人上下就多一個風險點,一旦出事還存在追責的問題,而且每封一天都是損失,還會影響在客戶心裏的印象,以後就不到你這裏來了。”
疫情下船員換班手續的繁瑣也讓港口一方感覺頭疼。2020年五月左右,王天平所在的碼頭有且僅有一次允許外輪在此換員。王天平說,硬着頭皮辦這件事是因爲當時船舶上的“特殊情況”,“船員已經在船上呆了一年沒有下過地,船公司反饋說心理都出了問題,開始有暴力傾向。船已經靠岸,他們在船上出事我們也要擔責任。”
國內某大型港口船舶代理公司工作人員說,疫情前,換員是極普通平常的操作,沒有任何難度可言,基本按流程打報告即可,疫情後,換員難度大幅度提升,“難歸難,最後還是能走下來。只是時間流程被拉很長,基本上船到錨地前半個月就得跟我們敲定,然後發文件過來,審批流程至少一週。”
採訪中,多名外輪船長和船舶代理表示,上海、青島等大型港口,成功換員的可能性較高。“小一些的港口,有些沒有換員的能力,比如沒有完全隔離的條件。”一名船舶代理稱,每個港口的收緊程度都不同,如果是鬆散型的港口,有時甚至不同的碼頭也有不同的規定,“比如這個碼頭可以下,那個碼頭就不行。沒有統一的標準。所以最後能不能下船,一個是和地方執行操作方式有關,另一個和地方疫情發展密切相關。”

8月11日,大豐輪發出施打新冠疫苗申請書。受訪者供圖
疫苗難題
換員問題還直接影響着船員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弘進輪上20名船員,只有輪機長打過疫苗,他也成爲所有感染者中“自愈”情況最好的一個。周念安也很想打疫苗,但他11個月前登船時,國內的新冠疫苗尚未正式推出,疫情發生後,港口都不允許船員下地,對於船員來說,隨時出海的特性讓他們能夠按時按地接種兩針疫苗變得極爲困難。以上種種,造成相當數量的外航船員,身爲高風險人羣,卻完全“裸奔”。
記者瞭解到,東悅輪上的12名中國船員裏,5人沒有接種新冠疫苗。本次下船,他們的另一項要務就是去打疫苗。
8月11日,大豐輪(DATO FORTUNE)船長馬衛俊帶領船員,簽了一份《大豐輪船員施打新冠疫苗申請書》發送給船舶代理。大豐輪是巴拿馬籍貨船,船上23名船員都是中國人,14人未接種疫苗。申請書中明確希望能施打“一針式”疫苗。“安排防疫人員施打或者組織專車去岸上接種點都行。我們願意支付由此引起的相關費用,我們願意承擔由於我們施打疫苗而可能感染其他人員的一切法律責任。”截至記者發稿時止,大豐輪的申請尚未獲得回應。
外航船員出海,一般兩三個月才能回國一次,嚴格按照間隔一月打兩針疫苗幾乎不可能實現。今年5月,中國船東協會向國家衛健委、交通運輸部提出爲船員接種“一針”新冠疫苗請求,擬在11個口岸城市提供。
根據巴哈馬海事局(BMA)一項調查的結果, 全球87%的海員仍在等待接種第一支新冠肺炎疫苗。也就是說, 堅守在新冠肺炎疫情前線的海員中只有13%接種了疫苗。
等待破局
關於船員輪換的問題,國家六部委曾在2020年4月出臺過一份《關於精準做好國際航行船舶船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就中國籍船員換班問題提出要求:國際航行船舶入境後,計劃換班下船的中國籍船員經海關檢疫無異常且核酸檢測陰性後,自船舶駛離上一港口滿14天、健康記錄顯示連續14天及以上正常的,在辦理換班入境手續後,港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應當給予便利。
根據《2020年中國船員發展報告》,截至 2020 年底,我國共有註冊船員 1716866 人,其中國際航行海船船員 592998 人。2020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境內港口中國籍船員換班 14.7 萬人次。
但在現實執行中,大部分船員甚至走不到“海關檢疫”的步驟。“約束性文件沒有強制效力,在疫情壓倒一切的情況下,最後決定權還是在地方政府和港口手裏,造成現狀的原因就是相關方不敢擔責任,‘一刀切’。”採訪中,多名船長這樣認爲。
山東交通學院國際商學院陳超教授認爲,要解決現狀,需要出臺能落地執行的管理細則,以及加強邊防防疫功能。作爲港口方管理人員,王天平也在這場困局中覺得困惑和兩難,“這不是某個公司或者碼頭造成的,是整個大環境的問題。要解決它,換班的程序和方式應該有個統一的規範。把要求固定下來。”
多位航運界人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表示,航運界在等待一個疫情期間外輪船員下船的標準程序,即使它可能複雜,但“好過沒有”。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周念安、王天平、鄭泛爲化名)
文 | 新京報記者 楊雪 實習生 郭莉莉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