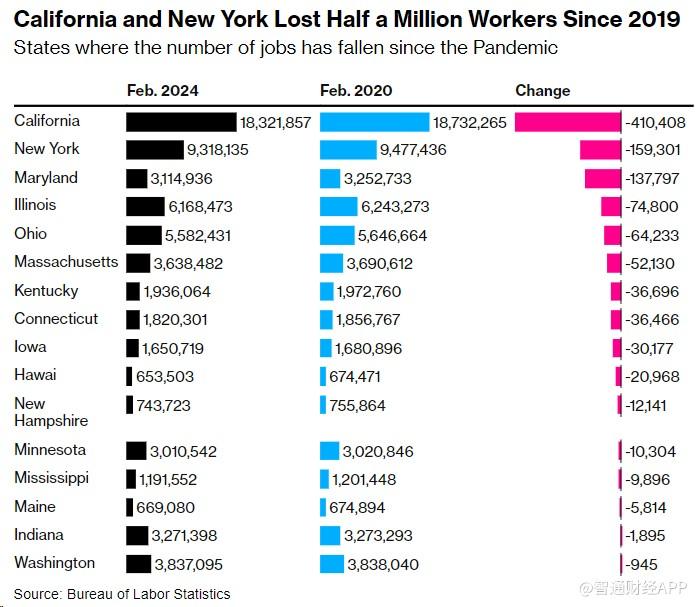熬過最難的2021年,後疫情時代餐飲困局何解?
作者/楊銘
編輯/劉珊珊
最近很多熱點,跟餐飲行業相關。
一方面,是茶顏悅色、海底撈等頭部餐飲企業因成本問題深陷虧損漩渦,肯德基、麥當勞也表示因成本原因集體漲價。如頭部火鍋企業海底撈,就在近日預警,預虧45億原因是300餘家經營不達預期門店關停,以及原材料、物業租金大幅增長、疫情反覆衝擊等原因導致。
另一方面,是外賣佣金,再次引發討論。2月18日,國家發改委等14個部門聯合印發《關於促進服務業領域困難行業恢復發展的若干政策》通知。其中一條指出,要求引導外賣等互聯網平臺企業進一步下調餐飲業商戶服務費標準,降低相關餐飲企業經營成本。

商戶服務費俗稱“佣金”,也是外賣平臺與商戶長期存在矛盾部分。政策發佈後,外界就將目光聚焦到美團與餓了麼身上:行政引導下,外賣佣金是否會繼續下降?
民以食爲天。行業兩大關注熱點,其實都說明了同一件事:餐飲生意越來越難做,成本結構失衡問題越來越凸顯。想幫助後疫情時代的餐飲行業,以及更多中小商家活下去,如何降低經營成本是其關鍵。
其中,房租、原材料、人力三項硬成本,向來被稱作線下餐飲經營的“三座大山”,而外賣佣金近年來也備受爭議。只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三座大山”短時間內無法改變情況下,降低外賣平臺佣金紓解商家壓力,成爲看起來最簡單的選擇。
去年5月,美團、餓了麼進行外賣費率透明化改革,將原本按訂單金額固定比例抽取的佣金,分爲技術服務費與履約服務費兩部分,跨出平臺調整與商家利益協同的重要一步。
目前,上述費率改革已在多個城市落地9個月。當餐飲行業再起波瀾,有必要再次深入追問,如今外賣佣金到底是什麼比例?費率透明化是“舊瓶裝新酒”,還是真正落到實處?“三座大山”壓力未解時,即便外賣佣金降爲零,是否又能真正紓解餐飲行業當前難題?
佣金VS“三高”,誰給商家帶來最大成本壓力?
“在我看來,房租、人力、原材料,是真正壓在我們商家頭上的大山。”2月22日晚,廣東東莞四月咖啡館負責人韓寶琳(化名)告訴“極點商業”。
開店這條路上,韓寶琳跌跌撞撞摸索了快5年。她的咖啡館如今佔地200多平方米,員工近20人,以堂食爲主,但外賣仍然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平均每月能送出2000單以上。也就是說,堂食和外賣,對韓寶琳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營收方式。
外賣成本上,她給“極點商業”算了一筆賬:每單外賣售價40-59元,佣金是按新費率——也就是技術服務費計算,目前在東莞的比例爲6.6%,平均每單佣金2.64-3.8元;大頭是給騎手的配送費,也就是按距離遠近、訂單價格收取的履約服務費,平均每單配送費大約在3.9元左右。合計每單需付出成本6.54-7.8元,收入33.5-51.8元。

如果以此計算,那麼每單利潤還算可觀。問題是,房租、人力、原材料等硬性成本上,每月大概需30萬元,讓韓寶琳的生意直接變爲微利。
“房租上,房東透口風說要每年漲租10%,讓我很苦惱,不知如何解決。”韓寶琳說,原材料上,最近水果、進口動物奶油一直漲價,導致店裏招牌草莓牛乳茶、多肉葡萄檸檬茶等成本一直上升,但又不敢輕易漲價。
韓寶琳目前能想到的困境擺脫方法是,加大外賣配送範圍,以此去彌補房租原材料不可控上漲帶來的影響。“6.6%外賣佣金並不算高,也讓我真的有賺。”她說,即便是每月8000元履約服務費也划算:2000多外賣訂單,找人自配送,起碼需要3個配送員,自己根本無力承擔,還要承擔風險。
在四川眉山仁壽縣,憨憨幹拌麻辣燙目前每月有5000多外賣訂單,每單平均售價35.5元,扣除佣金、履約服務費後到手24元左右。
2月23日,其負責人李民益同樣對“極點商業”明確稱,並不認同外賣佣金帶給商家最大壓力說法,“外賣確實要扣點,訂單量越多,總佣金越多,但銷量就越多,利潤也更多,佣金是增量生意裏需要付出的成本。”
在他看來,這筆賬需要如此算:即便這個月沒有一單外賣,房租、人力成本並不會因此減少一分,自己每賣出去一串麻辣燙——房租、人力、原材料合計一起約佔60%的成本,且呈不可控上漲之勢。“做餐飲的,才能真正瞭解這種壓力。”
如果說中小商家沒有規模優勢、議價能力不強,但很多頭部連鎖餐飲企業也難逃房租、人力、原材料上漲壓力,甚至陷入生死危機。

以海底撈爲例,其成本增長曲線斜率已變得非常陡峭:平均每店年租金成本約59.98萬元;2021年上半年,員工成本爲71.62億元;原材料及易耗品的成本達85.02億元,同比增長95.5%。茶顏悅色、星巴克、麥當勞等也將最近漲價主因,歸爲原材料價格上行——有數據顯示,中國餐飲行業原材料成本佔營業收入比例約爲30%-40%,且每年以2%的速度增長。
因房租、原材料等成本原因倒下的餐廳已經數不勝數。根據《2021餐飲發展6大趨勢簡報》顯示,2020年餐飲業新開店數約250萬家,關店門店數約355萬家。
“原材料、人力成本高,最不濟還能通過讓步食物品質、縮減規模控制,但房租卻是無法調整的固定成本,即便想轉手都無人接盤。”過去十年開店四次,四次失敗的李輝說。
近兩年疫情影響下,這一壓力更是有增無減。調查顯示,2021年有77.5%的餐飲商戶表示在門店租金上存在經營壓力。而且,這種高租金壓力並不止餐飲行業,比如線下商超普遍租金比例在20%~40%之間,購物百貨則收取高額的租金,服飾業態另外再收取18%~25%的高租金。
相比不可控的硬性成本,外賣佣金在2021年進行了費率調整——從粗放模式到透明化改革後,佣金明確爲技術服務費,履約服務費只在商家選擇平臺配送時纔會產生。

來源:極光大數據
從“極點商業”多方瞭解看,過去9個月內外賣新費率已在全國大規模鋪開,越來越多的商家開始採用新費率。根據極光大數據發佈的《2021餐飲外賣商戶研究報告》顯示,超過9成商戶繳納的佣金,即技術服務費低於8%,佣金在6%-8%的商戶佔比達到了66.3%。
外賣佣金爲何受爭議?
佣金是商業活動中一種合理的勞務報酬,各行各業自古皆存在。其說法歷史淵源長久,在中國史籍上早有記載,《史記·貨殖列傳》稱之爲駔儈。
“外賣平臺收取佣金,從商業模式看無可厚非,也是支撐企業發展、服務運營的成本基礎。”有業內人士指出,外賣配送是“點對點”模式,即每一單都需要配送員按照相應地址送達,互聯網很多企業存在的邊際效應和規模效應,在外賣行業尚未發揮作用,反而是背後的人力、研發、服務等成本很難被規模攤薄。(例如,按照美團說法,工具包括信息展示、交易結算、經營分析;服務包括客服諮詢、系統維護等。)

來源:美團財報
一個關鍵問題是,從上述調研數據來看,當前6%-8%的外賣抽傭比例,是否在合理區間內?
抽傭比例到底多少合理,一直未有最終定論。去年3月,全國工商提案中有一條:“外賣平臺抽擁在10%-15%區間纔是餐飲企業可以接受的,否則很難實現盈利”。倘若以此看,目前外賣佣金率位於這一區間下半部分。
橫向對比,歐美外賣平臺幾乎都爲國內外賣平臺的2倍——以Grubhub爲例,此前超過20%的配送費、12.5%的基礎佣金、0-17.5%的4檔推廣費相加,合計爲30%-40%。並且,在去年8月紐約市立法規定佣金設定15%上限後,Grubhub公開聲明表示反對。
縱向對比,直播帶貨佣金比例爲20%-30%且不包括坑位費,2020年網約車業務實際抽成比例爲15%-25%,電商佣金一般佣金爲5%左右,且不包括技術年費、保證金等其他支出。另外蘋果也抽成30%,安卓應用市場甚至抽成高達50%。
單純數據對比,外賣目前6%-8%佣金比例並不高。從外賣平臺角度來看,也多次“委屈”表態外賣是微利業務,且利潤存下降趨勢。
以美團爲例,商家傭金,也就是技術服務費收入一直是美團核心——2020年財報數據顯示,美團餐飲外賣全年利潤28億,騎手成本487億,全年餐飲外賣訂單超過100億筆,平均每單外賣利潤0.28元;到了2021年Q3,美團佣金收入爲232.2億元,但由於固定成本提高等因素,單筆外賣利潤下降至0.22元。

調查數據顯示,單筆外賣利潤下降至0.22元
詭異的是,儘管外賣佣金對比其他行業、國外同行並不高,且幾乎所有餐飲從業者都一致對“極點商業”認爲,人力、房租、原材料,纔是影響餐飲業生存最重要因素。爲何是外賣佣金反而頻頻引起爭議?
這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國內餐飲企業的“三高”問題,長期突出,但公衆端感知並不強。外賣行業還未興起的2011年,中國烹飪協會就表示,十年內房租上漲了5倍,“三高”壓力下餐飲店平均壽命爲兩三年,出現了每年15%的倒閉率。
“三高持續上漲,但公衆端卻很難感知,比如房租成本,房東零零散散遍佈全國,其中滋味只有餐飲經營者自己體會。”開店連續失敗四次的李輝如此認爲,外賣平臺主要是美團和餓了麼,絕大部分商家都通過這兩個平臺配送,對佣金的敏感性、話題性也就更高。
二是外賣平臺作爲公衆、商家、騎手的連接器,每個人都可以感知,也就備受關注。截至2021年6月,我國擁有4.69億外賣用戶規模,比2020年增長4976萬人,佔全體網民規模的46.4%——這意味着,我國近一半網民都點過外賣,也就有了更多參與感。
三是新冠疫情衝擊下,更多中小餐飲商家上線外賣平臺,邁出數字化重要一步。但鑑於外賣平臺的特殊性,無法像電商行業那樣將配送成本區隔開來,在費率透明化前,商戶只能看到一個總數字,這是佣金爭議根源。
“作爲商家,不怕付出佣金,怕的是規則、費率不透明。”韓寶琳就稱,在以前,外賣商戶收費模式較粗放,不同距離、不同時段訂單按照固定比例收費,無法清晰瞭解各部分資費在佣金中的佔比,這讓她對此相當抱怨。後來費率的逐漸透明化,又成爲她認可當前佣金主要原因。

“極點商業”瞭解到,去年5月以來,雖然新費率已在全國大規模鋪開,但落地到每一家餐飲商家需要更多時間。另外,雖然像韓寶琳這樣理解、支持新規的商家越來越多,但仍有少部分商家、騎手、公衆,將佣金與配送費混爲一談,理解上還存在一定偏差。
這一點,對政策的“誤讀”上也可以看出。以最新通知爲例,“引導”並非“命令”,且針對餐飲業提出7條紓困扶持措施,涉及企業防疫補貼、緩繳保險費用、拓寬融資渠道等方面——其中,2022年被列爲疫情中高風險地區所在的縣級行政區域內的服務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租金減免,實際上對餐飲商家渡過難關幫助最大,卻鮮少有關注。
相比普降佣金,更有意義的是什麼?
與外界喧囂之聲不同,很多商家均明確對“極點商業”表示,合理的外賣佣金,比降爲零更爲重要,也更透明。
“6.6%外賣佣金就算降低到零,每月省不到3000元,不夠一個員工工資。更重要的是,如果外賣平臺因此服務、運營不下去,分店只有關門,得不償失。”韓寶琳就說,自己也曾抱怨過佣金問題,但降到合理區間範圍後,再“強行下降”商家來說反而不是好事。
這不難理解:在外賣產業鏈中,平臺、商家、騎手、消費者是一個脣齒相依的命運共同體,但外賣行業又是一個邊際效應、規模效應不明顯的特殊行業,短時間難以通過規模、運營做到降本增效,加上人力、研發、服務等成本只會越來高,6%-8%的佣金下調空間確實越來越小。
“如果佣金繼續降低甚至降到零,要麼平臺虧損越來越大難以生存,要麼與騎手、消費者分攤成本壓力,甚至用其他收費模式轉移成本。平臺、商家、騎手、消費者都會受損。”有互聯網觀察人士明確指出。

這個道理,其他佣金收入爲主行業同樣適用。比如房產中介,佣金比外賣行業更受爭議,加上行業競爭激烈、魚龍混雜、收費不透明,中介行業頭部企業鏈家2015年曾提出過一種“零佣金”模式,但這種探索最終宣告失敗:既未提高房屋成交效率,也未降低租客成本壓力。
毋庸置疑,鑑於房租人力原材料“三高”壓力十多年來一直存在,讓餐飲行業早已告別高利潤黃金時代,進入肉搏戰階段,外賣對餐飲行業有着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對“堂食”生意好的商家是增量補充,對生意差的商家,則是一種新生機會——這從疫情兩年來,如果不是外賣行業,不少餐飲商家難以存活就可得到證明。因此《經濟日報》對此評論:如果商家沒有收入,哪怕佣金從20%降到2%,商家還是撐不住。
這意味着,相比單純降低佣金,對外賣平臺應用長期主義去評估其價值:一是要求平臺交易規則透明,責權分配清晰。二是平臺如何幫助更多餐飲商家降本增效,創造更多的價值。
有觀察人士認爲,去年5月推行的費率透明改革化,確實沒有做到百分百所有人滿意,但某種程度體現了外賣平臺重要探索的未來思路:明確告知商家技術服務費是佣金,同時又把履約服務費——也就是配送服務費的選擇權交給商家自主選擇。
一部分商家,目前看上去已經受益。“費率透明化後,最爲直觀的就是成本支出更少。”廣州張騰記燒臘負責人稱,相比以往,每一單會減少8毛錢成本,一個門店月銷量有5000多單,可以省下4000多元的成本。
相比成本節省,更重要的是能否推動商家根據自身優勢、需求,去重估外賣市場的價值和盈利邏輯。
從“極點商業”多方瞭解來看,由於外賣業務量彈性增減,收取的履約服務費比例不再統一,爲追求更多利潤和收入,有的商家會傾向於選擇距離近、價格較高的訂單。比如長沙蝦友匯燒烤城,80%以上訂單都是配送距離3公里以內的近單,做好“附近3公里”生意後,店鋪整體營收增長了10%。

另一些商家則有不同生意經。遼寧瀋陽經營多年的“喜辰水餃”,從3年前每天幾十單外賣,到如今外賣月單量過萬,老闆孟先生琢磨出了“3公里內外”的運營攻略:85%比例來自3公里內,佣金每月會節省支出6000元-8000元;15%來自3公里外,雖然成本有增長,但可以拓展口碑。
問題是,上述案例,是否適用於所有餐飲商家?是否可以讓上述商家,一直保持盈利增長態勢?
顯然不一定。“餐飲是一個很難構築護城河的特殊行業。”李輝就認爲,無論是堂食還是外賣,消費者都在隨時變化餐廳、口味和需求,這種變化幾乎沒有成本,也並非低價、優惠券就可以取勝,導致餐飲行業用戶黏性相當低。
“三高”壓力難解下,這一切顯然考驗着外賣平臺、餐飲商家的綜合運營能力。多位觀察人士就認爲,餐飲行業線上化、數字化趨勢浪潮不可阻擋,外賣對絕大部分商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破局手段,“因此單純普降佣金,並非紓解餐飲行業困局正解。而外賣平臺、商家如何合力共贏,也將是長期性的探索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