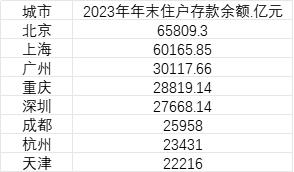專訪鄭永年:中國應在數字文明時代起到引領作用
當前,數字經濟已成爲穩增長的關鍵力量。2021年全國數字經濟相關企業超1600萬家,全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GDP佔比近40%。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修訂終審通過,首次標註97個數字職業,反映出我國數字經濟領域蓬勃發展的態勢。
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主辦的“新時代下的數字經濟發展與治理”研討會在深圳召開。研討會匯聚了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等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的著名學者和各領域專家,從技術突破、風險管理、機制探索和應用領域等多角度切入,探討了新時代下數字經濟的國內外發展動向與未來潛力,爲數字經濟發展與治理提供了前沿思想和創新路徑。
在此次研討會上,21世紀經濟報道圍繞中國在數字經濟時代的機遇與挑戰,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數字經濟戰略專委會主任鄭永年進行了專訪。鄭永年認爲,數字經濟領域更要強調統籌兼顧發展與安全,要通過開放來提升競爭力。

鄭永年。資料圖
中國要引領數字文明發展
《21世紀》:你認爲過去十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哪些特點?
鄭永年:當前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實際上是從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興起時奠定的。現在我們對於與數字技術相關的社會經濟現象有很多種說法,如“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等等。其實我更傾向於使用“數字文明”這個表述,一個更綜合的概念,也與過去我們所說的“工業文明”相對應。因爲,我們既要重視數字時代的經濟效應,也要看到社會、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數字化”影響。例如手機其實就是數字文明的一個載體,而不僅僅是數字經濟的成果。
中國在數字領域的很多方面,已經處於先行者的地位。近年來,我國平臺經濟快速發展,已經是我國GDP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在經濟與社會轉型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一方面,平臺經濟解構了原有的經濟社會生活模式,大大提高了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推動技術和產業變革朝着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進,有助於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各個環節,也有利於提高國家治理的智能化、全域化、個性化、精細化水平。另一方面,平臺對社會也產生了複雜的影響,平臺經濟的發展也面臨着一些挑戰。
回顧這10年數字經濟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黨中央把發展數字經濟上升爲國家戰略,而且這一戰略在各個地方逐步得到落地實施。例如長三角、珠三角,甚至是內地許多城市,都在大力推進5G網絡、大數據中心和智慧城市建設,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新基建,區別於以前我們所說的公路、橋樑、港口、航空港、高鐵等硬基建。目前中國已在消費數字化、產業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政府社會治理和服務數字化、社會政治參與和個人權益維護的數字化五個維度全面發力,消費領域的數字化成爲主流,生產領域中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迅速,“東數西算”等成爲新基建的重頭戲,電子政務已在全國推廣並不斷成熟。改革開放撬動了我們的經濟發展,帶動了數字經濟這樣一個新的發展形態,從國家到地方,對數字經濟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對的,也符合大的趨勢。
目前全球領先的互聯網公司、科技巨頭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歐洲、日本都還缺少大型互聯網公司。所以在當前的數字文明時代,中國不僅不能缺席,更應有動力也有基礎去引領這個時代。
統籌兼顧發展與安全
《21世紀》:你所說的“中國要引領數字文明”,需要注意哪些問題?應做好哪些準備?
鄭永年:關鍵是要處理好互聯網領域的發展與安全(監管)問題。一方面要看到平臺經濟對國家治理帶來的挑戰,以及數字領域存在着激烈的大國競爭。以FAANG爲代表的美國頭部平臺企業,不僅主導着美國國內的平臺經濟,更是深度介入了全球事務,它在成爲全球化的核心抓手的同時,爲世界各國構成了嚴峻的治理挑戰。在經濟領域,平臺經濟的飛速發展在構建新型經濟模式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如衝擊現有市場秩序(比如不公平競爭)、抑制技術創新發展(比如扼殺式併購)、損害消費者利益(比如個人信息濫用)、侵犯勞動者權益(比如算法剝削)等現象。
同時,平臺經濟加劇的全球範圍內社會分化問題也值得重視。掌握了這些新技術的人和能夠有效利用這些技術的企業家獲得的財富越來越多,而其他人羣的收入沒有得到明顯提高,貧富不均越來越嚴重,這種情況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尤其突出。這樣的經濟不平等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近年來民粹主義氾濫的根本原因。
在社會領域,平臺算法和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信息繭房”現象,“信息繭房”塑造着全球年輕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其中一些激進主義的思潮對傳統社會道德造成了衝擊。在西方的政治制度條件下,這些數字化進程帶來的副作用也使得民粹化趨勢進一步加劇。
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一些不合理的監管措施對互聯網企業發展可能造成一定影響。目前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都受到社交媒體的深刻影響,在此過程中,發展與安全、政府與社會、企業與社會的很多關係都要理順,數字經濟不光是一個技術的問題。
數字技術本身是中性的,是爲人類服務的,發明創造和技術革新可以用來解決社會問題,也可能帶來社會問題。數字文明的良性發展不是一個自發的、被動的過程,它需要社會制度的引導和配合,需要我們積極地爲之創造適宜的制度環境。其中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從而讓社會的每個羣體都能享受到科技和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成果,這就需要一種能夠對社會做全局性的動員和協調的機制。
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優勢就是相比西方資本主導的社會,中國能夠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但在此過程中也要注意平衡對企業創新活力的呵護。例如數字經濟領域中的一些大型企業,若從於社會、市場有益的方面來看,它們因爲擁有紮實的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有能力生產質量過硬的產品,能夠爲行業裏的中小企業提供公共品以及產業鏈支持,我們要引導這些大型的互聯網企業往這個方向發展。
以遊戲產業爲例,我們要科學地看待遊戲產業的社會經濟影響和作用。從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它在解決就業問題方面發揮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因此我們要把它好的一方面發揮出來,同時也儘可能地將它的不良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所以在數字經濟領域更要強調統籌兼顧發展與安全。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還要強調開放。
推動數字經濟企業走出去
《21世紀》:今後一個時期內,應該如何更好地激活和發揮市場經濟主體活力,推動數字經濟企業走出去?能否談談你的建議。
鄭永年:上世紀80、90年代以後,中國形成了強大的製造業產業鏈,儘管在一定時期內大部分企業位於偏產業鏈中低端的環節,但因爲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而當時世界上主要經濟體也是以開放姿態積極擁抱全球化,所以全球市場的有效配置得以形成。數字產業也是同樣道理。
首先,數字技術的發展應該要能跟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相抗衡,具有技術競爭力。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浪潮下,我們與美歐發達經濟體是相向而行的,這些發達經濟體也都希望主動向中國開放,獲得大規模市場的紅利。
然後是規則制定與更完善的監管。在當前逆全球化浪潮迭起、國家間貿易摩擦加劇,甚至是美國試圖對中國進行產業鏈脫鉤的情況下,我們應當比以前更加開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數字經濟領域的擴大開放,並不是說不要監管,相反地,也要完善相應的制度和規則。歐盟和新加坡雖然沒有像中美一樣湧現衆多互聯網科技巨頭,但它們都率先發力建立起完善的數字經濟監管規則,讓數字科技企業在合法合規合理的範圍內取得良性的發展。
我們要考慮如何既能全面融入數字時代、擁抱數字文明,同時又能保護公民的個人權利和隱私。數字化不但賦能於產業,也賦能於個人。在這個時代,越能保護個人的權利和隱私的規則和制度,就越能走向世界。
所以說,在數字文明時代,中國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實現可持續包容性發展,還應該起到引領作用,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爲構建人類更美好的未來作出貢獻。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我們要堅持不干預別國內政,加強國際基礎設施和國際公共品共享,堅持創新發展要共享,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作者:洪曉文 編輯:陸躍玲)
責任編輯:吳劍 SF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