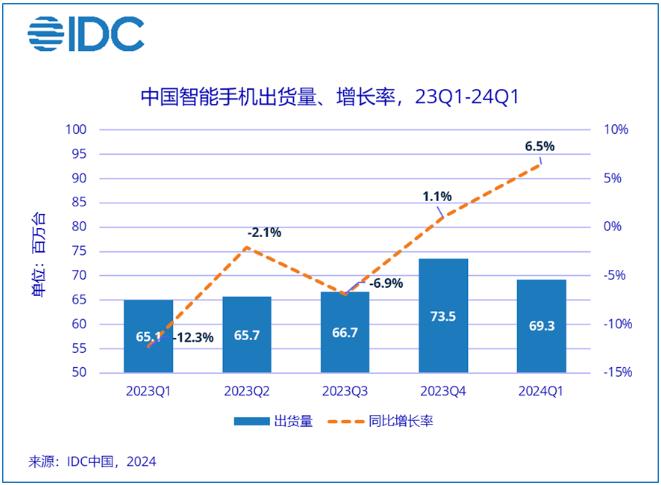10萬用人缺口背後:鄭州富士康的兩難考驗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記者/李秀莉
實習記者/陳銀霞
攝影/大白
人員缺口
11月17日,是鄭州富士康新員工張軍第一天正式上崗的日子。
鄭州富士康一共三個廠區,張軍要去的航空港廠區,是富士康全球所有工廠裏最大的一個。每年9月份,iPhone新機發佈會後,一直到12月,都是富士康的生產旺季,也是所有產線拉滿的時刻,鄭州航空港廠區更是承擔着全球約一半蘋果手機的組裝工作。但今年的生產旺季,對鄭州航空港區的富士康來說,有點特殊。
晚上7:30,張軍換上無塵服和鞋子,準備進入車間,開始夜班工作。車間很大,目測能容納上千人,但這晚,仍有部分生產線處於關閉的狀態,另一些正在運轉的生產線旁,也空着不少工位。“我聽一個老員工說,如果滿負荷開工,一個生產線上都人挨人,密密麻麻的。”中途上廁所時,張軍看到垃圾堆積如山,讓人無處下腳。乾涸的水漬在洗手池的表面形成一層裂紋。他猜測,車間可能是剛開放不久,還未來得及打掃。
張軍的工作內容是檢查蘋果手機的外殼,如音量鍵、攝像頭等硬件的安裝是否有錯誤和遺漏,然後再放回生產線上,傳給下一道工序,這項工作一般要兩個人,但這天晚上,他對面的工位始終空着。坐在張軍旁邊的工友告訴他,自己剛從方艙出來,原本所在的另一個部門,因爲疫情,“人都跑光了”,剩下的人只好被合併到其他部門。富士康航空港區一共分東西兩個廠區,他們所在的K區位於東廠區,主要包括像張軍這樣的新員工和陽性轉陰的老員工。
老員工口中的“跑”開始於10月底。根據媒體報道,富士康疫情在10月9日左右出現端倪後,因爲信息不透明、園區管理和防疫能力等問題,恐慌情緒在員工間蔓延,從10月26日開始,大批員工離開富士康。

2022年10月30日,華夏大道徒步返鄉的富士康員工
張飛是鄭州航空港區的一名人力中介,在富士康門口開了一家店鋪,平時以招募快遞日結工和富士康普工爲主。他向本刊記者回憶了富士康員工“大逃亡”時自己經歷的一幕。那是10月28日前後,自己正在廠區裏辦事,有兩個女工攔住他,“說要一人給我200塊錢,讓我給他們送去一個地方,大概10公里遠”。疫情還在持續,張飛沒敢答應。“你猜然後怎麼樣?她們說,哥,不行的話,你可以給我們找個住的地方嗎?我們不住富士康,只要出來住就行,給你錢。”張飛感到震驚,“就誇張成那樣,寧可跟男的住一起,連安全都不顧了,也要走。”後面張飛勸她們,要是宿舍沒陽性,就回宿舍,要是有,真想出來,可以去港區附近的一些橋底下。“但她們畢竟是女生,可能也害怕,後面她們走了。那是正式‘大逃亡’前一兩天。”
張飛已經在鄭州航空港區做了七年多的中介,他告訴本刊記者,富士康每年不同月份的用工人數會隨需求波動,大致有兩個招工旺季,第一階段是春節後的一個月,一般招幾萬人,彌補春節前流失的人口。第二階段是7~10月,每年這個時候,蘋果發佈新品手機,再加上國外的聖誕節,國內的“雙11”、春節等,市場需求旺盛。作爲蘋果手機最大的代工廠,爲應對增加的訂單量,富士康會提高生產線和用工人數。“平常富士康的用工人數,保守估計在十五六萬人左右,旺季能達到30多萬人。”
今年也不例外,9月8日,蘋果公司發佈了iPhone 14系列新品。據媒體報道,富士康是該機型最大的代工廠商,佔iPhone 14系列整體代工比例七成左右,同時也是高端iPhone 14 Pro系列機型的主力代工廠商。富士康早在兩個月前就開始爲此做準備,在一篇發佈於官方微信公衆號的文章《今年高峯已提前,返費高達一萬元》中提到,自7月17日面試起,有效出勤55天且在職90天的新員工,根據不同崗位有不同獎金,派遣工最多能拿到的返費爲1萬元,小時工最高工資達每小時28元。
爲了應對每年用工人數的波動,富士康會將員工分爲三種類型:正式的全職工、派遣工、小時工。其中,小時工以小時計費,每幹滿一個月,月初發一部分工資,月末再返回一部分差價;派遣工次之,底薪2000元,幹滿三個月給返費;正式工底薪2000~2200元,沒有差價和返費一說,但是有五險一金和加班費,工作年限越久、加班費越高。每年招工旺季,增加的主要是更具靈活性的派遣工和小時工。
另一位返鄉員工阿凱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提到,疫情之後,他所知道的返鄉員工裏,大多是像他這樣的小時工和派遣工。據另一位富士康中介的說法,富士康一般會將有一定技術性含量的崗位分配給正式工,派遣工則主要從事輔助類崗位,因此大批派遣工離開後,最受影響的可能是裝配手機殼、電池等輔助性崗位。
阿娟是選擇留下的工人,她向本刊記者描述人員缺口不斷變大的過程,“富士康一個車間裏,人數由低到高,分爲線、組、課、部幾個等級,從幾十人到數千人不等,疫情發生後,一開始,幾個部的人組到了一起,隔了幾天,一個課的人都湊不齊,到最後,一個線的人都不夠用了。甚至連線長都跑了”。阿娟所在的生產車間,正常情況下,一個線體有約400名工人,10月底之後,“基本都走完了”。剩下爲數不多的工人和其他線體合在一起,每天工作10.5小時,但生產量只能達到此前的40%。

2022年11月6日,鄭州富士康園區內,防疫人員進行環境消殺
11月7日,蘋果公司發佈聲明,因受疫情影響,富士康鄭州工廠目前的產能大幅降低,新款手機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的出貨量會出現暫時下降。“我們正在與供應商密切合作,以恢復正常的生產水平,同時確保每個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公告說。
11月10日,富士康母公司鴻海董事長劉揚偉在第三季度法人說明會上說:“以鄭州來說,在一個超過20萬員工的廠區,要兼顧防疫規定以及正常生產需要很強的管理能力……河南省政府明確表示會全力支持富士康,以最快速度來撲滅疫情……我們會在最短時間內努力回到正常產能。”
根據本刊記者採訪的多家人力公司的說法,大概從11月7日開始接到富士康的用人需求,總指標在10萬到12萬人。
緊急招工
陳肖是河南優米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的人力,她告訴本刊記者,11月10日接到富士康的招工需求,條件和以往明顯不同。首先是用工年齡,從此前的45週歲以下,放寬到48週歲。其次是薪資待遇,除了每小時高達30元外,還享有四天的隔離生活補貼,補貼標準按照入職時間長短,每天從100元到400元不等;在職滿30天額外享有3000元穩崗津貼。“算下來,第一個月保守估計1萬多元,後面兩三個月7000~9000元。這個補貼力度前所未有。”陳肖說,高薪吸引下,一週之內,公司已經招聘2萬~3萬人。
優米人力是富士康的一級中介代理機構。2015年開始,鄭州富士康提出和有實力的代理機構直接簽約合作,優米人力就是其中之一。陳肖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合作的前提,除了資質齊全,還要有一定經濟實力。“第一年合作要給廠區交1000萬元保證金,第二年之後,每年交50萬元。”發展到現在,鄭州富士康一共有六家長期合作的一級代理。其中,五家負責河南省內的招工,各自獨享特定區域,業務範圍不重合。另一家則專門負責省外招工。
千島勞務資源有限公司駐上海負責人龐小白告訴本刊記者,他們負責的招工範圍就主要以省外爲主,集中在上海、蘇州、崑山一帶。但在這波招聘中,80%以上是在外務工的河南籍老鄉,“到11月,已經不是電子廠的招工旺季,再加上今年大部分手機賣得不好,其他品牌手機的代工廠要不了那麼多人,所以普遍工資低。趁着這個機會,很多人就選擇回老家了”。外省返鄉的員工需要在省內隔離三天後再進廠,龐小白說,這幾天,鄭州中牟縣、航空港區一帶的隔離酒店已經住滿了人。後來者都安排在焦作、洛陽、開封等周邊縣市的酒店裏隔離。
一級代理拿到招工任務後,除了一小部分直招外,大部分會分包給下一級代理。以優米人力爲例,其合作的二級代理一共上百家,優米給它們按天支付管理費以及人頭費。“往年推薦一個人一般150~400元,這次最開始是500元,後面漲到了800~1000元,而且是一次性給。”一位二級代理告訴本刊記者。爲了拿到這高額的人頭費,二級代理們除了自己直接招人外,還在附近鄉鎮招募了一批業務員,他們大多有在外務工的經歷,認識的人多,通過微信羣、朋友圈、抖音、快手、親朋好友等發廣告,拉人頭。
除了仰賴市場的招聘體系外,河南省政府也參與了此次緊急招工。在河南省,富士康是一家特別的企業。根據河南大學副教授陳肖飛在其論文《勞動力視角下跨國公司地方嵌入與區域發展戰略耦合機制——以富士康鄭州投資爲例》中的說法,2011年鄭州富士康開始招工,那一年也成爲河南省農業人口省內轉移人數高於省外輸出人數的拐點。除了創造就業崗位,富士康對鄭州的外貿貢獻也極爲突出。以2020年爲例,富士康全年出口總額達到316億美元,佔鄭州進出口總額的80%、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0%。
因此,每當富士康有人力上的緊急需求時,地方政府都會施以援手。早在2012年,爲滿足iPhone 5系列手機的生產需求,鄭州富士康開始對外招募約20萬名員工。當時,河南省雖然是著名的勞務大省,但大部分人習慣到廣東一帶打工,留在省內的勞動力並不多,在此背景下,河南省政府出面,將任務層層下派,要求每個鄉鎮招募30~50人去富士康,甚至將招工指標納入政府工作考覈,與此同時,聯合省內的職業學校,組織學生到富士康實習。最終,在政府、企業和社會機構的多方配合下,20萬人很快招滿。
這一次也不例外。幫助富士康招工的指令很快下達到了省內各地。駐馬店是此次招工的重點區域。駐馬店一家中介機構的負責人衛東告訴本刊記者,11月7日,他參加了一場由當地人社局統一組織的會議,會議內容針對富士康的緊急招工,共五六十家本地中介參與。“駐馬店勞務公司多,九幾年就開始做人力資源,在全省勞務輸出裏面排前四。”衛東說,“當時是說計劃在駐馬店市招1萬人左右,當然越多越好,由中介和鄉鎮一起完成。”除此以外,還有周口、新鄉、信陽等環鄭州地區。
除了藉助於中介,各地政府也在鼓勵鄉鎮幹部直接招人。在一個洛陽市某村村民展示給本刊記者的鄉鎮幹部微信羣裏,有村幹部自發請願帶親戚和兒子去富士康。另一位河南省周口市和平社區的工作人員則告訴本刊記者,除了富士康給到的待遇外,11月19日之前報名的人,社區額外再給1500元補貼。
最終,中介和村鎮招到的工人,由各地市人社局統一接收。蔡先生是駐馬店市開發區人社局的一名工作人員,也是此次區隔離-閉環管理的總負責人,他告訴本刊,人員報名後,先組織在當地酒店隔離,三天後,再點對點閉環轉運到富士康招募中心。從7號市政府的任務下達之後,蔡先生已經和局裏的其他同事連軸轉了一星期,最終將幾百名工人送達富士康。
來到富士康的人們
11月13日,第一批報名者抵達鄭州富士康。
從大巴車上下來,張軍看到鄭州富士康報到大廳的門口已經停了一排車輛,從車牌和車身上的紅色橫幅看,有駐馬店、漯河、信陽、周口等地的,加起來一共有200多人,大部分是30歲以上的中年人,年輕人很少。“我估計第一批都是來試水的,要不是生活所迫,人家不會來。”

2022年11月13日,首批新招募的員工陸續抵達鄭州富士康
張軍今年46歲,河南信陽人,說話時帶着河南口音,他原本是一名木工,往年都在老家周邊的建築工地上幹活,一年能賺六七萬元。疫情這兩年,“蓋新房的越來越少”,作爲地產業最末端的一環,張軍受到的影響直接而明顯——活兒越來越少了。今年的光景更慘淡,“一個活兒也沒有”。張軍不得不轉行,在信陽溮河區的“網紅一條街”上租了個攤位,天氣熱時賣涼皮,天氣涼時賣麻辣燙。生意最好時,一天可以賣兩三百元。但好景不長,進入冬季,疫情捲土重來,封控的區域一天天變大,網紅一條街上的客人在變少,生意開始變差。到10月,一天賣不了100塊錢。眼看年關將近,11月9日,當看到中介的朋友圈裏發佈富士康招聘消息時,張軍第一時間報了名,“先把這個年過了”。
蔣梅則屬於“外省迴流”員工。她在東莞的電子廠裏做了兩年,工資最高時可以達到每小時22元,今年訂單量變少,工資一降再降,等她離開時,已經變成每小時16元。再加上所做的工作需要用到眼睛,已經43歲的蔣梅適應不了,10月27日,她辭工回了老家信陽。本希望在本地找點活兒,但每月工資大都只有三四千元。所以,當她看到鄭州富士康每小時30元的工資時,立刻報了名。
通過中介報名後,蔣梅聽說老家母子河村政府也在組織人去富士康。她將自己的情況報給了村幹部,“我問村裏是不是有指標,他說是的是的,我說我已經在信陽的酒店隔離,準備去了,他高興得很,說那就把我的名字報上去。他還說村裏就去了我一個,其他人都不願意來”。
報名完成,接下來是三天的集中隔離期,張軍和蔣梅被安排到信陽市區的某賓館裏,每天下樓到附近的社區核酸檢測點做一次核酸。11月13日,隔離結束,11位信陽工友在一位當地交警的護送下,坐車前往鄭州。車子一路幾乎沒停,當從高速公路下來,進入鄭州航空港區時,城市看起來依舊空空蕩蕩,公交車也已經停運,路上只有極少的行人和私家車,路兩旁的商鋪全部關着門。
第一批新員工被分到富士康的裕鴻公寓,小區一共15棟樓,每棟10層,每個房間可住10個人,一共可容納數千人。在這裏,還要繼續隔離三天,其間由社區志願者提供盒飯。和蔣梅同宿舍的,是一位來自新鄉的女性,30多歲,聊天時蔣梅得知對方是村幹部,“說是被‘拉壯丁’來的,行李就帶了一個小包,裏面是防護服,酒精噴壺,免洗洗手液,別的好像啥也沒帶,連換洗衣服都沒有,當天晚上八九點的時候,趁天黑,她就偷偷跑掉了”。
11月16日,結束三天隔離後,第一批新員工坐上大巴車,早上7:30從宿舍出發,半個小時後到達富士康廠區,大家按叫到的工牌號一一分組,領取勞保用品和鞋櫃。不少鞋櫃裏留着上一撥工友離開時沒來得及拿出來的東西,工作人員又重新清理櫃子,一直到下午5點多,才坐上大巴車返回宿舍。

富士康新老員工分開居住。這是改造後的天成公寓,該公寓後來提供給陽轉陰的老員工居住
離開還是留下?
雖然在政府的大力張羅下,鄭州富士康的第一輪緊急招工湊齊了需要的人數,但疫情對一個勞動力密集大廠的挑戰並沒有結束。
11月17日早上,剛上了一天班,張軍在微信羣裏看到,裕鴻公寓出現了核酸檢測十混一陽性,要求所有人馬上做單管檢測。“到第二天微信羣裏就說有五個人被隔離了。”同一天下午5點多,蔣梅坐上大巴車去富士康廠區上第一個夜班,途中正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我們的電話裏傳來一陣亂哄哄的聲音。“有個人健康碼突然變成紅碼了,正在讓她下車。”蔣梅向我解釋。
本以爲只是小範圍的感染,但來到車間後,蔣梅才聽說自己所在的生產線上有十幾個人因爲核酸檢測異常剛剛被拉走,因爲人數不夠,也沒有管理人員從中協調。11月17日這晚,蔣梅所在的生產線最終沒有拉起來,60多個工友在車間裏閒坐了一晚上。
一天之後,裕鴻公寓個別公寓樓開始被封控管理。張軍所住的宿舍被貼上了封條。張軍宿舍的另一名員工,被分配到廠區安全總務部門,負責進出車間的安檢工作。20號下午4點半下班後,被主管要求搬到廠裏住,兩個小時後,裕鴻公寓開始要求封控管理,人員只進不出,每天將盒飯送到宿舍門口。

正在搬宿舍的員工,他們中的有些人在短短一個月裏搬了3次宿舍,有些人直接住在廠區內
一邊需要補充人手,穩定產能,以支撐今年的“蘋果”新品出貨季,一邊又要應對傳播力極強的病毒在新增人手中可能產生的傳播,這是2022年冬天,鄭州富士康面臨的嚴峻考驗。而病毒的無孔不入也超過了人的想象。“我們來之前還在當地隔離了三天,進富士康之前都是健康的。”張軍對本刊記者說,僅有的兩天上班時間,也都由廠區用大巴車點對點閉環轉運,但進廠後不久,陽性依然在工人羣中出現了。在張軍發給本刊記者的視頻裏,11月20日,裕鴻公寓大門口已經被拉上柵欄,由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把守,道路旁是臨時搭建的物資帳篷。不時有工人拿着行李,準備坐上門口的轉運車輛離開。張軍不知道他們將被拉到哪裏,也不知道小區具體的感染人數,“反正每天都有被拉走隔離的”。

園區內等待轉運的富士康員工
張軍也想走,但他算過一筆賬,現在回去,需要自己叫車來接,單獨來接一趟是2000元錢。回到老家信陽,再集中隔離7天。“費用自己出,一天一兩百”,算下來,拿不到3000元的全勤獎不說,還要自己再花三四千塊。但已經有新來的人在陸續離開。
11月18日早上8點多,張軍正在睡覺,被一陣爭吵聲吵醒,他走到樓道里,聽到樓上有五個周口口音的工友正在和富士康工作人員爭吵,“他們想走,但富士康工作人員不讓他們自己走,說必須要等人過來接”。張軍聽到,幾個周口口音的人開始打電話,一直折騰到將近中午,五個人提着行李離開了宿舍樓。張軍所住的宿舍原本有10個人,到11月19日封控之前,也走了四個。
不少富士康新員工告訴本刊記者,對新老員工混合辦公的安排表示擔憂。鄭州富士康航空港廠區以雍州路爲劃分界線,東邊爲東廠,包括K、L、G區等廠區,西邊的爲西廠,包括A~F區,根據一份富士康內部的通告,疫情發生後,禁止東西兩廠區穿插上班。其中,老員工在連續五天核酸陰性後,到西廠區上班,新員工和陽性轉陰的老員工在東廠區上班。“我第一天上班時,聽老員工說,他們剛從方艙出來的,都不是天天做核酸,說是體內已經有抗體了,做了也是陽性。”張軍回憶,“那我和他一起工作,肯定害怕。”

富士康現在實行錯峯進餐,午餐時所有人分開坐,每人發一份盒飯
具體害怕什麼?本刊記者的採訪裏,好幾位進廠的工人都提到,既然自己敢來,就不怕這個病毒本身,怕的只是染上以後沒人管。至於“沒人管會有什麼可怕的後果”,誰也說不清,只知道染上後會被拉走。拉去哪裏?過什麼樣的生活?沒人告訴他們。而正是這種未知,滋生了最大的恐懼,並在人羣中蔓延。
11月23日上午,張軍發給本刊記者的一段視頻裏,一羣富士康員工正在情緒激動地向廠區相關負責人提出對目前疫情防控手段的質疑,“在宿舍裏做的核酸,顯示異常,但是健康碼是綠的,爲什麼?我已經不相信核酸了,在這個地方確實都已經害怕了,我們有可能都是小陽人……是不是在把我們當敢死隊?”張軍告訴本刊記者,視頻中的人爲豫康新城華鴻小區的員工,剛進來不久,因爲要和老員工一起在車間工作,害怕被傳染新冠,希望可以拿錢走人。
11月24日晚,富士康發佈公告:“對於選擇離職返鄉的同仁,公司本着人文關懷精神,對返鄉同仁給予1萬元費用,含薪資、隔離費、誤工費、車費等各類補貼。”並提到:“爲了讓大家安全有序返鄉,政府會統一安排車輛組織輸送。掃‘離職碼’辦理離職登記後上車前先支付8000元,返鄉登記掃‘乘車碼’後四小時內再支付2000元,此費用由政府公信力擔保。”
張軍所在的宿舍,六個人裏走了四個。張軍也登記了信息,拿到1萬元補貼,於11月24日晚回到老家信陽的隔離點。但也有不少人選擇留下來。風波過後,富士康的生產線仍然在繼續。對這個矗立在豫中平原的龐大工廠羣來說,生產是它最重要的使命。根據當地媒體的報道,12月初的富士康廠區生產線、街道、餐廳都已逐漸恢復人流。報道寫道:“始終不停工不停擺的企業,將在做好疫情防控各項工作的同時,以高昂態勢保持穩產高產,力爭實現‘全年紅’。”
(文中阿娟、張軍、蔣梅、衛東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