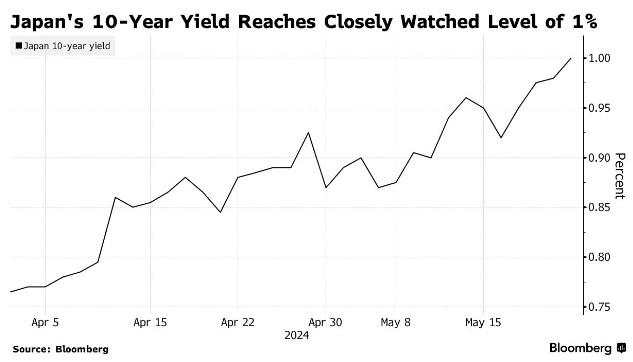【日本研究】孟凡禮 王文涵:廣島和平紀念館的戰爭紀念特點與作用評析
摘要:戰後建立的廣島和平紀念館具有側重“戰爭受害”的顯著特點,對於“片面”二戰史觀的塑造發揮了一定作用,而戰後國際反核運動的不斷發展,又使廣島成爲日本進行“反戰”宣傳以及宣誓“和平”的重要資源。通過對廣島和平紀念館戰爭紀念特點與作用的評析,可以加深對戰後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的認知,對全面評價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的發展也有重要意義。
作者分系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天師大政治與行政學院研究生
關鍵詞:廣島和平紀念館 戰爭紀念 戰爭受害 和平主義
內容提要
如何紀念二戰以及選擇對“加害”還是“受害”的強調,是戰後日本社會進行“戰爭紀念”時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廣島是日本作爲二戰“受害者”和“加害者”雙重身份的集中體現,其戰爭紀念的內容與特點也因此具有典型象徵意義。廣島和平紀念館是戰後廣島市進行戰爭紀念的主要設施,存在明顯側重展示“戰爭受害”、忽視加害者身份的現象。通過對廣島和平紀念館戰爭紀念特點與作用的評析,可以加深對戰後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的認知,對全面評價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的發展也有重要意義。
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肇事國,在未進行充分戰爭責任清算的背景下,日本關於戰爭紀念存在法理上“戰爭批判”與意圖上“戰爭肯定”的潛在矛盾性。特別是在外部缺乏強制力量、內部擁有強烈“戰爭肯定”意圖的背景下日本的戰爭紀念存在趨向於淡化侵略者形象的問題。將本國遭受的戰爭受害作爲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基礎,成爲戰後日本戰爭紀念設施所普遍遵循的基本邏輯。原爆使廣島成爲日本遭受二戰破壞最爲嚴重的城市之一,使得“戰爭受害”擁有廣泛社會心理基礎。戰後建立的廣島和平紀念館具有側重“戰爭受害”的顯著特點,對於“片面”二戰史觀的塑造發揮了一定作用,而戰後國際反核運動的不斷發展,又使廣島成爲日本進行“反戰”宣傳以及宣誓“和平”的重要資源。
1“戰爭受害”與廣島和平紀念館的建立
作爲軸心國主要成員,日本在二戰期間所進行的侵略戰爭給亞洲鄰國帶來巨大災難,是戰爭的主要加害者、二戰的元兇之一。在二戰後期,伴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不斷推進、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特別是美軍對日本本土進行的大規模戰略空襲以及對廣島、長崎所投放的原子彈爆炸,使日本本土遭受嚴重破壞。對於“戰爭受害”的總結與強調成爲日本戰後重建的一項重要任務,包括厚生省、經濟安定本部等都進行了戰爭受害調查並提供了具體數據。戰爭結束後不久,在1945年9月4日、5日召開的帝國議會臨時會議上,東久邇首相作了題爲《導致戰爭結束的原委》報告,這也是關於日本“戰爭受害”的第一次正式報告。
原爆給廣島帶來的巨大破壞是直接且深遠的,這爲戰後日本社會圍繞戰爭性質與責任的爭論增添了新內容,併成爲爭論的一個焦點。一派認爲原爆可以抵消戰時由日本軍國主義所犯下的暴行。這一派以戰爭遺族會爲代表,在日本政壇擁有廣泛影響,且其戰爭“受害者”觀念更能刺激民衆情感而引起共鳴。另一派則主張原爆是帝國主義政策失敗的表現,主張利用原爆遺蹟質疑、批判日本的殖民主義政策。這一派以日共、全國教師工會等爲代表,其觀點主張雖以歷史事實爲依據、符合戰後世界的發展趨勢與潮流,但在原爆所帶來的滿目瘡痍映襯下卻顯得蒼白無力。總之,原爆帶來的毀滅性打擊使普通民衆產生了深刻“戰爭受害”心理,以戰爭遺族會爲代表的右翼力量爲模糊戰爭責任積極利用這種“輿情”,使戰爭受害意識在廣島不斷蔓延。
另一方面,美國在戰後實現了對日本的單獨佔領作爲原子彈的投放者,當然不能容忍對原爆“積極”意義的反對與否定。戰後擔任廣島復興顧問的美國中尉約翰·蒙哥馬利就曾堅稱廣島慈仙寺所建設的“廣島市戰災死歿者供養塔”,應當取名“國際和平紀念塔”而非“戰禍佛事塔”,體現了美國對於原爆的態度。同時,在戰後廣島的重建過程中,日本政府還高度依賴美國援助,美國政府的態度自然會反映到關於原爆的各種不同類型紀念活動中。
至此,決定戰後廣島戰爭紀念“走向”的各方博弈格局基本形成。一方是普通民衆,原爆給其生活帶來了巨大破壞,心理創傷需要安撫;另一方是國會以及內閣中圍繞戰爭責任、戰爭反思問題出現的不同政治力量,以主張淡化侵略色彩的右翼力量爲主導;第三方是堅持原爆正當性的美國佔領當局,不允許抹殺二戰時期反法西斯盟國的正義性、堅持日本對外行爲的侵略性。在不同力量的角力與博弈下,“和平紀念”成爲各方能夠接受的關於戰爭紀念的最大公約數,也是各方樂見的一個結果。這一結果導致在廣島的原爆紀念設施中,普遍將核武器而非它的使用者視爲最大罪惡。而原爆主體的缺失,也使人們不再去追究核武器之所以被使用的原因,爲日本政府逃避戰爭責任提供了可能。廣島的戰爭紀念帶有了先天片面性的特點。
“和平紀念”由此便被嵌入到廣島戰後戰爭紀念的活動進程中。1948年6月20日,廣島市議會決定建立廣島和平紀念公園。1949年5月11日在廣島籍參議院議員寺光忠提議下,“廣島和平城市建設法”在國會進行表決並獲得通過。7月7日在廣島舉行全民公投,91.2%的選民投了支持票。1949年8月6日《和平城市建設法》生效,給廣島建設相關和平紀念設施提供了財政保障。在普通市民、地方政府以及“原子彈爆炸災害資料保存會”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參與下,廣島和平紀念館於1949年開始建設,1955年新建築落成、開館,館藏品5911件。
2側重“戰爭受害”的展覽
廣島和平紀念館位於廣島市和平紀念公園內分東西兩館並以天橋相接。紀念館的展覽佈局乃至整體建築,在迄今60多年的時間裏發生了較大變化,但紀念館展品選取的主要原則——以原爆破壞爲中心,未曾改變。
西館爲主體館,也是1955年開館之後的主要展示場所。該館是在原爆後初期所建,體現原爆巨大破壞力的各種遺蹟、遺物構成了其主要展示內容。“它將焦點集中於個人而不是政治或經濟”,並通過場景的模擬來重現這種危害,臺灣學者陳佳利將其視爲“重建人間之煉獄”。西館的展示可從類別上分爲兩大部分:物的展示和“人”的展示。物的展示包含大量受害者的遺物,如半融的酒瓶、破爛的學生服、燒焦的飯盒等,這些由一般平民或學生所擁有、日常用品的展示,往往能引發參觀者的情感觸動,帶來明顯的視覺衝擊。“被爆者證言”則通過親歷者的口述來傳達原爆的恐怖,形成日本人獨特的戰爭認知。西館的展覽是建立在原爆是“特別殘酷”“絕對不合理”這一系列毋庸置疑的假設基礎之上的。荷蘭日本問題專家伊恩·布魯瑪將廣島的戰爭紀念稱爲“情感型道德主義”是對這一特點的深刻總結。丹尼爾·塞爾茨也認爲廣島和平紀念館“主要是通過反對核戰來宣傳和平意識”,“並不是一個學習的地方”,而是如廣島和平文化中心將紀念館定位爲“世界和平的麥加”一樣,紀念館是一個民衆去祈禱以及尋求赦免核戰爭罪惡的地方。
東館是1994年重新裝修後增加的設施。在地上三層的展示區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位於一樓中央的原爆遺址模型以及原爆前後廣島市的地理模型。通過原爆前後地理模型的對比,可使參觀者直接獲取廣島市地理面貌巨大改變的信息,感受原子彈的強大威力以及廣島所遭受的傷害。二樓以“廣島的歷史”爲主題,展示“戰前的廣島”與“戰後廣島的復興”。
該館回應外界對其只展示戰爭受害的質疑,刻意增加了對日本“加害”方面的展示。如,在展示中也可見對廣島作爲“軍都”的歷史、“南京大屠殺”以及“朝鮮強制勞工”等日本對外侵略行爲的介紹。比如,對於廣島作爲“軍都”的歷史介紹:“1931年的滿洲事變展成爲全面對中戰爭。第五師團爲首先加入對中戰爭的部隊之一,並且一直維持前線作戰。……隨着1942年6月中途島海戰以及瓜達爾卡納爾戰爭的失利,戰局越來越不利於日本。1945年4月,第二總集團軍設立於廣島,並已準備在日本進行本土決戰的可能性,也因此大大地增加廣島的軍事重要性。”
關於南京大屠殺,在“南京淪陷燈籠矩陣”展示區解說詞中寫道:“中日戰爭初期,日本軍隊佔領了中國許多城市,並在1937年12月佔領了首都南京。……在南京,中國人被日軍屠殺。但對死亡人數卻存在不同認識,從數萬人到數十萬人。中國政府認爲死亡人數爲30萬人。”
可見,紀念館中對於日本“加害”行爲的展示存在避重就輕、刻意模糊的特點,與戰爭“受害”的展示形成強烈反差。
東館三樓的主題爲“核武的危害”,主要通過“暴風災害”“高熱災害”和“輻射災害”等幾個方面說明原子彈的巨大危害。
另外,在東館內還設有一個“外國人被爆者”的主題展覽。受廣島原爆影響的主要有朝鮮半島與中國的勞工、東南亞國家以及南北美洲移居日本的居民但在紀念館中卻沒有給予他們如日本人般的同等待遇,只在一個角落裏有簡單的文字說明。
根據東館展覽的結構設計,可以看出設計者對西館單純的“受害”展覽進行修正的努力,嘗試加入了一些“加害”、普遍性危害等因素。正如東京大學教授加藤歸一所指出的,在廣島和平紀念館1994年重新裝修之前,“展示戰爭中日本的加害行爲是不被許可的”。但通過考察其展示內容及展示形式可知,在東館中“刻意”增加的對於“加害行爲”的展示,是非常有限的。這種有限性表現在展現程度的侷限性以及展覽材料的單調性。學者太田滿認爲,雖然在廣島和平紀念館新增的東館中增加了對加害事實的記述,但在具體展示上依然是將原爆之外的東西排斥在外;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副教授、國際和平博物館副館長山根和代也指出,“與直白的表述原爆危害的事實不同,日本對鄰國如韓國、中國的侵略行徑在紀念館中很少被看到”。而且,在爲數不多、程度有限的關於加害行爲的展覽中,仍然存在展覽形式上的不足:缺乏“物”的展示。根據越智啓太對東京家政大學199名曾到訪廣島和平紀念館女生的問卷調查,發現“記憶率”與展示物的種類直接相關,實物的展示往往更能被記憶,而認知的形成則依賴由“記憶率”所帶來的心理衝擊。進行物品展示是紀念館的職能所在,廣島和平紀念館對於日本“加害”行爲的“文字化”處理,極大削弱了其在這方面的警示與教育意義。
3社會教育:塑造“戰爭受害”的片面二戰史觀
德國學者阿斯曼認爲,記憶不只停留在語言或文本記錄中,各種文化載體如博物館、紀念碑、文化遺蹟等在傳遞歷史記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將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傳統代代相傳。特別是,在日本二戰後民主改革過程中,美國佔領當局認爲博物館有助於推動日本民主化、和平化的進程,將博物館置於社會教育的核心而博物館的功能與作用也在明治維新後不斷被日本人所接受。日本政府在1947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中將教育分爲在校教育和校外教育兩大類,博物館②作爲“爲所有人提供學習機會和學習環境的機構”,被視爲重要的教育設施,開展定期不定期的學習活動、普及歷史教育是其重要功能。1951年頒佈的博物館法,則進一步確立了博物館在社會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進入80年代以後,博物館的實地考察成爲日本初等和高等教育的一門必修課,博物館在社會教育方面發揮的實際作用日益突出。
廣島原爆因具有“地域性”和“普遍性”特徵,對全國範圍參觀者與學生的修學旅行具有巨大吸引力。1955年開館以來至2017年4月,總入館人數接近7000萬人,除去不足500萬人的外國參觀者,日本本土參觀者約有6500萬人次。對於廣島和平紀念館在社會教育方面的作用,本文一方面以廣島和平紀念館留言薄爲素材,另一方面以廣島和平研究所2010年對中小學問卷調查結論爲依據,評價其在塑造二戰史觀、戰爭觀方面的具體作用。廣島
和平紀念館自1970年10月15日起,在出口處設置參觀者留言簿,讓參觀者表達其參觀感受及意見。紀念館選取1970年至2005年920條留言中的325條,集合爲《來自廣島的質問:和平紀念館的“對話筆記”》一書出版發行。
整體來看,在公衆留言中佔比重最大的是反對戰爭與嚮往和平(29%),此種反戰情感多是基於原爆後的慘狀而形成。未成年人的參觀感受最爲典型、直接,表現爲恐懼與震驚等。作爲戰爭紀念館,廣島和平紀念館在展現戰爭的恐怖方面有明顯效果,參觀者普遍感受到戰爭的殘忍性,但在戰爭歷史的教育方面卻作用了了。對於紀念館的這個特徵,也引起了部分參觀者的質疑。
日本公衆特別是未曾經歷二戰的青少年的留言,對於評價紀念館在社會教育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義。親歷者或遺屬往往會有主觀情感介入,而作爲一個“旁觀者”,其觀點與態度往往是參觀帶來的直接感受體驗。對於二戰後出生、未曾經歷戰爭的年輕一代來說,戰爭紀念館是他們瞭解、認識戰爭的重要渠道。而廣島和平紀念館在吸引青年人方面也採取了一系列,如在入場費方面,中小學生全部免費、超過20人以上的大學生團體免費。
廣島和平研究所曾於1968年12月、1971年7月、1975年6月、1979年8月、1987年12月、1996年5-6月和2010年8-9月先後7次對廣島中小學生進行“和平”學習的路徑與效果進行了調查。比較7次調查結果,發現關於“原子彈爆炸”信息獲取來源的變化最大——由電視轉向原爆倖存者,廣島和平紀念館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廣島和平研究所2010年調查報告,初次到訪廣島和平紀念館的學生集中在小學4-5年級(55.1%),而參觀感受更多是對於原子彈爆炸的“受害”印象與恐怖感加深(43.8%)。整體來看,原子彈爆炸的巨大破壞力所帶來的視覺衝擊,使青少年參觀者在驚奇與恐懼中結束參觀,很少能夠起到對於戰爭歷史的社會教育作用。
廣島和平紀念館在“展現”歷史方面的取捨,限制了其社會教育功能的發揮,同時,“片面”歷史觀唸的塑造,又成爲日本在戰爭責任問題上與周邊國家實現真正和解的巨大障礙。
4國際傳播:以反核重塑“和平主義”國家形象
“和平”是戰後日本政府所強調塑造的國家形象,以其作爲弱化並取代軍國主義形象的重要工具。對於和平國家形象的構建,“廣島的和平紀念館是一個適合用來做對外宣傳的窗口”。戰後以來,日本政府通過制定具體政策並積極推動,使廣島和平紀念館成爲廣島乃至日本的名片。比如,由聯合國裁軍審議委員會管理的“聯合國裁軍獎學金計劃”,將培養外交官“致力於裁軍的意志”爲使命,自1983年以來,每年有24名到30名不等的受訓外交官到日本進行學習訪問,截至2012年共計761名。這些年輕外交官在日本爲期6天的學習日程中,會專門安排一天參觀廣島和平紀念館。“聽到原爆倖存者的講話,是我生命中最受震撼的一件事情”“使我對和平有了新認識”,是這些年輕外交官們普遍的參觀感受。另外,根據廣島《中國新聞》的調查,二戰結束至2014年8月,超過155個國家的大使級以上政要曾到訪廣島其中82個爲部長級。近年來,每年也有50至60名政要到訪。
另一方面,在政府高層交流之外還有大量研究機構以及青年學生到訪,廣島和平紀念館發揮了重要公共外交載體的作用。此種民間形式的人員交流與信息傳遞,具有一般政府或官方層面所不具備的優勢,具有全面化、深層化與廣泛性等特點,對推動和平主義國家形象的全面擴展具有重要意義。
廣島和平紀念館真正被世界所廣泛關注,是在2016年G7峯會期間美國總統的到訪。美國總統於5月27日應邀到訪廣島,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獻花並“發表了超過預期的17分鐘演講”。作爲戰後首位訪問廣島的在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到訪具有非同一般的影響與意義。自2009年以來,日本廣島、長崎民衆曾先後6次向奧巴馬發出邀請,因此也有論調認爲這是“民間外交的成果”。美國總統雖然沒有爲71年前美國投下原子彈的行爲道歉,僅表示對遇難者的哀悼之意,但無論如何,美國總統到訪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特別是在日本公衆對於二戰歷史的態度方面。正像《聯合早報》一篇社論所指出的,“即便不道歉,訪問仍將助長日本右翼模糊二戰罪行的勢頭,加速日本政治的右傾趨勢”。訪問也引起世界對於廣島的進一步關注,在奧巴馬訪問的第二天即5月28日、29日,廣島和平紀念館的參觀人數達到13389人,包括2869名外國人;6月份遊客人數爲148462人比去年增加41.8%,而外國人增加56.5%。
根據國際著名旅遊網站“貓頭鷹”(Trip Advisor)在2014和2015年所發表的年度報告顯示,廣島和平紀念館連續兩年位居“日本前10博物館·美術館”第1名、“最受外國人歡迎的日本景點”第2名、“亞洲前25博物館·美術館”第3名。在來自世界各地參觀者的4900條點評中,“有意義”“震驚”“反思核武”“世界和平”等表述反覆出現,並感嘆日本政府保存原爆遺蹟方面的成就、稱讚其在和平教育方面做出的努力。
總之,廣島依據其自身獨特“優勢”,在世界反核、棄核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和平”逐漸成爲這座城市的重要符號象徵。同時,作爲代表日本國家形象的廣島市,也因在國際無核化運動中的突出作用而使日本的和平主義國家形象凸顯。只是在這種形象的構建中,日本政府“刻意”淡化了加害者形象。日本試圖以曾遭受原爆嚴重危害的廣島爲起點展現二戰歷史,這應當是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真正實現“超越”的起點,是對日本普通民衆、世界愛好和平人士所謂負責的態度,也成爲其邁向和平主義國家的真正開端。
對於二戰歷史的態度已成爲影響日本與周邊國家關係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也成爲東亞區域一體化發展中的重要障礙性因素。戰爭記憶構成一個民族記憶的主體,共同的榮耀或苦難經歷是推動民族主義發酵的重要因素,正確戰爭觀與歷史觀的塑造與培育便顯得尤爲重要。日本確實遭到了戰爭的巨大破壞,因原子彈而逝去的日本民衆也確實值得同情,但正如中國外長被記者問到對日本政府邀請外國領導人赴廣島訪問的看法時所指出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加害者永遠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憐憫之情不能取代理性反思,正視歷史永遠都是更好走向未來的前提。而“戰爭受害”與“戰爭加害”這一對看似矛盾的身份也並非不可融合,就像在廣島和平紀念館東館出口處一塊展示標語中曾寫的:“日本也有殖民主義政策並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對許多國家的人民帶來了不可估量的也是不可逆的傷害。我們必須反思戰爭以及戰爭的原因,而不僅僅是核武器。我們必須吸取歷史教訓,仔細辨別並避免軍國主義道路”,只是類似的展示與態度在日本的戰爭紀念館中並未成爲主流。(註釋略)
文章來源:《東北亞學刊》2019年02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衆平臺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