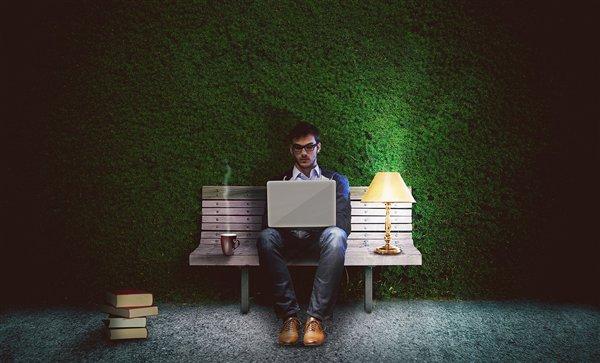農大的畢業生都去哪兒了?大學生畢業做職業農民有沒有明顯優勢?
摘要:從記者找到的中國農業大學就業生取向數據統計結果來看,至少就該校而言,從事農林牧漁業等一線農業工作的畢業生,正在逐年減少。記者隨後查閱了《中國農業大學2017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發現當年本科畢業生共2742人,其中987人直接就業,而1126人則選擇升學。
新京報訊(記者 曹雁南)又逢一年畢業季,就業成了學生與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題。中國農業大學官方就業統計表顯示,2018年,中國農業大學5144位畢業生中,僅有400餘人畢業後直接從事農林牧漁業,而縱觀2017、2016、2015年,這一數據正在逐年顯著減少。中國農業大學的畢業生們畢業後都去了哪裏?那些當年畢業後選擇農業的學生們如今境況如何?大學生畢業做職業農民有沒有明顯優勢?新京報鄉村頻道記者對此進行了一個初步調查。
資料圖:中國農業大學。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央企與生態餐廳 兩位室友的不同人生
於萌2011年從中國農業大學園藝學專業畢業時,還不曾想過自己如今會成爲一名建築類央企總部的職員,專門負責外事服務相關的工作。現在每天和審批手續打交道的他,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種子公司負責“十字花科和傘形科”新品種的生產與實驗。那時於萌的日常就是繞着全國跑,挑選地區安排對種子進行測驗,以判斷新種子是否有能力進入市場。
這份工作和於萌大學專業十足對口,但他只做了兩年。3000元月薪實在太低是一方面;頻繁在鄉村出差停留,讓於萌覺得自己每月近半的時間都處於信息閉塞狀態,這讓他很不習慣。
但真正讓他下決心轉行的,還是對農業類工作從業前景的擔憂。“我覺得這個行業很難實現普遍性的收入提升,即使增收也會少於其他行業,整體發展上對政策依賴性也太強。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感覺。”種種顧慮之下,於萌最終選擇了離開農業,經過幾番調整,他來到了現在的崗位上,“雖然專業荒廢了,但我不後悔我的選擇 。“
而和於萌的大學室友,則選擇了一個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庶,2011年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農學系,這是他依着自己的興趣選擇的專業,也是如今“最慶幸的事兒”。畢業後李庶先去了中國農科院做了一名科研助理,但很快因爲“研究理念不合”辭職。隨後的幾年裏,他在有機農場裏做過技術,在回龍觀開過饅頭點、蛋糕店,也辦過教育公司。而現在,李庶正和農友們合作,從全國各地的生態農場採購原材料進行麪點加工,在順義有了家自己的小餐廳,專門售賣生態有機主食,並計劃在將來開墾屬於自己的種植地。
換了這麼多職業,李庶終於在而立之年找到了自己人生最喜歡的事兒。“我一直就是想種地,從小就愛種花侍草。”現在,餐廳裏不僅有很多城裏人慕名開車找來,外賣方面也人氣十足。李庶平常活躍在順義,每週視情況而言“進城趕集”,參加不同的農產品集市,藉機宣傳自己的餐廳,爲將來發展尋找機會。
5144位畢業生 “務農者”不到500人
當年班級裏30位同學,李庶是畢業後唯一還在一線能接觸農業種植的。這樣的情況並不罕見,一位專門組織有機農業市集的專業人士就向記者感嘆過,這些年農大的學生畢業後從事農業的人太少了,她公司裏各行各業轉型過來的人都有,但農業專業出身的只有一位。
從記者找到的中國農業大學就業生取向數據統計結果來看,至少就該校而言,從事農林牧漁業等一線農業工作的畢業生,正在逐年減少。
中國農業大學共設有18個學院,涉及農學、工學、理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文學、醫學、哲學等9大學科門類。其中本科專業65個、雙學位專業10個、碩士點144個、博士點95個、博士後流動站15個。農業相關專業作爲中國農業大學的主攻方向,其在課程設置上也是重中之重。以本科爲例,記者在中國農業大學官網上找到了一份2013年招生專業名稱與課程方向表,其中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生物學院、動物科技學院、動物醫學院等專業設置全部屬於農業相關。水利與工程學院內也專門設有農業水利工程及農業環境建築與能源工程專業。而經濟學院和人文發展學院內除了國際經濟與貿易、金融學等專業外,同時還設有農村區域發展和農林經濟管理(農業商務)專業。這一數據,或者可清晰表達,農業專業在中國農業大學的課程設置裏比重極大。
與此同時,記者在中國農業大學的官網上找到一份《中國農業大學2018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依照國家統計局行業分類標準,中國農業大學 2018 屆畢業生就業行業前三位分別爲農林牧漁業,教育,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農林牧漁業作爲中農大的傳統就業方向,2018屆5144位畢業生裏有超過400位投入其中進行擇業。而2017年,具體數據沒有標註。而同一網站上,2016年的數據報告則表明,當屆有近500位畢業生選擇農林牧漁業進行就業。再把目光跳回2015年時,當屆選擇同一領域的畢業生則逼近700人。
中國農業大學官網截圖
具體到各專業上的就業數據,記者檢索發現,就本科專業而言,通過專業名稱直觀判斷,涉農專業除生物科學、葡萄與葡萄酒工程、園藝等理科實驗班畢業生全部升學外,其餘專業如應用氣象學專業共18人,而升學比例高達66.67%,出國比例爲11.11%。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爲本科中升學比例最低專業,共28人,升學比例7.41%,出國比例卻高達71.43%。
對於農林牧漁業人數的不斷減少,李庶認爲,這與收入直接掛鉤。“各個收入調查裏,農民收入都算是最低的,導致大家基本不願意從農。”
當然,從事農業研究、農業貿易也都算“從農”,但職業農民畢竟是基數最大最主要的部分。按照李庶的說法,記者查詢了農業部於2018年底公佈的農民人均收入統計,據調查,2018年我國農人人均純收入預計超14600元,較2017年提高了1000元以上,增速也在7%左右,和上一年基本相等。但相較於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及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而言,農民收入仍舊整體偏低。
班裏唯一的“女農民” 種草莓養活自己
雖然收入一般,但每年的畢業生裏,仍不乏李庶這樣“用愛發電”的人。劉香萍,湖南人,2013年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園藝專業,如今是一名日常生活在昌平小湯山種植草莓的職業農民。與李庶一樣,劉香萍也是她們班裏當年20多個畢業生裏,現在唯一一位在一線從事農業種植的人。畢業後,劉香萍先是在公司裏找了一份銷售的工作,但因爲“實在喜歡種地”,兩年後她辭去工作,和家人一起來到昌平承包起大棚,開始了她的草莓種植事業。
按劉香萍的說法,她做出這個選擇純粹是出於對種地的熱愛。她自述湖南老家裏一直有地,她從小跟隨家人在地裏勞作,對土地與種植業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選擇種草莓,原因則簡單的多,“聽別人說能賺錢”。
最早劉香萍和家人一起承包了兩個大棚,每個棚半畝地,草莓產值棚均2500斤。很快,兩個大棚變10個,到了2018年則擴展爲18個。而這些地裏的所有事務,日常全靠劉香萍與3位家人一起打理,最忙的時候每人每天最少工作12個小時。草莓採摘的高峯時期,她和家人每日手採300餘斤,要從下午開始,一直採摘到夜裏近12點。
採好的草莓最早沒有打開銷路,劉香萍只能自家開車拉着幾十斤草莓去昌平擺攤售賣。2018年開始,她在海淀與朝陽區分別聯繫了一家定點送貨的水果店,每天早晨6點出發送貨;今年,她又和學弟一起合作在電商平臺及微信上開始了草莓銷售。
繁忙的工作,並沒有給劉香萍帶來超高的回報,雖然收入也能養活自己,但她直言在當地只屬“一般水平”。劉香萍覺得自己種草莓的水平一般,因爲這是一件需要時間澆灌的技術。“種草莓是馬拉松,全程要全神貫注不能出錯。選地,摘苗,澆水,防止病蟲害,都要人仔細盯着。”但看着草莓一點點變化、豐收,劉香萍也覺得十足欣慰,這是她最喜歡的事兒。
劉香萍現在日常一直生活在昌平,只有送草莓時偶爾進城。她說她喜歡待在小湯山,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並且這個年輕的女孩兒認爲“物質慾望太麻煩了”。在她看來,化妝比種地還要麻煩。因爲種地更有意義,“化妝沒有價值,種地有人喫”。談到將來,劉香萍的觀點也很自由。她覺得自己不一定一輩子種草莓,在哪也不一定,但是唯一肯定的是,自己一定會和土地繼續打交道。
一名創業者的告誡:種植不是大學生所長
儘管農大畢業生務農比例是如此之低,但在有限的個例裏,居然確實能找到不太平凡的例子。
相比於劉香萍的“家族生意”,2010年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生物科學專業的陳躍文,如今在世俗意義上,顯得更“成功”,他也是諸多校友口中公認的“做得相當不錯”的一位。陳躍文畢業後沒有選擇像別的同學那樣繼續升學或者投簡歷就業,而是直接選擇了創業。“我大學時期就和同學合作進行過水果玉米的創業,從研究基地裏選擇貨源進行具體包裝銷售;也和朋友們合作進軍教育培訓領域,並用這裏掙來的錢投入農業創業。”雖然水果玉米的發展其後不算特別成功,卻在陳躍文心裏種下了創業的種子。隨後,他幾次挑戰創業方向,最終堅定在農業領域繼續拼搏。“之所以選擇農業放棄培訓,因爲農業還是未知的大的市場,且競爭小、空間大、有很多未知的可能。”
如今,陳躍文已經是一家頗有名氣的農產品公司的創始人,他的公司主要從事農產品品牌化及標準化,以品牌經銷和與網紅大V們合作的方式來對產品進行銷售。現在,陳躍文的公司有了自己的基地,今年有2000畝左右的自營基地,每年合作的水果基地也有幾千畝。
作爲如此成功的農業領域創業者,陳躍文卻對決心從事一線農業工作的校友們的前景不太樂觀,他認爲這個領域裏從事的大學生少是“好事”。“自己就是喜歡種地,也沒有錯,每個人的喜好和理想都值得追求。但要想清楚,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畢業後選擇除了興趣之外,還要創造價值,要取長補短。單純種地不是他們擅長的,任何一個農民都會種得更好。現在大家或許誇大了農業類大學生的專業度與做好的可能性,而選擇性忽略了傳統農民的專業度,從而忽略了每個行業都是有基礎與職業性的。”
陳躍文給出的現實建議是希望大家發揮所長,或者發揮別人不能發揮的價值。他舉例說,“農業種植領域,更專業及管理能力更強的人羣,其實往往是有多年甚至數十年經驗的農民及其中的種植大戶,而非農科院校的畢業生。種植並不是大學生們所長。”在他看來,即使大學生有志於從農,也是應該以溝通、銜接、技術積累及指導爲主,而不是實操爲主。
“前幾年,我以爲大學生畢業後從事生產種養殖屢屢遇到困難,只是銷路或經驗有問題,這幾年合作得多了,才發現他們的生產、管理、成本預計、風險評估等等都存在不足,確實不如傳統農民做得好。大學生可能擅長的是如何把這個行業的潛力和前景尋找、激活出來,把傳統農業及農產品,和現代化的消費需求進行連接。以此給農業及其從業者帶來更好的效益,降低行業風險提高穩定性。也可以給消費者帶來有價值的產品、服務和體驗。“
這是典型的創業者思維,因爲在陳躍文看來,種植就算是最小單元的創業,每個農民,都是個體創業者或者經營者,種植業也是競爭最激烈的行業。“一個大學生,種植經驗沒有,資金沒有,土地資源沒有,和普通農民很難競爭。”在他的工作接觸中,認識的成功者全部都是傳統農民和種植大戶,沒有一個是畢業五年內的大學生,“小規模種幾畝幾十畝的除外”。
升學成爲大學生們又一主要選擇
另一方面,陳躍文記得自己入讀的生物學院以科研爲學習主體,畢業時全獎出國的有三分之一左右,國內讀研的三分之一,而直接選擇工作的連三分之一都不到。這一說法,在中國農業大學歷年的畢業生就業統計裏,記者找到了客觀數據支持。
《中國農業大學2018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顯示,中國農業大學2018屆畢業生共5144人,其中本科畢業生2748人,1005人畢業後參加工作,就業比例達到36.57%。而當屆畢業生升學數則爲1110人(升學比例40.39%),以微弱優勢高於就業人數。此外,另有478位畢業生選擇畢業後出國。
就業與升學幾乎持平,甚至就業人數低於升學人數的現象,不止存在於2018年。記者隨後查閱了《中國農業大學2017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發現當年本科畢業生共2742人,其中987人直接就業,而1126人則選擇升學。如果再加上當屆541位出國畢業生的數據聯合統計,那麼2017屆的本科升學人數則遠高於就業人數。
對此,記者在2017年的就業質量報告中,找到了中國農業大學官方披露的2011-2017屆本科畢業生深造情況圖表,在這份統計裏,學校把國內外升學人數做了統一計算、對比。從圖中觀察,2011屆本科畢業生升學率爲44.99%,而到了2017屆時,本科畢業生的升學率迅速竄升至60.79%,並存在逐年上升趨勢。
中國農業大學官網截圖
越來越多的畢業生相較就業選擇了升學,是否存在農村就業環境不理想的問題?經濟學家杜猛認爲,這一情況意味着國家政策激勵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國家應該加大政策鼓勵,使年輕人相信未來在鄉村的職業前景等於甚至大於城市。”同時,鄉村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不得力的問題,也是影響就業的關鍵因素。杜猛認爲,年輕人如能在鄉村享受到能夠接受的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體系,他們自然願意選擇更加宜居的地方進行生活。
對就業環境的困惑,使得不少學生選擇以升學的方式換取更好的就業機會。《中國農業大學2017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中,碩士生就業比例高達82.36%,遠遠超過當年9.61%的升學比例。
孫偉,2011年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農學專業,畢業後他選擇繼續讀研,參加了學校的2+2項目(即讀研2年,校內做輔導員2年)。直至2015年碩士畢業,他正式留校做了一名輔導員。在孫偉近年來的學生工作中,他同樣感覺到升學是畢業生們的主要選擇之一。“一方面我認爲是由於國家擴招,這幾年研究生招生人數不斷加大。其次,目前很多用人單位正在逐漸提高門檻,很多以前本科畢業能做的工作,現在的門檻已經升爲研究生了。這也是一種導向。”
而除了就業與升學,公務員在記者的調查中也是畢業生們所選擇的高頻行業。除此之外,教育、金融、製造業等各行各業也都有農大畢業生的身影。
到農村去是“向上走”還是“向下走”?
劉楠,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探村博士聯盟發起人,長期關注鄉村問題。在他看來,畢業生們最終沒有選擇農業工作,是個人觀念與社會環境的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很多人還懷有偏見,認爲農村就意味着凋敝落後,農民教育文化水平低,做農業工作枯燥,從事農業難獲得社會認同。”同時,劉楠表示,大城市涉農的企業機構少,工資待遇偏低;而返鄉創業則需要資金和能力的雙重配合,很多畢業生無法承受相應壓力;很多地方農技人員老年化很嚴重,現有的基層農技推廣體系發展空間較小。
基於年輕人追求新鮮感和自我實現的現狀,劉楠建議當代農業工作模式應有所創新,現有農業發展模式、農產品的售賣等或可和新媒體結合,拓展生存空間。“在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風向標下,農業大學的畢業生大有可爲。但是很多問題要思考,例如,在新形勢下,如何優化農業大學的課程設置和培養方案,如何把學校目標和市場需求有機結合,如何開拓有趣有料有營養的農業類職業渠道,都需要動員各方行動者,獻計獻策。”
這一看法,也與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不謀而合。蘇海南表示,社會環境過去無意中對於農業相關工作的矮化,是導致很多畢業生不願從農的一大因素,“在輿論看來,農業相關工作的社會地位與收入都比高新技術、公務員或者二產三產等行業要差一些,這就無形中使得學農學生與學生家庭對這個行業望而卻步。此外,農口工作與當代年輕人嚮往大城市、追求‘高大上’的希望背道而馳,在傳統觀念裏仍屬‘向下走’” 。另一方面,蘇海南提出農業專業設置、教學管理與現代農業需要的脫離,也是畢業生“從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在校所學農業相關知識,後來發現不利於不便於就業。”蘇海南認爲,在傳統農業轉型現代農業的路上,大學課程調整、教學方法的升級也應該儘快適配。
對於農大較高的升學率,蘇海南認爲 “升學如今是普遍現象,不止農業領域,各個行業都是如此,在就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大家都在爭取更好的就業機會。”同時,對大學生從事一線農業工作,蘇海南表現出高度認可與支持。“這是一件好事。建立於愛好興趣之上的就業選擇是非常值得鼓勵的,也是大學教學的正道。學生們的知識儲備會轉化爲實踐技術,現在還只是他們積累量的階段,總有質變的那天。”
“師哥”陳躍文說不贊成大學生從事一線種植,劉香萍對此持保留意見,她也同意傳統農民在種植上更爲專業的說法,但未來卻不見得如此,尤其是在鄉村振興這一大背景下,“大學生現在是種不過農民,但大學生如果可以像真正的農民那樣腳踏實地去摸索去奮鬥,再加上我們已有的知識和眼界,前景只會更好。”
新京報記者 曹雁南 編輯 張牽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