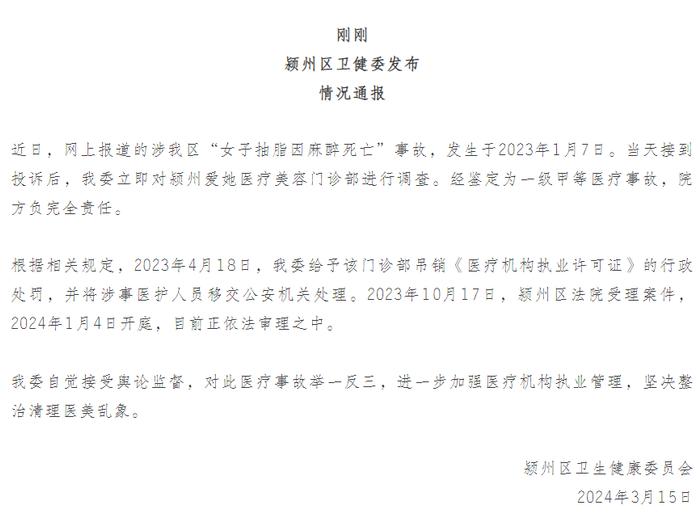散文:拔牙記
文/王祖芳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佈】
人上了一定的年紀,身體的器官就像機器的零件用久了一樣,這裏出點故障,那裏有點毛病,是很自然的。有的故障可能自己搗鼓一下就解決了,有的務必去找懂行的人。
我的牙齒因爲牙齦萎縮導致壓根逐漸裸露,而我偏偏又貪戀鯽魚頭的美味,在一次大快朵頤的時候,“咔”的一聲牙斷了,但它暫時還被牙齦拽着。這顆牙搖搖欲墜了三年,我小心翼翼地護着它三年,硬的不敢喫,沒法喫,冷的熱的不能喫,一喫就牙痛,最後這顆牙在我的無限遺憾中離開了。它離開後,旁邊的牙也孤立無助,不堪一擊,於是我就走向了一條補牙、看牙的不歸之路。
假期裏,我終於下定決心去口腔醫院拔牙。醫生耐心地告訴我下午不拔牙的原因,於是商定了一個上午去拔牙。那天早上,我早早地做好準備,來到醫院,這時已有一個病人在接受拔牙,我在門外等着。我焦急略帶些緊張地在醫院門廳裏走了一圈,找了找報架上放着的花花綠綠的書中有無我愛看的雜誌,結果發現全是有關牙齒方面的廣告小冊子,只好作罷,坐在門口等着,百無聊賴,看看其他來醫院的人的穿着,揣摩一下她們的年齡、職業、幸福指數等等,如此這般。其中有一對看情態是母女,女孩大概是準大學生,來進行牙齒整形。女孩不停地輕輕問:“會不會痛?”她媽媽不厭其煩地回答。我聽清她們的對話,惺惺相惜,立即把剛纔我打聽得到的答案告訴她:不痛。原來每個來看牙醫的人都把治療牙病看作一件痛苦的事情。人們在預料未知事情的時候喜歡先往不好的方面、難的方面想,所以常會採取逃避的態度。
輪到我了,躺在專用躺椅上,我睜大着眼睛,注意着醫生的舉動。醫生撥弄了幾樣工具,戴上口罩、醫用眼鏡、醫用手套,全副武裝後舉起針對着我的臉,我張着的嘴巴忍不住顫動了幾下。針扎進去的時候有一點刺痛感,刺了兩下,牙齦的裏外已各打了一針麻藥,一會兒功夫,醫生用鑷子又是起,又是拔,但是我一點都沒感覺到痛。好像看到醫生夾出來一個東西,我問:“拔掉了?”
醫生答道:“拔掉了。”
醫生又拿出一根針,上面有一段黑線,我緊張地問:“還要縫啊?痛不痛?”
醫生說:“不痛的。”
想想平時不小心針戳到手都很痛,現在先要針戳,還要把線在牙齦裏穿來穿去會不痛嗎?醫生大概看出我的心思:“縫兩針好得快,天熱要防止發炎。”
我張着嘴,醫生已經在抽線,接着打結了。咬着兩個棉球,我站了起來,感覺被打麻藥的地方成豁嘴了,但用手摸一下,嘴巴還在,再摸摸感覺像香腸脣。
拔牙過程出乎預料的順利,很輕鬆地就完成了一件醞釀已久的“大事”,如果不是五音不全,如果不是沒有一首歌能唱得出來,一路上我真想哼哼小曲,完全忘記了無法咬合的嘴中露着白色棉球,面目還有些猙獰。醫命不可違,醫生說咬棉球四十分鐘,我多咬點時間準沒錯。一個小時後我才取出棉球,發現牙根還在出血,拔掉牙的地方隱隱地空心痛,幸好臨走時醫生送給我五個棉球,於是拿出一個棉球塞入豁牙。一直等到一個半小時左右,我用手摸摸嘴脣有知覺了,又過了一會兒,嘴脣麻嗖嗖的,牙根的疼痛也來湊熱鬧,但完全不像水果店的售貨員說的那樣麻藥過後痛得要死,這點痛奈何不了我,看書寫字皆不受影響,除了喫東西。因爲中午喫飯不多,兩粒消炎藥喫下去,喝下去的水在胃裏直晃盪,沒過多久,肚子裏唱起空城計。
一週後,去醫院拆線,我問醫生:“我每天晚上刷牙以後從不喫東西,這牙齒怎麼還那麼糟糕呢?”
醫生說了這樣一句話:“口腔衛生是一方面,基礎也是一方面。”怕我不懂,醫生又說,“就比如汽車,有的汽車經得起碰撞,有的就不行。”這我懂。
基礎有的時候真就這麼重要,學習有基礎,人與人之間有感情基礎,房屋建造必須要有基礎,但是我始終相信後面的努力和付出也是必須的!不能坐以待斃,飯得喫,生活還得繼續呢。
(圖片來自於網絡)
顧問:朱鷹、鄒開歧
主編:姚小紅
編輯:洪與、鄒舟、楊玲、大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