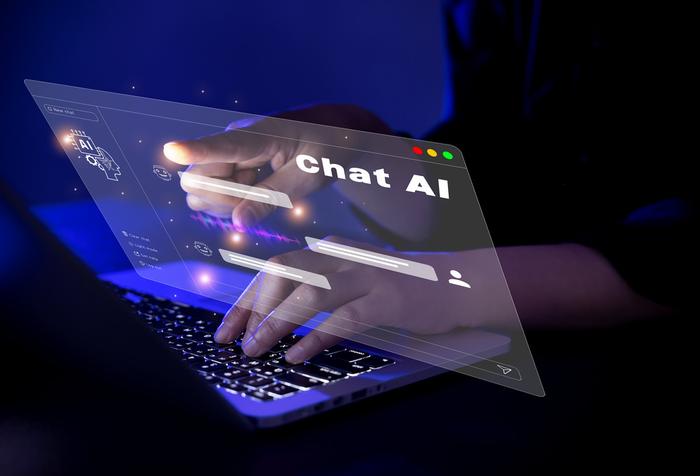毛坦廠的高考經濟:代陪讀"前景不錯”
被稱爲“亞洲最大高考工廠”的毛坦廠中學位於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廠鎮,每年都會吸引大批學子前來備戰,隨之而來的是衆多陪讀家長以及這些學生和家長帶來的高考衍生經濟。青年學子在這裏奮力拼搏,力圖追求更好的分數、前途與聲譽。中國教育的現狀和平民家庭對“魚躍龍門”的渴望,被典型地濃縮於此。近日,澎湃新聞記者實地探訪毛坦廠中學以及聚集大批陪讀家長的毛坦廠鎮,以尋求當地真實的“高考生態”。
十年前,隸屬於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區的毛坦廠鎮曾流傳着一句話——“來毛坦廠賣水果都能賺”。
這些年來,憑藉着“高考經濟”,確實有不少毛坦廠人“富裕了”。然而,也有不少因看中毛坦廠的“高考經濟”蜂擁而至的人們,如今卻面臨“賺不到錢”想要逃離的境遇。
代購,從“湧入”到“關門”?
毛坦廠中學禁止學生帶手機。於是,每到放學或假期,學校周邊的電商代購店總是人氣很高,學生在店裏通過登錄電商平臺下單購買,代購費每件5元,以衣服和鞋子以及生活用品居多。此前曾有報道說,這裏的電商代購,最瘋狂時,一天能掙三萬。
一個普通的週末,學校東門一家電商代購店裏坐着不少學生。老闆告訴澎湃新聞,有的學生甚至一呆就是一上午,所以很多店主爲了讓人流動起來,限定了購買時間。
放學後,校門口的電商代購店坐滿了網購的學生。
對於“日入三萬”的說法,老闆連連搖頭:“那是瞎說”。他說,雖然這個鋪面是自家的,每年不用擔心房租問題,但生意已不如以往,現在幾乎每天都處於虧損狀態,爲了搶生意,店裏已不再收取代購費,“算上電費和損耗,每天還要虧”。?
因爲自家房子離學校遠,租不了好價錢,眼看着毛坦廠中學越來越好,在外打工的蘭華(化名)10年前回來開始創業做生意。他回憶說,自己曾開過公用電話店,但因手機在陪讀家長中越來越普及而告吹。而後,他又聽說電商代購賺錢,於是開店做起了電商代購。不過,蘭華表示,電商代購雖說一單能收5元,但事實上,從學生下單、到貨、退貨等,需要花費很多精力,賺到的錢僅僅夠抵扣房租,有些入不敷出。
“一年房租41000,每天500塊都做(賺)不到。”老北門一家代購小店店主表示,幾年前聽說這裏的電商代購生意好做,便想着回來大幹一筆,但在這裏做了三年後發現,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可能前五年做生意賺錢那是賺錢,現在不行了”。
老北門東側的“樂淘淘”是毛坦廠第一家電商代購店。店老闆姓姚,如今30出頭,已在毛坦廠結婚安家,但他坦言,因鋪面租金一年要6萬餘元,與店鋪年收入相差無幾,自己也打算做完今年就把店盤出去,離開毛坦廠去大城市另起爐竈。“日入3萬那是吹牛。但剛開始那幾年確實挺掙錢的,特別是‘雙11’時,一天毛收入最多有5萬多。”姚老闆感慨,“(原來)平日生意好的時候,一天也能有幾千塊收入。”
姚老闆介紹說,2007年前後,他辭去了大城市的工作來到毛坦廠,花了3000多元租下一間鋪面半年的使用權,搞起電商代購。“那時沒錢,毛坦廠房子也租不起價,跟房東說先租半年,房東也同意。”他回憶說,剛開始生意並不好,一天只有幾單。“那個時候毛坦廠學生多,但還不出名,也沒有快遞點,我都是開車到六安市區取貨回來,每單代購費20元”。
幾年後,隨着毛坦廠中學的名聲越來越響,姚老闆代購店的生意越來越好。代購費也從20元降到了10元,降價的原因,是因爲每次往返城區的取貨成本相對固定,買的人多了,每單的成本就變少了,“收多了也不好意思。”姚老闆說,“那時專門買了輛三輪車拉貨,要不然貨太多,裝不下。(當時)毛坦廠基本上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快遞,都是我(店裏代購)的貨。”
相比那時 “忙不過來”的情景,現在的電商代購店清閒了許多,大多數店主爲了賺錢,在店裏同時經營起了打印、代收快遞、公用電話、賣電子產品周邊等生意。
放學後,學生在校門口電商代購店用公用電話給家長打電話。
姚老闆介紹說,這些年,有不少聽聞毛坦廠代購能賺錢的年輕人從打工的大城市回到這裏開店:“慢慢地就有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現在總共大概有十來家”。
如今,隨着移動網絡和移動客戶端的日漸普及,毛坦廠的電商代購生意已褪去了往日的光輝,逾半數電商代購店都貼出了“店鋪轉讓”的標語,年輕的老闆們都計劃着去大城市闖出一片天地。
全託,從“陪讀”到“管理”
全託——也被叫做“代陪讀”,毛坦廠中學校門口最常見的“招牌”之一。
如今在毛坦廠經營着三處全託中心的朱道羣,是最早嗅到毛坦廠代陪讀商機的人之一。工商登記資料顯示,由她自己擔任法人代表的“六安市毛坦廠家政服務有限公司”2017年7月31日註冊,經營範圍包括家政服務、餐飲服務。朱道羣告訴澎湃新聞,全託中心根據政府相關部門要求,都配備有相應的安全措施。比如鎮上每年在暑期都會牽頭對他們這一類的全託機構進行安全檢查,主要檢查範圍包括滅火器是否合理配置、水電是否規範使用、住宿學生是否符合人數限制等。鎮政府還要求租住房屋的學生家長簽署租賃證明進行備案,以確保政府部門和學校能準確掌握學生在外租住的情況。
朱道羣稱自己是六安人,今年50多歲。5年前在毛坦廠陪讀兒子時,在當地買了房,並且萌生了退休後“創業”的想法——做“代陪讀”生意。
“代陪讀”主要負責學生的叫早、喫住、日常生活,幫家長監督學生課餘行蹤等。
爲了方便學生出行,除了將自己買下的房子作爲全託中心的場所外,朱道羣還租下了老北門和東門口的幾處房間供學生居住,一個房間擺有兩張牀和書桌,雖然衛生間在房間外,但基本一一對應。
代陪讀機構的“連排”洗手間。
上學期間,朱道羣和在自家房子裏的學生們同喫同住。每天,她的鬧鐘清晨5點半就會響起,自己洗漱完,並幫學生們燒上開水後,她會挨着敲門叫醒熟睡的學生。學生每晚放學時,她會守在樓下“清點”學生人數。
朱道羣的三處全託中心共“管理”着百名學生(每處約30多人),每個學生根據住宿條件不同,一年收費在2至4萬不等。她表示,除去房租、水電氣、三餐的物料和人工成本,一年能盈利十萬餘元。
晚上11點半,代陪讀機構的管理員在宿舍樓下等着晚歸的學生。
在朱道羣看來,全託中心的學生,家庭條件都比較好,父母以做生意居多,“爸媽沒時間陪孩子、管孩子,送到我這也放心”。
對於“代陪讀”這門生意,談着“創業”經歷的朱道羣表示很看好其前景。?
跟朱道羣的“創業”不同,在毛坦廠做全託的71歲退休教師王麗(化名)說,自己做全託不爲賺錢,看着孩子考上大學,心裏就開心。
2009年,退休的王麗從老家張家店(離毛坦廠20分鐘車程)到毛坦廠陪讀自己的孫子。後來,孫子考上大學後,不少親戚、老鄉就請她繼續留在毛坦廠幫忙代陪讀。“每個月500生活費,幫忙給孩子燒飯、洗衣”,王麗說,今年陪讀了30多個學生,從高一到復讀生都有,“每天要給洗30件衣服”。
王麗一邊燒飯一邊注意着放學時間。
9年過去了,王麗依舊租住在毛坦廠中學東門和老北門之間的這處民房裏。房東告訴澎湃新聞,每年都有不少學生回來看望王麗,“剛纔就來了一個”。說到送走的畢業生,王麗自豪地說:“一共帶了96個畢業生,只有6個人沒有考上。”她代陪讀的一些學生畢業後,過春節、放暑假,還專門會到她家看望她,這讓她感到很溫暖。
在私人全託中心備受家長青睞的同時,鎮上一家酒店經營的全託中心在當地也有着不小的名氣。據該全託中心工作人員介紹,目前入住率在70%左右。每個學生每年的收費約爲3萬元,學生兩人一個標間,牀前擺有帶櫃書桌;男生女生分別住在不同樓層,每個樓層都安排了24小時輪班的生活阿姨;每天早中晚加宵夜,都由酒店餐廳負責。
相比私人全託中心而言,酒店全託少了“家庭”氣息,但“管理”卻更規範。而在不少當地人眼中,毛坦廠的代陪讀是個“香餑餑”。一位見證了毛坦廠鎮從大別山區不知名的小鎮到現在聞名全國的“高考工廠”的本地人感慨,“你別看現在這裏其他生意不好做,只要毛中在,代陪讀生意差不了。”
代陪讀機構公共區域貼有標語。
旗袍,從“生意”到“文化”
旗袍——對於陪讀家長來說意味着“旗開得勝”。隨着天氣轉暖,在毛坦廠的小路上,不時會看到一些身穿旗袍的女人。經過幾番詢問,她們多數會提到一家距離毛坦廠中學老北門不到百米的旗袍小店。
“這個花色很襯膚色。”“料子摸起來真舒服。” 4月24日晚9點,這家旗袍小店還是人來人往,四五個不同年紀的女人,擠在約1米寬的小過道里挑選着款式和布料,最年長的看起來有60來歲。
徐坤(男)正在幫客人測量尺寸。
臨近高考,鎮上旗袍店裏的生意一天天好起來。“基本做旗袍就是在4月、5月,到6月高考了,他們(陪讀家長)就會走了”,旗袍店老闆徐坤是個不到40歲的男人,他利落地用軟尺量着客人的尺寸,一邊在訂單紙上熟練地寫下數字,一邊對澎湃新聞說:“去年旗袍銷售量大的時候,一天可以賣十幾件。”
量身、剪裁、熨燙、縫製,每一個工藝徐坤都說得頭頭是道。他告訴澎湃新聞,自己做旗袍的手藝都是此前在北京打工時學來的。
徐坤的老家在離毛坦廠約10公里路程的東河口鎮,16年前剛初中畢業的他去到北京打工,10餘年間從對旗袍一無所知到當上私人定製的旗袍師傅。直到5年前,他偶然間發現了毛坦廠的商機,於是辭去了北京的工作,和妻子一起來到毛坦廠開了當地第一家旗袍店。
店門口,一位兼職的陪讀媽媽正在熨燙着布料的造型:“旗袍需要邊做邊熨,對裁縫的手藝要求很高,我原來在老家就是做這個的,完成一件旗袍(我)一般能拿到幾十元。” 徐坤告訴澎湃新聞,店裏一般有三個“員工”,流動性也大,因爲對手藝要求高,一般都是有手藝的陪讀媽媽主動“找上門”。
“去年高考的時候,有個家長穿旗袍被拍到了,(她穿的)就是我家做的旗袍。” 徐坤的妻子高清興奮地分享着去年看到新聞報道上出現毛坦廠陪考家長時的場景。
店裏的旗袍因材料和質地不同,價格從200-1000元不等。高清表示,買旗袍的人羣並不只限於有錢人家;家長訂旗袍也並不只爲孩子高考討喜,有家長會訂很多件,平時也穿,而有家長只會提前訂一件,等到高考再穿,“(有人)家裏三個孩子,就買一件,穿三次。反正條件好的就買好點的,條件不好的就買差一點”。
徐坤補充說,店裏夏天賣旗袍、冬天做大衣,除去人工和每年19000元的房租,在這裏開店一年的收入在六七萬,和在北京打工相比基本持平,“像昨天生意好,入賬(未扣除成本)有4000多塊錢,但一年也就這50來天生意最好,一到放假就沒什麼生意了”。
“年紀大一點的就穿唐裝,年紀輕、身材好一點的就穿旗袍,偶爾也有陪讀爸爸過來做衣服,但爸爸爲高考做(衣服)的會很少”。徐坤說,這5年,夫妻倆一共在毛坦廠開了3家旗袍店,一般早上8點開門,晚上12點關門。如果不下雨,晚上8至10點就是店裏生意最好的時候。週末,還偶有學生來店裏詢問,想給媽媽定做旗袍,“有女生過來看,說媽媽平時(陪讀)挺辛苦的,想給媽媽做旗袍。男孩子也有(來問的),有的雖然問了不買,但他有這個心,我們也感覺挺好的”。
徐坤說,他們夫妻倆見證了毛坦廠的旗袍從無到有、從有到流行的過程。
在毛坦廠常見家長身穿旗袍。
“原來沒有(旗袍店),毛坦廠做旗袍的,我們家是第一家。” 徐坤回憶稱,最近幾年隨着鎮上開始搞老街旅遊、旗袍秀活動,穿旗袍的越來越多,當地漸漸形成一種“旗袍文化”。“旗袍本身就是我國的一種傳統服飾,看到小鎮旗袍風氣一點點起來了,心裏也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