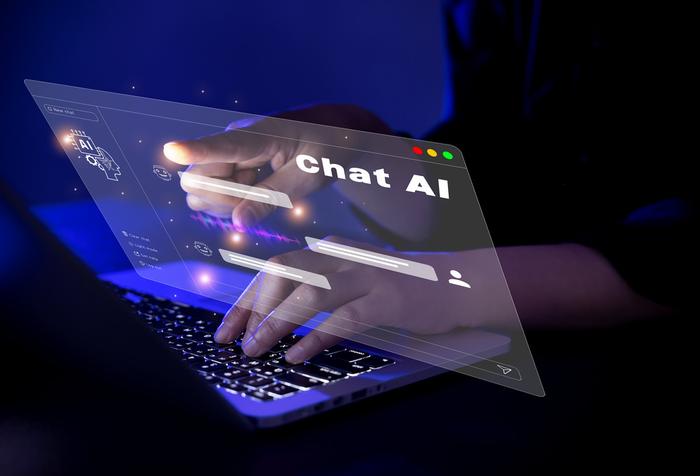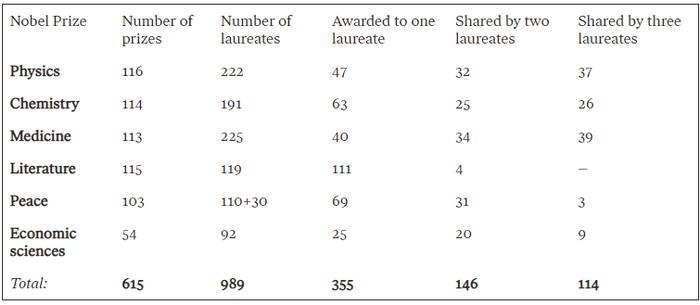著名作家曹文軒:幽默無用,要被中國人尊敬,就得端着臉神情嚴肅
張英
“中國人對嚴肅與幽默的偏重很不相同,因此對那些善於幽默的人往往都不能給予很好的待遇。要被中國人尊敬,就得端着臉神情嚴肅。”
6月6日上午,爲慶祝六一兒童節,騰雲讀書會“網絡DNA素養課”名師講堂在北京北四環西路66號舉行。
我們邀請了著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國際安徒生獎得主曹文軒,他帶了剛剛出版的新作《草鞋灣》,並從兒童文學創作到家庭親子閱讀,進行了分享。
本文爲獨家專訪,系首次發表。
《我的兒子皮卡》這套書,是根據我的兩個兒子的成長經歷寫成的,他們是故事主人翁的原型,根據故事需要,他們兩個人的故事,做了一點位置的調整。我把老大的故事變成老二,把老二的故事變成老大。但是小說故事主要是寫老二,老二叫皮卡。
爲什麼叫皮卡呢?他是一個小男孩,出生的時候很不容易,卡在媽媽身體裏一個地方了。可是“卡”這個字在我老家鹽城的方言不念“qia”,念“ka”,卡在那個地方,出不來,因爲人家不願意來到這個世界上。
皮卡這個小孩命特別大,因爲媽媽懷他的時候,有流產的預兆,然後住院。住院的時候,特別馬虎的拍B超的醫生告訴她:胎兒已經死亡,勸皮卡的媽媽早點動手術,不然會鈣化的,會有問題。這樣一個結論,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一個叫皮卡的男孩來到這個世界了,絕無可能了。
可是媽媽不死心,有一天她去北京中關村醫院,去看她的一個好朋友。這個好朋友不是醫生,他是行政工作人員。到了他的辦公室裏,沒有他,然後就問同事到哪了?說他好像到B超室去了,去看他的一個朋友。
然後皮卡的媽媽就走到了B超室,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好朋友就問她懷孕的情況。然後好朋友說,來,順便B超再檢查一遍看看。我印象特別深,當時我就坐在醫院的走廊上,皮卡的媽媽進去了。大概過了15分鐘,滿臉笑容還帶着眼淚說:“寶寶的心臟跳動得特別有力!”
不久,她原來住院的那個醫院,還給我們打電話說:“你們什麼時候來動手術啊?”我沒有責罵他們,把在中關村醫院檢查的情況告訴他們,他們啞口無言。我說,算了。你們差一點扼殺了一個小小的生命,他叫皮卡。
當然,《我的兒子皮卡》的故事,也不僅僅是兩個兒子真實的故事。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難以做到實寫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事情,就能夠把作品寫得非常圓滿的,不可能,一定有虛構的故事,這樣才能讓一部作品圓滿。
《我的兒子皮卡》對成長中的孩子會有很大的啓發性。家長們也可以從皮卡的成長之路,看到家長的苦中歡樂,以及關於如何陪伴孩子成長的啓示。在我的整個寫作的系列裏頭,《我的兒子皮卡》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作品,也許就是我們大家在心中所認定的最典型的兒童文學。
如果說《草房子》、《青銅葵花》不是特別典型的兒童文學的話,那麼《我的兒子皮卡》差不多就是最典型的兒童文學。我說不清楚什麼叫典型的兒童文學,但是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想在座的所有朋友,你們現在大概就有一個樣子,典型的兒童文學的樣子。
我爲什麼想起來寫這樣一套作品呢?第一,我不想浪費兩個好兒子的成長所提供給我的獨一無二的寫作資源,我就想我帶你們太辛勞了,那麼地辛苦,你們也該報答我,怎麼報答?就是把你們的生活,作爲我的寫作資源提供給我。我養你不是白養的,你得讓我寫十本書、二十本書,就是你們的故事,算是給我的報答。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第二個原因,是因爲我們看到了許多寫給兒童的作品,我感到很不滿意,就是覺得這一類的作品,一味地追求所謂的笑,搞笑,一味地籠絡兒童,一味地爲了銷量。所以我決心寫一套可以把它稱之爲文學作品的小說。就是說要對得起“文學”這兩個字,要有足夠的文學性,而不只是搞笑,不只是讓小孩喜歡,要寫一套文學性很強的書。
因爲在我幾十年的寫作經驗裏頭,我得到的結論就是一部書怎麼能夠穿越時間和空間,這有一個東西:文學。它必須是文學品,它必須是藝術品。只有當它是文學作品,具有很強的藝術性的時候,它纔可能成爲可以穿越時間,穿越空間永遠活下去的作品,不能一笑了之,應該讓那個孩子長久地記憶,記憶一生。這是我要寫它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我以前寫作品,大多數情況之下都是往高處走,孩子們看《青銅葵花》、看《草房子》,我想你可能會有這樣一個感覺,我是往高處走的,我儘量讓它在你看的時候會有一點點難度,而且我常常寫的是少年,年齡偏小的,幾乎沒怎麼寫。
所以我在《我的兒子皮卡》裏,決定從高處往低處走,寫一個年齡比較小的孩子的生活,寫一些通常的兒童文學作品,這是第三個原因。
兒童的閱讀與成人的閱讀有許多不同之處,小孩喜歡看一個形象,和自己一樣,慢慢長大,許多故事裏,有一個固定的形象,這本書裏是他,下一本書還是他,唯一的形象,寫了十本、二十本,乃至更多本書。很多小孩特別喜歡看的這麼一類的書,他喜歡形象的重複。比如說米老鼠、唐老鴨、不一樣的卡梅拉等等。許多形象成了經典,甚至成了一個國家的文學的驕傲。
如果我來創造一個叫做皮卡的形象呢?寫下去、寫下去、寫下去、寫下去,一直寫下去。我想給中國兒童文學創造一個形象叫“皮卡”。我以爲我現在已經走在了這條路上,有一個出版社,它專門成立了一個皮卡的機構,就是來主推皮卡這個形象。
說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一定要講講一個詞叫幽默、詼諧。皮卡與我以前的作品相比,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幽默。好玩,看完了以後你想不笑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對“幽默”這個詞的理解不一樣,或者說正是因爲我對“幽默”這個詞的不理解,導致了我對現在一些所謂的搞笑的作品不滿意,決定才寫皮卡的。幽默不是搞笑,幽默不只是搞笑。而且小孩搞笑很容易的,嘎吱他不就笑了嘛,撓他的腳板心不就笑了嘛,那麼容易。可是笑完了一無所有。
在我看來真正的幽默要達到什麼境界呢?智慧的境界。只有當你的作品,你所謂的幽默達到這個境界的時候,我才覺得它是我要寫的作品。
另外我爲什麼寫這個“幽默”,就是因爲我有感於幽默在中國可能是不夠發達的。我不是說我們這個國家沒有幽默,我也不是說中國人沒有幽默,中國人幽默感還是很強的。而且我也不認爲中國原來的文學都沒有幽默,《紅樓夢》裏頭沒有幽默嗎?《水滸傳》裏頭沒有幽默了嗎?《西遊記》裏頭沒有幽默嗎?豬八戒不讓你感到好笑嗎?都有的。
中國還有許多文藝形式是專門來製造幽默的象徵,就是讓你笑。但是中國對幽默的理解確實是不夠深刻的。在這個講禮教的國家,莊嚴、肅穆、嚴肅是他經常的面孔。中國人儘管在許多場合很幽默,但中國人將幽默場合限定得太死,他狹窄。
因爲中國人對嚴肅與幽默的偏重很不相同,因此對那些善於幽默的人往往都不能給予很好的待遇。要被人尊敬,你就得端着,板着臉,神情嚴肅。你老開玩笑,老愛幽默,人家就不把你當一回事,就不會把你尊起來。這很要命,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本性藏起來,到處裝作一本正經的樣子,到處作出一幅尊嚴的樣子。
在中國是嚴肅的人高於幽默的人,幽默是那些嚴肅的人所欣賞的,但他不去效仿。他也喜歡聽相聲,他也喜歡幽默,但是他不幽默。當然在特殊的場合遇到老同學了可以,在家裏也可以,但是在有一些場合他絕對不幽默。因爲你幽默得太多,這個人不能讓他當官,當官的人就是應該板着面孔。
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講,在中國呼籲“幽默”都是必要的。而在兒童文學這裏呼籲幽默就顯得更有必要了,因爲在中國的兒童文學裏頭長期經營,就一直缺乏這種品質。雖然中國的兒童文學也講情趣,但實際上這種思路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貫徹。
再說兒童情趣與幽默似乎也不是同一個概念。對兒童情趣的理解似乎也非常淺薄,根本不足以幫我們理解幽默的意義。我們今天有一些兒童文學,小孩很喜歡看,因爲它幽默。
但是這個幽默,第一淺,一笑了之,笑完了以後給你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第二這個幽默大概也只是中國的小孩會看了幽默。一旦翻譯成英文、翻譯成法文、翻譯成德文,這個幽默就蕩然無存。爲什麼呢?它所謂的幽默就是在語言上耍貧嘴。可是這個耍貧嘴一旦翻譯成英文、翻譯成德文、翻譯成俄文,它就不在了。
許多在中國大陸小孩看來非常幽默的作品,就不要說翻譯成其他語種到國外了。即使到我們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臺灣,它就根本走不開。臺灣的小孩根本就理你,這有什麼好笑的呢?
我想寫一個小說,想寫一套無論被翻譯成哪一種語言,它都是幽默的。因爲那個故事本身是幽默的,用英語表達也好,用法語表達也好,用德語表達也好,它一定會讓你感到非常地有趣。即是語言,語言所表達的那個意思幽默,而不是語言本身幽默。
所以我在寫《我的兒子皮卡》的時候,是帶了這樣一種想法去寫的。其實現在的皮卡已經有很多版本,它其實已經成立一個IP形象了,而且這個形象越來越鮮明。
這一套書是二十一世紀出的,作家出版社又出了一套。天天出版社又出了《我的兒子皮卡》的圖畫書,因爲書裏頭有許多東西,可以拿出來作單篇給小小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