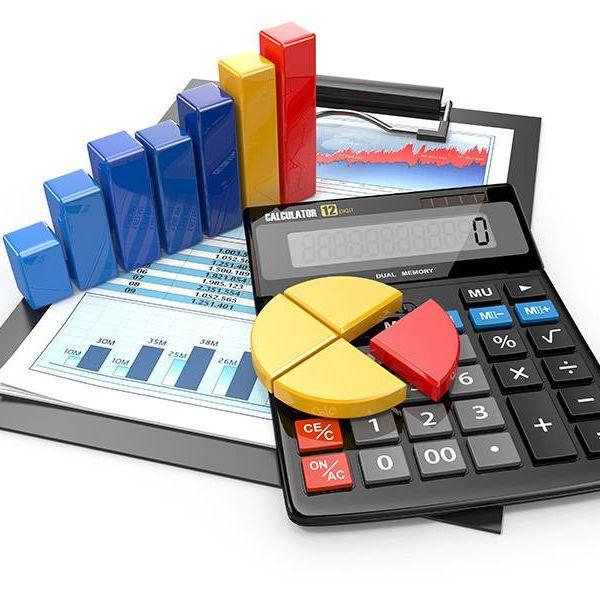短短十年,國產“鋼鐵穿山甲”何以躋身世界之強?
摘要:左邊的第一張圖的盾構機用於秦嶺隧道建設,是當時中國最貴的一臺設備,花費了3.5億人民幣的外匯。比如2017年,我們中國在莫斯科拿到了第一個地鐵項目,需要五臺盾構機。
來源:我是科學家iScientist
經過多年的探索和研發,中國盾構走在了世界前列,不僅滿足了國內需求,同時也開始大規模開拓國際市場。從依賴進口到走出國門,中國盾構如何讓“鋼鐵穿山甲”通達四方?中國鐵建重工集團掘進機事業部土壓盾構研究所副所長,工藝技術部部長孫雪豐爲大家帶來演講《從零起步,躋身世界之強的“鋼鐵穿山甲”》。
以下爲孫雪豐演講實錄:
我是孫雪豐,是中國鐵建重工集團掘進機事業部的一名工程師,我主要做的是盾構機的研發設計工作。

大家不一定見過盾構機,但是它們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的公路、鐵路和地鐵隧道,很多都是用盾構機來開挖的。它們形狀不一,大小、功能也各不相同;它們像鋼鐵穿山甲一樣,所經之處就會形成一條長長的隧道。

給大家看一張照片,這是我們在常德用到的盾構機,是不是很漂亮?我們中學有一篇課文叫《桃花源記》,照片中這個盾構機叫最美“桃花”。這個照片可能顛覆了大家的一個印象——地下工程機械都是傻大黑粗的。實際上,我們也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它不僅顏值高,而且也很厲害,一天能夠掘進幾十米。
在沒有盾構機以前,我們開挖隧道和地洞都是靠人工。上面是我們小時候熟悉的電影《地道戰》的片段。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八路軍聯合當地老百姓,在華北地區藏兵千百萬。他們當時開挖隧道,就是一鍬土、一鋤頭地把土開挖下來,然後再用土兜把它給運出去。

再到我們北京修建地鐵一號線的時候,採用是礦山法施工——也就是大家所理解的爆破。大家看一下這個工作面,它的環境是不是很差,是不是很危險?而且工作效率也很低,一天只能開挖幾米。

那麼盾構機是怎麼產生的?19世紀初,英國要從倫敦的泰晤士河底下修建一條隧道。但是這個隧道如果直接開挖的話,很容易塌方;人在底下施工的話,就會被淹沒。當時修建隧道的重任落在法國工程師布魯諾爾(Marc Isambard Brunel)的身上,他左思右想都沒有結果;直到有一天,他在輪船上看到船蛆在輪船甲板上鑽洞,從中得到靈感,設計了世界上第一代盾構機。
後人在第一代盾構機的基礎上不停地進行升級,由人工開挖逐漸到機械開挖,到現在,盾構機都是一個全斷面的刀盤。現在的盾構機也從最初的鐵匣子,變成了巨大的“鋼鐵穿山甲”。

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臺盾構機,直徑有17.5米,相當於七層樓這麼高。

我們再看一下“鋼鐵穿山甲”是怎麼工作的。前面的圓盤叫刀盤,相當於穿山甲的嘴,就是靠它來把前面的土壤和岩石開挖下來。然後這個刀盤的後面,有螺旋輸送機和皮帶輸送機,它們是穿山甲的腸胃,把渣土運輸出去。螺旋輸送機的四周有藍色的推進油缸,它是穿山甲的腿,這些腿頂在管片上面,把我們整個機器推着前進。
我們再看一個短片,看它具體是怎麼工作的。
十幾年前,中國不能夠自主研發製造盾構機。從2000年開始,中國開始新一輪的地鐵、鐵路和公路的大規模建設,這時候我們需要大量的盾構設備。
當時就需要大量從國外進口。中國如果沒有自己的盾構機,那麼工程建設的進度就得不到保障,技術也受制於人。

首先,國外的設備,非常昂貴。左邊的第一張圖的盾構機用於秦嶺隧道建設,是當時中國最貴的一臺設備,花費了3.5億人民幣的外匯。
第二,國外的設備,研發設計人員多在海外,對中國的工程地質不是很瞭解,不能夠根據我們的工程地質進行一些針對性的設計。比如右上第二張圖,是用於廣州地鐵建設的一臺盾構機。廣州有一種特殊的土層叫“紅層”,特別黏。所以盾構機的刀盤非常容易堵住,就沒法前進。
第三,國外的設備,生產週期特別長。他們要簽訂合同以後,纔開始準備原材料——所以說一臺地鐵盾構機,它的生產週期從簽訂合同到交付,總共需要12個月。而我們現在需要多久呢?只需要5到6個月。
第四,進口的設備,售後很差。我們設備在掘進過程中遇到問題,得聘請國外的工程師過來解決。但是售後週期很長,費用也很高——工程師從國外出發,就要開始計算費用,每天要1200歐元。如果需要國外的工程師長期駐守在工地,就要給他提供高檔的酒店餐飲。用在秦嶺隧道的這臺設備,我們當時想請國外工程師到我們項目上,那行,你先得幫他建一個標準游泳池,這是他們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說,中國如果要大規模地開展地鐵建設,要實現中國速度,我們必須要研發製造自己的盾構機。
我非常幸運,畢業以後就來到了我所工作的中國鐵建重工集團。那時候,國產盾構機的研發纔剛剛起步。

這個是我們研製的第一臺複合式土壓平衡盾構機,用在長沙地鐵2號線建設。當時我進我們單位的時候,廠房還沒有建好,我們就一邊搞建設,一邊搞研發,待在一個鐵皮房子裏面,冬天很冷,夏天很熱。
很幸運,我們沒有購買國外的圖紙,憑藉自己摸索畫圖,畫了十多萬張圖紙,製造出了我們第一臺盾構機。
但是製造出第一臺盾構機,纔是剛剛起步。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地大物博,工程地質複雜多樣。單一類型的盾構機不能適應所有工程地質掘進。

城市大部分都是軟土軟巖地層,適合用盾構機(圖中)掘進。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說重慶,地底下是堅硬的岩層;如果用盾構機掘進,刀具就很容易磕壞。所以我們給它設計了一臺硬巖適用的掘進機,業內叫做TBM(圖左)。再比如右邊,這個設備我們叫“頂管機”——它的設備比較短,可以看作是一臺迷你版的盾構機,它適合在短距離隧道(比如城市裏的過街通道)的地層掘進。
針對三種不同的地質,我設計了三臺不同的盾構機。但是如果兩種地層碰到一起了怎麼辦?

比如在廣州到佛山的一段城際鐵路建設中,有一條六公里的隧道——前面的400多米是軟土,中間的4公里是硬巖,再出來又變到軟土。怎麼辦?我們聰明的工程師把盾構機和TBM的功能結合在一起,就像給穿山甲設計了兩套牙齒、兩套腸胃。它根據地形的變化,可以自由地切換。
經過這些年的探索與實踐,我們完成了從適應單一地層到適應複合地層的突破。

近段時間,我又做了一些新的嘗試。這個是我們給上海設計的一批盾構機,這些盾構機具備一定的“思考”能力。我爲什麼做這件事呢?大家可能沒有進過隧道,所以可能不瞭解——隧道底下溫度很高,有40多度,還很潮溼,裏面的工作環境很苦悶。
怎麼讓我們的作業人員能夠解放出來呢?是不是可以少人化,甚至無人化?普通的盾構機都是人下達指令,然後盾構機來掘進;而我們這批盾構機,它前面有傳感器,所以能夠根據前面地層的變化自主調整設定參數,實現了從人工操作到人工監管的突破。

隨着國產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們現在的盾構技術不僅僅能夠滿足國內需求,還漸漸走出了國門。
比如2017年,我們中國在莫斯科拿到了第一個地鐵項目,需要五臺盾構機。大家知道,我們北京在建設地鐵一號線的時候,有一批蘇聯的老專家過來援助我們;現在我們回到莫斯科,相當於學生到師傅家給老師講課,壓力很大。
當時,這樣的重任落在我和我的團隊的身上。接到任務之後,我第一時間就飛莫斯科去當地調研,結果發現,難度比我預想的還要大。
爲什麼?

第一,莫斯科的溫度很低,一年的冰凍期有六個月,所以盾構機要適應零下30度的低溫。
第二,莫斯科具有很複雜的工程地質條件。盾構機的轉彎半徑特別小,掘進的時候坡度很大,然後還有40米以上的富水深埋地層;再一個,它要穿越既有的一些車站——在國內遇到這樣一個難題,就需要請專家過來援助,在莫斯科我們一下碰到了四五個。
第三,他們的施工習慣也不一樣。莫斯科有80年的地鐵建設經驗,如何讓我們的盾構機滿足他們的習慣,就需要我們進行深入考量。
第四,標準體系也不同。我們採用的是國標(GB),而他們有自己的標準。如何讓我們的設備符合當地的法律法規,是中國設備走出去的必經之路。
爲這五臺盾構機,我們特地開展了一些針對性的設計:我們研發了能夠耐零下30度低溫的主驅動系統,給設備做了很多加熱的裝置——普通設備大部分都做冷卻,而這個設備我們給它做了加熱裝置,這樣的設計應該還是第一次。

這個設備研發出來以後,深受當地人喜歡。他們用俄羅斯家喻戶曉的一部電視劇叫《爸爸的女兒們》其中五個女兒的名字來命名。這個設備到了當地之後,也覺得非常好。現在五臺設備,有三臺已經貫通了,並且創造了俄羅斯每天最高掘進35米的記錄。

回想十多年前,我們的設備完全依賴進口,到今天,我們中國的設備已經佔據了國內市場90%的份額,並且佔據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場。可以非常自豪地說,中國已經成爲全球高端地下工程裝備的第一軍團。
但是創新的步伐永不止步,我們會一直並且將來要繼續引領技術前進的步伐。

比如說我們已經成功研發出來的常壓換刀技術。這東西爲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爲盾構機在掘進的時候,是靠牙齒來咬前面前方的岩土;時間長了之後,牙齒容易崩掉。我們普通的盾構機,工人都是在進到前方的土體裏面進行換刀,水壓很高,非常危險。我們設計了這種常壓換刀的技術之後,人可以進到刀盤的結構裏面去,由高壓變成常壓——這樣我們的作業人員就可以很安全。

又比如說我們正在研發的隧道智能拼裝機器人技術——這個就是讓機器來代替人去進行管片的拼裝和TBM的鋼拱架安裝。在我們TBM掘進過程中,後方的巖體非常容易坍落,人拼裝鋼拱架就非常危險。我們用機器來代替人,就可以減輕他們的勞動強度,從而讓我們的隧道施工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21世紀是地下空間開發的世紀,我們盾構機研發會更加蓬勃——比如說我們在進行的超大豎井掘進機,還有面向川藏鐵路設計的超級掘進機。
向未知的地層掘進,充滿挑戰,但是我樂在其中。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