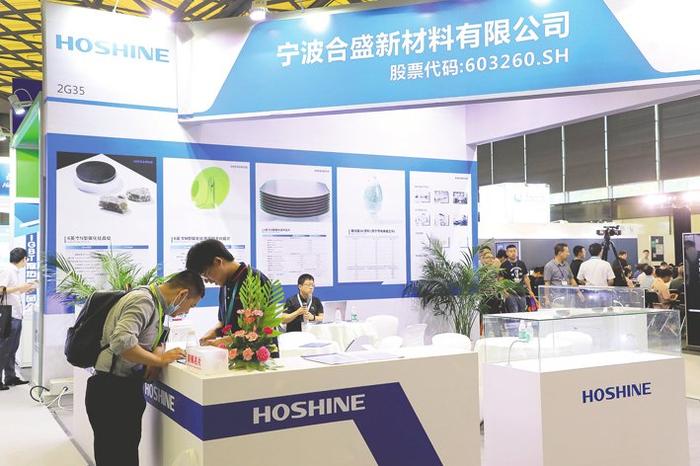超5萬江南棄兒被送北方收養 50年後靠DNA集體尋親
8月12日,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新塍鎮楊家浜,棄兒趙淑亮從600公里之外的山東莒縣趕來,與50年未見、現年84歲的母親沈阿大相見。他緊握住母親顫抖着的手,喊了聲“媽”,隨即陷入沉默。50年過去了,沈阿大說着浙江方言,趙淑亮說着山東方言,母子倆雖然緊握着雙手,卻完全聽不懂對方的話。
三年困難時期,江南(江浙滬)地區尤其是農村出現了較嚴重的糧食短缺,一些孩子一出生就被父母遺棄,被福利院收養後,又被政府分批派送到北方相對殷實的缺兒少女的家庭中。“三年困難時期”過後,這種狀況仍時有發生,其中不乏節育措施落後、選擇性別養育以及地方民情等原因,直到70年代。這些孩子被稱爲“江南棄兒”,趙淑亮就是其中一位。
趙淑亮的生父(圖)已經去世。50年前,他覺得“兒子多了養不好,長大娶媳婦都困難,不如送出去找個好人家”,便將四子放在鎮上,後被人發現送往了嘉興救濟院(現嘉興市社會福利院)。同年,山東莒縣農村的趙家有六個女兒,想要個兒子。通過介紹,楊家四子輾轉被抱到山東莒縣趙家,成爲6個姐姐的弟弟,取名趙淑亮。
十三四歲時,趙淑亮和夥伴們打架,夥伴罵道,“你是野孩子,不是你媽生的,不和你玩。”委屈的趙淑亮抹着眼淚回家,母親以“小孩都是撿來的”爲藉口安慰他,這個話題就這樣被終結了。趙淑亮回憶,“抱養的總覺得低人一等,父母不說,也就不問了。”之後十幾年,母子雙方一直保持着默契,誰也不願提這件事。看着生母一家的大合影,趙淑亮說,如果當年自己沒被送走,合影上肯定人更多。
80多歲的養父母去世後,舅媽給了趙淑亮一張寫有“戊申閏七月念(應爲“廿”,作者注)一日丑時”生日的紅紙,這是他的親生父母所留。50年過去了,紙張被反覆打開、摺疊,已殘破不堪,手一摸就會掉下一塊。拿着這塊紅紙,趙淑亮踏上了尋親之路。
8月2日,趙淑亮跟隨來自山東、河南、安徽、江蘇等地,共計200餘人的“江南棄兒”尋親團,來到嘉興市人民公園參加首屆尋親會。尋親團們有的手裏拿着幼時物件,有的舉着牌子,有的拉着橫幅,更多的是拿着寫有自己出生信息的尋人啓事。近百人留下血樣,經過DNA比對,趙淑亮、瀋海琴和陸海英三位江南棄兒幸運地找到了親人。
1974年2月18日,天氣陰冷,在海寧斜橋錢家埭一座低矮房子裏,時年25歲的吳桂香生下了第二個孩子。窮困潦倒的家庭搖搖欲墜,孩子被丈夫抱走,放在原斜橋鄉政府的門口(如圖)。做父親的戀戀不捨,心裏打了個賭:如果孩子哭鬧,就抱回家。可是孩子沒有哭,父親眼睜睜地看着她被抱走。
女兒被本地的沈先生收留,取名爲瀋海琴。懂事後,瀋海琴萌生了尋找親生父母的念頭。在8月2日的尋親大會上,有朋友跟她說,一位叫錢新萍的尋親者與她長得很像。兩天後,她們見了面,“那種親切感馬上就來了,很奇怪。”錢新萍說,在與瀋海琴聊天時,錢新萍的寵物狗只圍着瀋海琴嗅個不停。當時旁邊還有很多人,狗卻理都不理。8月8日晚上9點多,DNA結果證實了兩人的親姐妹身份。
母女相見的那天,兩人的淚嘩嘩地往下掉。“那個時候太苦了,衣服白天穿在身上,晚上就給你墊在下面當尿布,送走了你,接着穿。”吳桂香言語間充滿了對二女兒的愧疚。瀋海琴則在旁邊流淚聽着,沒說一句話。瀋海琴望着牆上父親的遺像,望着當年把自己送出去的爸爸,沉默着。
剛找回的女兒瀋海琴要回自己的家了,吳桂香才意識到女兒會再次離開,她揮着淚告別。44年前送走孩子的情景,如同放電影一樣,在母親吳桂香腦子裏反反覆覆出現。從瀋海琴現在的家到出生地,僅13公里的路程。這13公里,硬生生將骨肉之情阻斷了44年。
1972年2月14日,陽曆是西方情人節,陰曆是大年三十除夕。在嘉興秀洲新塍鎮沈家浜,村婦沈文珍生下一女嬰。因爲之前已經有兩兒一女,家裏生活條件差,丈夫便於大年初二將女嬰放在新塍鎮集市上,隨後女嬰被撿起來送往嘉興救濟院(現嘉興市社會福利院)。派出所的檔案顯示,當時的福利院爲陸愛英取名“王新”。
同年10月8日,南湖區七星鎮的陸先生輾轉來到福利院,抱養了“王新”,取名“陸愛英”。自從四五歲記事時起,陸愛英就明白了自己是領養的,但是嚴厲的養父一直不讓她提這件事。直到2008年,快70歲的養父摔傷,陸愛英一直陪伴左右。“父親告訴我,希望我想辦法找找親生父母,了卻心願。”陸愛英在家附近的養老機構工作。“照顧老人,確實是又髒又累的活。當我沒耐心時,我就想啊,想着眼前的說不定就是我親生爸媽,就恢復了耐心,就不怕累了。”
在尋親會上,陸愛英的二哥、二嫂帶着母親沈文珍看到了既是尋親者、也是尋親志願者的陸愛英,別人還指着陸愛英告訴她二哥,這個女的跟你長得像。時隔46年,一家人第一次距離這麼近,但是彼此之間卻沒有對話。6天后,在現場留下的血樣監測DNA證實了她與沈文珍的親權關係。
陸愛英現在的家距離她的出生地僅30公里左右。8月12日是回家認親的日子,陸愛英一早化了妝,“上次化妝還是20多年前結婚的時候”。車子走到村口,陸愛英便示意司機停車,她要從村口走回出生的家。她的二哥早已準備好了鞭炮和煙花,也請來了廚師在家裏燒菜,迎接回家的妹妹。
鞭炮聲一響起,陸愛英微笑的表情瞬時哽咽了,隨後突然上半身垂下,踉蹌地彎了一下腰。圍觀的人被鞭炮燃燒的煙霧淹沒,陸愛英在丈夫、尋親志願者等人的陪伴下走向家裏,一下撲進親生母親的懷抱。“他們都有自己的媽媽,我沒有,今天我終於也有了自己的媽媽了。”她把頭埋進媽媽的懷裏說。有人把現場照片發在尋親羣裏,尋親者臧霞說,叫出心中那聲媽媽,心中多少委屈都放下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尋親棄兒都那麼幸運,更多的人還在希望和失望中掙扎、尋找。8月5日,來嘉興尋親4天后,來自河南鄭州的王瑩來到南湖遊覽。船上有人搭訕問她,大姐,你是嘉興人嗎?她想了想回答:是。
王瑩於1964年12月30日出生於嘉興,被遺棄後送往福利院。“當時她叫元麗,腦袋又大又重,顯得身體很小。尤其是將她豎着抱時,腦袋在空中晃來晃去像要掉下來,總讓人覺得好像生了病。”自小在福利院長大的郎解說。王瑩11個月大時,鄭州33歲的王女士結束了一次不幸的婚姻,心灰意冷,並且不打算再婚。沒有生育的她經人介紹來到福利院抱養孩子。也許是看到頭重腳輕的王瑩心生憐愛,便隨緣在衆多棄兒中選中了她。
王瑩結婚後,育有一女,初爲人母,看着孩子愛不釋手,理解了做母親的苦與樂,也開始想起自己的親生父母。“有一次做夢,夢到自己出生的家是白色的牆,灰色的瓦,家裏的木樓梯刷的是暗紅色的油漆……”在鄭州的一個派出所查找多次,最終確定了,她出生在浙江嘉興。半個世紀後,沿着當年被抱走的滬杭鐵路,王瑩在女兒的陪伴下來回到出生地嘉興尋親。
8月2日 ,在尋親會上,王瑩淚如泉湧:“我一到家鄉,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掉下來,心裏十分難受,但看到家鄉的美麗風光時,又感到十分親切,彷彿父母和家就在眼前……希望當年不管什麼原因送走孩子的父母,放下思想包袱,來認領這個孩子。”
經過民間志願者不完全統計,結合公開報道的交叉求證,“江南棄兒”多達5-10萬人。如今半個世紀過去,棄兒們在各地長大。他們普遍經歷了童年時期被稱爲“抱養的、野孩子”的譏諷,在自卑中長大,他們有的等養父母去世後尋親,有的隱瞞着養父母開始尋親。經過了從怨恨到理解的心理歷程之後,他們試圖弄清楚“我是誰,我從哪裏來”這個困擾了大半生的問題。尋親之路艱難且漫長,他們在希望和失望的交織中前行着。
經過民間志願者不完全統計,結合公開報道的交叉求證,“江南棄兒”多達5-10萬人。如今半個世紀過去,棄兒們在各地長大。他們普遍經歷了童年時期被稱爲“抱養的、野孩子”的譏諷,在自卑中長大,他們有的等養父母去世後尋親,有的隱瞞着養父母開始尋親。經過了從怨恨到理解的心理歷程之後,他們試圖弄清楚“我是誰,我從哪裏來”這個困擾了大半生的問題。尋親之路艱難且漫長,他們在希望和失望的交織中前行着。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