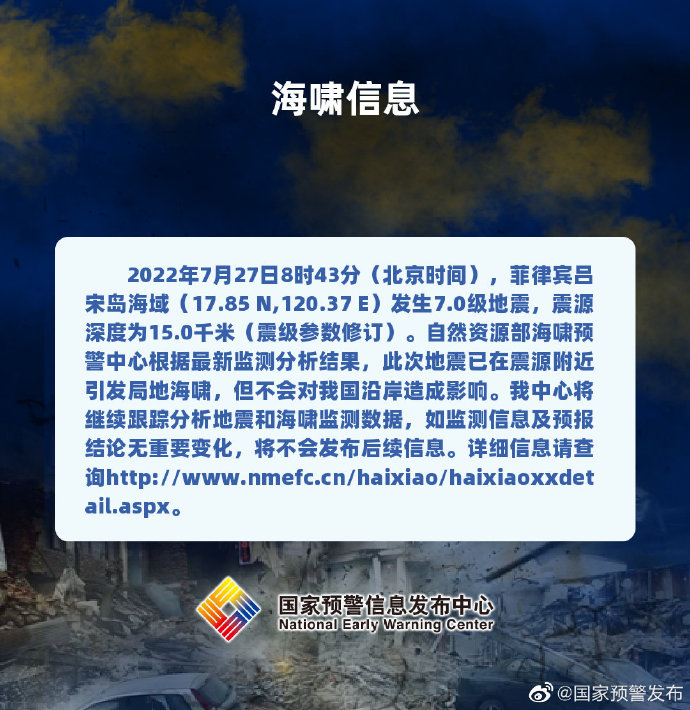逃離庫勒丨有本事你去臥軌啊!
逃離庫勒丨有本事你去臥軌啊!
1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庫勒村的黃昏。
我攥緊雙拳,躺在鐵軌的中央,頭使勁往後抻,試圖埋進枕木中間的石塊裏。腳底前方,火車聲音隱隱傳來,我感受到鐵軌開始不安分地震顫。鐵軌旁邊的樟樹上,冒出幾個腦袋,他們和我一樣正屏住呼吸,見證着這個奇蹟。
“來了,來了。”
聽到聲音,我微抬起頭。眼前的龐然大物已經出現在鐵軌的拐角處。謝聰說得沒錯,火車頭的確和艾斯奧特曼的面部有幾分相似。我把眼睛眯住了,深吸一口氣,縮緊肚皮,等待火車從我身上爬過。
火車發出喧囂的汽笛聲,我的耳膜都要刺穿了。還沒來得及害怕,一陣陰影從我的腳底處爬升上來,瞬間,我已經藏身在火車的底盤下面。
我永遠記得,火車過後,我胃裏翻江倒海地難受,腦裏總是充斥着轟鳴聲,像有人正拿着棍子使勁攪着我的腦漿,敲敲打打。當時我的臉上糊滿了青黃排泄物,站起來的時候,我裸露的小腿上還黏着塊嬰兒尿不溼。
樹上的小孩都跳了下來,捏着鼻子不敢靠近,茫然地看着我。而我正對着他們傻笑。
這是我六歲的故事。
六歲的時候,庫勒村的小孩子間流傳着一個勇士的遊戲,誰敢趴在鐵軌間,讓火車碾過並毫髮無損,誰就是勇士,就是小孩間的頭兒。這個類似於孫猴子獲封美猴王稱號的遊戲,讓所有小孩躍躍欲試。只要身材夠纖瘦,在鐵軌中央保持好姿勢,火車駛過的時候,能夠耐住底盤的轟鳴和喧囂震響,一般不會出事。
然而也有意外。一年後,老蔡的兒子山間放馬,在枕木上睡着了。他也許是側着身子睡覺,司機遠遠發現了他,緊急啓動制動裝置,然而已經來不及。他的上肢被火車頭撞飛足有二十米遠,肚皮被車鉤撕裂,內臟或攪進底盤,或泄在鐵軌旁的石坡上。
尋找他的頭顱花費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庫勒村的周圍是深山,山裏的野狗循着血腥而來,將他腦袋叼走。村裏獵民發現的時候,他腦袋的血肉已經被啃食殆盡。
這件事情發生後,勇士遊戲也就無人提及了。
2
庫勒村被重山環繞,與世隔絕,僅靠一條鐵道和綿延的泥路與外界聯繫。老蔡失去他兒子後,把家遷到鐵道附近,專門警示過往小孩別在鐵路附近逗留。
老蔡是我們村裏的有名的“運手”。他有一匹毛色純白品種不明的馬,每週末的拂曉時分,他就騎着馬沿鐵軌旁邊的過道進鎮,購買鄉親需要的日用品或秧籽化肥回村。我爸是這塊地方唯一的醫生,老蔡經常拿着憑證,幫我爸帶些診所緊缺的醫藥品回來,其中就包括張一翔外婆需要的麻藥。
張一翔的外婆是個瞎子,她的眼睛是幼年在山上迷路時被木刺戳瞎的。深山的溼度常年偏高,她的眼睛雖瞎了,卻會隨着溼度升高而犯痛,只能靠注射麻藥來鎮痛。每回天氣轉陰前,張一翔就出現在診所門口,向我爸購買一根注射器和一小玻璃瓶的利多卡因麻醉劑。
張一翔是我們當中,衣着最時髦的小孩,他的嘴裏永遠吮着顏色百怪的水果糖。這些都是他遠在北京的媽媽給他郵寄來的。張一翔從來沒見過他的的媽媽,他大概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就被送回山裏,然後六七年過去了,他媽媽從來沒回來過。
後來我從謝聰那裏大概瞭解了一點內幕,張一翔的媽媽之所以不回來,是因爲她在外面做了別人的小三。情夫是個地產開發商,不願意有私生子,張一翔的媽媽便瞞着開發商把孩子生了下來。然而生下後,她也後悔起來,於是把嬰兒送回庫勒村,每月郵寄點東西回來,但從來沒看望過他。
我不知道謝聰是從哪獲得的這些消息,他神祕兮兮告訴我後,囑咐我不準告訴其他人。我問爲什麼,他說他要用這個來敲詐張一翔。
張一翔是我們小孩子間的霸王。他沒有躺過鐵軌,沒有經歷火車從身上駛過的感覺,但他卻一直是我們小孩間的老大。他善於用糖果玩具賄賂體格健壯的孩童,然後欺負不服他管教的小孩。謝聰是個孤兒,從來沒受過束縛,自然不服張一翔。所以他成了張一翔經常欺負的目標。
謝聰住在間土磚房內,喫着村長每月送來的糧食,一袋土豆,一袋紅薯,兩吊臘肉,半袋米。張一翔的家是幢瓷磚房,住在離我們村落半里遠幽靜的山腰處。不上學的日子,張一翔大清早就去謝聰的土磚房內,踢開門後不由分說把他從牀上拖到田裏打架。謝聰時常讓他,因爲將他打贏的話,自己勢必沒好果子喫。
所以每次打不了幾個回合,謝聰就跪趴在地上討饒。
“服不服管啊?喂!”張一翔摁住謝聰的臉,盛氣凌人地質問。
這是他的習慣,他每說一句話後面都會不耐煩地加個“喂”,企圖讓別人儘快回他的話。
“服了,服了。”謝聰被壓在泥裏,口齒不清地回答。
張一翔高興得很,抓起一把泥團塞到謝聰的嘴裏,這事就算過去了。
張一翔走路時搖頭晃腦,嘴巴永遠撅着,說話奶聲奶氣,帶着一股子倔扭勁兒。背地裏我們極喜歡模仿他說話,這其中,又以謝聰模仿得最像樣。所以很多次被作弄後,趁張一翔不在家,謝聰會跑到瓷磚屋內,模仿張一翔的語氣把他外婆罵得狗血淋頭,這樣張一翔回家的時候就免不了有一頓打了。
張一翔還有一項癖好,那就是作弄老蔡的白馬。每至黃昏,那匹被拴在木樁上的白馬無事可做,便駐足發情,他的下體逐漸僵硬,像一杆標槍那樣碩長。這個時候的張一翔對作弄任何人都沒有興趣,他只對那杆標槍報着無限的好奇。他靜靜地坐在附近的稻杆堆上,靜靜地欣賞眼前的異物。一旦馬的下體開始軟化,他就興味索然地拾起塊泥巴或石塊朝它砸去。白馬被驚動,繞着木樁環跑,它的下體一前一後地擺動,張一翔就樂得大笑。
那匹白馬就是這樣陽痿的。
張一翔把馬搞得陽痿後,謝聰捱了老蔡的一頓狠打。因爲張一翔看到白馬下面血流不止後,立即向老蔡惡人告狀,說是謝聰幹得壞事。
謝聰無辜捱了揍,從此記恨在心。得知張一翔的媽媽是小三後,他將消息掖着,打算好好把握這個機會,狠狠懲治張一翔。
一次,閒的發慌的張一翔又將謝聰從土房拖出去打架,謝聰沒有讓他,使盡全力收拾了他一頓。張一翔倒在泥地裏,被揍得鼻青臉腫,他呼呼喘着氣,揚言要找人來。謝聰沒敢下手了,鬆開拳頭,把他扶了起來。
張一翔氣洶洶地說:“你扶我起來也沒用,謝聰,你打了我,我等下就去找人來。”
謝聰笑着說:“你儘管找人,你找多少人來,我就告訴這些人一個祕密。”
“什麼祕密?”
“關於你媽媽的祕密。”
張一翔有些慌了,他第一次一聲不吭地離開了。謝聰憂心忡忡地過了一天,但張一翔並沒有找人來收拾他。
然而沒過多久,張一翔又手癢了,跑來找謝聰打架。謝聰再一次將張一翔打趴,順勢抓起一團泥巴塞進他嘴裏,並告訴他說:“不要以爲你是開發商的兒子,我就不敢打你了。”
之後,張一翔再也沒找謝聰麻煩了。
謝聰看到報復奏效後,喜不自勝,於是開始找張一翔的麻煩。看到他在喫水果糖,謝聰會順手從他口袋裏抓出一大把放進自己的口袋,並扔下一句:“記住,別人可不知道,你媽是小三。”
有時候手上有髒泥時,他也會毫無顧慮地蹭在張一翔的新衣服上,甚至把鼻涕抹在他身上。
他說:“你媽只會送衣服,人又不回來,太絕情了吧。”
終於,張一翔忍無可忍,他把謝聰叫到學校後面的一個小角落,警告他假如再用這件事來威脅自己,會找人拆了他的土磚房。
謝聰毫不留情地叫囂:“你儘管拆,你拆了,我就睡你屋去。”
張一翔皺着眉,有些無可奈何:“你到底要怎麼樣?喂!”
“沒怎麼樣,我只是突然覺得,折磨你還挺好玩的。”
張一翔罵他:“鄉巴佬。”
“隨便你怎麼罵。”
張一翔不做聲了,他忽然訕笑起來,臉上流露着不屑。謝聰看着他的神情,莫名惱火起來。
“你在笑什麼?”
“你不覺得嗎?你好可憐。”
“你他媽纔可憐。”謝聰說。
“你一定等待報復我等了好久吧,好不容易逮着機會,就像狗皮膏藥一樣粘着我不放。你一輩子也就這回事了,你現在還能在這個學校讀書,是因爲老師同情你,才讓你免費入學。我外婆說,這個學校馬上就要倒閉了,馬上我媽媽就要接我和外婆出去了,我就可以進大城市裏上學,而你呢?只能守在庫勒村裏,守着你的土磚房活到老。你說,你可不可憐?”
謝聰的臉上露出一絲恐慌,這是他從來沒想過的問題。他說:“我會出去的。”
“你出不了,因爲你沒有爸爸媽媽。”
“那你也出不了,因爲你爸爸不認你這個兒子。”謝聰惡狠狠地說。
“我爸爸已經離婚了,他已經和我媽媽在一起了,他們馬上就要接我出去了。”
“你胡說。”
“信不信由你。”
說完,張一翔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3
“陳北,聽說學校要倒閉了。”謝聰問。
“學生實在太少了,而且大部分都交不起學費,倒閉是難免的。”
我們坐在院落的牆沿上。說完,我撿起旁邊一塊瓦礫向着前面的田地裏扔了過去,立刻,驚飛了幾隻野鳥。
“不讀書你會去哪?”謝聰問。
“不知道。”
“你有沒有想過離開?”
“離開?”
“對呀,你不覺得,這個村子實在太壓抑太無趣了嗎?”
“我得聽我爸爸的。”我說。
這句話梗住了謝聰。
“我……我不是故意的。”
“沒事。”謝聰耷拉着臉皮,顯得無精打采,他說:“陳北,無論如何,我一定要離開這個村子。”
“你爲什麼這麼想離開?”
“你看看這個地方吧,除了山就是山,無邊無盡的山,人待在這裏面有什麼意思,你知道嗎?每天聽到火車聲音,我有多希望能爬上面去,然後離開這個地方。但是我知道,我會馬上餓死在外面,我之所以能活到現在,全靠村長每個月接濟給我的糧食。”
之後的許多時候,我都看到謝聰在鐵路旁邊閒逛,他時而躺在枕木上,時而一輛火車駛過,他發瘋似的追着跑。許多次我都以爲他一去不復返了,然後他又慢悠悠地往回走。有一次他失蹤整整一天一夜,我想他終於走了,然而第二天,我看到他家的煙囪升起了炊煙。
於是許多人都知道謝聰想要離開庫勒村,但一根無形的鎖鏈禁錮了他,那就是糧食。每天早晨,許多小孩會結羣去敲門,看他是不是還在家。一旦發現他還在,就催促:“今天還不走?”
暑假過後,我們村唯一的學校終於倒閉了,但老師還是佈置了作業。那個暑假,陸陸續續有許多戶遷了出去,小孩離開之前,對留下的夥伴問最多的就是:“你什麼時候能搬出去?”
他們把這樣一個殘忍的問題留了下來,然後坐着推車,沿崎嶇泥路趕赴外面的世界了。
謝聰開始更爲頻繁的離村出走,但沒有一次真正離開。在沒有離開的日子裏,他經常坐在鐵路沿線的田埂上,嚼着草莖,思忖離開的計劃。張一翔每天都到各家串門,將一個好消息廣而告之,他從未見過面的爸媽馬上就要回村了,他的奶奶已經在收拾家當,一旦他父母回來,他們就能離開這個村了。他也經常走到田埂上,在謝聰身邊晃盪來去,伺機尋些話頭來刺激他。但謝聰毫無心思與他計較。
有天,張一翔對謝聰開了個無足輕重的玩笑。
“其實謝聰,我可以帶你出去。”
謝聰頭偏了偏,沒有回應他。
“喂!”張一翔不耐煩地呼叫。
“去哪?”
“離開庫勒村,去大城市。”
“你別開玩笑了。”
“假如我爸媽回來的話,我叫他們收你做乾兒子,然後帶你一起離開。”
“真的?”
謝聰轉過臉來,眼睛裏泛着光。
“前提是,你得跟我幹一架,但還不能打贏我。”
於是他們在泥地裏像牛犁田一樣幹得渾身黃泥,謝聰打得束手束腳,沒有還手,他的臉被揍得烏青,牙齒也被打掉了一顆。然而第二天,張一翔就翻臉不認人,死不承認之前許下的承諾。
剩下的日子裏,謝聰每天不再回到田埂上,徹底像塊狗皮膏藥一樣纏着張一翔,哀求他帶自己離開庫勒村。大人怎麼會隨隨便便收留一個小孩做乾兒子呢,這是當時的我都明白的事理。但謝聰似乎死馬當活馬醫了,他將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壓在張一翔這個毛屁小孩身上。
張一翔說:“你替我扇風。”
於是謝聰拿了一把蒲扇,使勁替他扇風。
張一翔說:“我累了,你揹我回去吧。”
謝聰不敢歇着,蹲下身子揹他回屋。
張一翔享受着謝聰的服務後,又一遍遍反悔。隨着父母回村的日子越來越近,張一翔開始嚴肅地審慎他的行爲,並鄭重告訴謝聰說:“你要明白,我不可能帶你出去的。”
謝聰回應:“你不能賴皮。”
張一翔父母回來的前一天,謝聰關在屋裏大半天沒有出來,炊煙不升,我們都覺得很反常。有小孩透過窗縫看到裏面情形後,連忙跑去找張一翔,大呼不得了了,張一翔一頭霧水,問怎麼了?
“我看到謝聰他,他在收拾行李。”
說完,謝聰已經揹着一大包行李走了過來,把它頓在地上,擦擦汗問:“哥,我們明天什麼時候走?”
張一翔氣的大跳,罵道:“我從沒見過你這麼不要臉的人。”
謝聰毫不在乎,暢想道:“你爸認我作乾兒子後,我是不是也得改姓?”
“你別做夢了,我不會帶你走的。”
謝聰怒了,大喊:“你怎麼能賴賬呢?”
“誰知道你這麼開不起玩笑。”
“我不管,我就纏上你家了。”謝聰說着背起行李,往另一條路上走。
“你去哪?喂!”張一翔急了。
“去你家守着。”
張一翔喊道:“你回來。”
謝聰邁着小步繼續走,理也沒理他。
“這樣吧,你再做一件事,我保證帶你離開。”張一翔說。
謝聰偏過頭,放下行李問:“是什麼?”
“還記得兩年前玩的勇士遊戲嗎?”張一翔吞了吞口水,聲音有些不自然,“假如你去鐵路上躺着,能保證火車過去你依舊毫髮無損的話,我就帶你走。”
謝聰躑躅了一下,答應了,他說:“我們現在就去鐵路。”
“不,要等明天。”
“明天?”
“明天下午,我再來驗收成果。”看到謝聰一臉質疑的神情,張一翔難得寬慰地笑了笑,說:“放心吧,我爸媽下午再出發,不會提前走掉的。”
4
然而第二天,謝聰死了。老蔡清晨發現了他的屍體,他的碎肢散在鐵道沿線,因爲很晚才發現,他的腦袋被野狗叼進了深山,下落不明。
張一翔一家沒和任何人打招呼,上午時分,悄然離開了庫勒村。張一翔果然還是騙了謝聰。
村裏人唏噓不已,認爲謝聰是自殺。我瞞着大人,來到他的出事地點。他的肢體已經被我爸爸拾撿拼湊,然後抬走了,村長正安排獵民進山搜尋謝聰的腦袋。鐵軌兩邊留下幾淌紅色血泥,我抬頭望了望,謝聰破舊的衣服還掛在樹上。他昨天就是穿着這身衣裳告訴我說,他晚上要先找一輛火車試驗一下,並篤定說着學校課堂教的最後一句諺語,不成功,便成仁。
腦袋一週之後才被找到,村長看了眼後,抹着眼淚直呼造孽啊。隨即大人們找塊白布將它矇住了,不過我還是一睹了它的慘相。我已經完全認不出這就是謝聰,他粉白的頭骨有幾處碎裂,骨面上泥濘不堪,只掛着一星半點的肉皮。
這個慘相讓我一連做了幾天的噩夢。
之後鐵道公安的工作人員來了,草草瞭解情況後就離開了。當時駕駛火車的副司機回憶說,他看到前方一個小孩似乎臥軌自殺,橫躺在鐵軌上。副司機按響汽笛警告,並啓動緊急制動,小孩聽到動靜後,緩慢爬了起來,不過已經來不及了。
這個和謝聰告訴我的有些出入。我想起一件事情,張一翔離開前的那天夜裏,他好像來我家買過藥。因爲圖方便,我和我爸晚上就睡在窗邊,如果半夜有人來買藥,只需敲一下那面毛玻璃,報明症狀,我爸會把藥從窗口遞出去,那邊會通過窗口把錢遞進來。
睡意朦朧間,那晚,我似乎聽到過張一翔的聲音,他買的是一支注射器和一瓶利多卡因麻醉藥。
我忽然有個恐怖的想法。但僅僅也只是一念之間,因爲那時候的我,還不懂謀殺的概念。
謝聰被葬在鐵路旁邊,他的土堆是很小一塊,隆在草叢間像塊木墩。他沒有立碑,也沒有鮮花,他的一生止於九歲。在生命盡頭,他的足跡也沒能逃離庫勒村。
那段時間,我經常凝望着謝聰的葬地,不免開始擔心自己的未來。一個月後,天氣轉冬,也許是破損的睾丸無法抵禦惡冬的嚴寒,老蔡的白馬瘋掉了。它嘶吼着掙開繮繩,跑到了鐵軌上,它沒有停步,朝着一個方向嘚嘚達跑着,使勁跑,直到被火車撞飛。
我想我大概也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新年過後,冬過轉春。爸爸的老弟騎着摩托沿鐵路過道進了庫勒村,他帶來許多禮品,然後把我接出了庫勒村。我從來不知道我還有個親叔叔,我只知道我媽在生我後就死掉了。
之後,我一直住在城市裏的叔叔家。叔叔是個搞藥材批發的老光棍,他頭盤禿頂,兩頰皮膚嚴重下垂,雖然才三十多歲,但已經像個行動遲緩的老人了。住在他家的生活是快樂的,雖然一個月裏他只在家裏待幾天,他經常全國各地奔波,但他回來的時候,總會少不了給我帶禮物玩具。他喜歡爽朗地大笑。他不像我爸爸似的,總藏着笑容,以嚴肅面孔示人。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叔叔每天早上要喫四個雞蛋,他能夠一口吞掉兩個水煮蛋,他的嘴巴極大,像個無底洞。然而在我讀高中的時候,他因腦癌去世了。
他把遺產全部留給了他哥哥,也就是我爸爸。爸爸關掉了庫勒村的診所,來到城市,住進了這個兩居室樓房。兩年後,我考上了北方的大學,主修歷史。大學畢業後,我回到這個城市,進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任職文員。
在那裏,我重新遇到了張一翔。
我不敢相信,時隔十幾年,他能一眼認出了我。因爲缺乏鍛鍊,穿着企業職員裝的我顯得臃腫不堪,眼袋厚重的像兩顆手雷,坐在電腦前敲文案的我,屁股總有一大半陷進座椅的海綿裏。然而張一翔還是一眼認了出來。他是公司的工程經理,這樣的他經常梳着油亮的背頭,西裝革履,額前總是彎下兩綹髮絲。
遇到他後,庫勒村久遠的回憶又重新被喚醒了。
我們進行了簡單的寒暄。他的性格已經內斂沉穩地多了,遠沒有小時候那般飛揚跋扈。然而我問他還記不記得謝聰,他似乎是想了一陣後,才恍然大悟地喊道:“哦,那個傻子啊。”
相逢的初期,我的心裏冒出許多雞賊的想法。希望以童年的交情,張一翔能夠在事業上提拔我一下,然而沒多久,我們倆的關係就平淡如水。但忽然有一天,他說他想回庫勒村看看,問我有沒有空。
我答應了。
5
聽我爸爸說,十幾年來,庫勒村已經徹底淪落成空村,即使政府出資修了條寬敞馬路,裏面也沒有一戶人家。老蔡和村長這樣資歷老的人,也早已投靠第一批搬出去的親戚了。
我給張一翔當司機,開着他的路虎,奔波在山間坑窪的石頭馬路上。我們倆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因爲他不抽菸,我忍着煙癮使勁嚼口香糖。
但有個問題,其實我早就想問他了。
在他近乎炫耀似的提及他馬上要承包的工地項目,他說現在是房產的世界,只要我好好幹,一定會出人頭地之後。我忽然問他,是否還記得他離開庫勒村前的那個晚上,他到我家買過麻藥。
我從後視鏡裏,看到他的神情僵了一會兒。他動動脣皮,問:“怎麼了?”
“那幾天之後可沒有轉陰。”我冷靜說道,繼續瞧着他的反應。
他笑了,說:“我外婆很早就過世,我也不清楚,她那晚到底爲什麼要叫我去買藥。”
“未雨綢繆吧,老人家都這樣。”我替他解釋。
“也許是的。”
車子又開了一大段,我們倆之間有很長時間沒有說話了。但我知道,他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樣不平靜。他忽然問我:“陳北,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庫勒村的?”
“你走之後的第二年春天。”我不動聲色地說,“你知道嗎,你走之後,那頭馬就瘋掉了。”
“什麼馬?”
“你不記得了嗎?就那頭蛋都被你打爛的馬呀,老蔡家養的。”
“哦。”他又笑了。
“你之後還誣陷說,是謝聰乾的。”
“那都多小的事了,誰還記的。”
“可你爲什麼會記得,離開前那天晚上你到我家買過麻藥呢?”
這句話顯然惹火了他,他的語氣生硬起來,“陳北,你到底想說什麼?”
“你離開之後,謝聰就死了。老蔡那時候住在鐵路旁邊,他告訴我爸說,他那天晚上曾看到你和謝聰在一起。”
張一翔頓了一下,點了點頭,說:“這很正常,他約我出來,就這樣。”
“對呀,很正常,你身上可還帶着麻藥和注射劑。”我哼了口氣,側過頭對他說:“老實告訴你吧,我爸很早就懷疑是你謀殺了謝聰,因爲他在謝聰的身上發現一處針孔,而且針孔周圍有利多卡因麻藥的刺激氣味。”
張一翔啞口無言了,他神情複雜地端坐在後面。
“只可惜我沒找到那枚注射器,要放現在的話,指紋一對比,你就死路一條了。我爸總是說,得饒人處且饒人,所以這事就過去了,但我總忘不了,你說,該怎麼辦?”
他明白我的意思了。
“你想要錢?”
我沒說話。
“這樣吧,兩套樣板房如何?”
“再加上你這輛車。”
“成交。”
他答應了。我打開窗戶,點了根菸。路上的大石塊不斷地磨蹭着底盤,眼前橫亙的山脈隱隱顯出一條鐵路,鐵路附近有塊開闊的土地,那片地方就是庫勒村。
“陳北,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張一翔忽然問,語氣有些輕佻。
“什麼?”
“你猜我殺謝聰的動機是什麼?”
“嗯?”我想了想,“你煩他,害怕他拖累了你?”
“不是的。”
“難道是,你怕他跟別人透露,你媽是小三的事?”
“那件事情。”張一翔笑得誇張,“村裏面的小孩大人後來基本全知道了,不算什麼祕密。”
“那是因爲什麼?”我不明白了。
他仰起頭,舔了舔脣皮,似乎下了很大勇氣,才說道:“有個祕密,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說過,因爲不敢。但我覺得,可以跟你說。”
我靜等他的講述。
“你有沒有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其實那天晚上,死的是張一翔?”
車子正橫過鐵道,我聞言下意識剎住了車。
“你是說?”我驚恐道。
"這個世界上,註定有些人的前行是爲了到達,而有些人的前行是爲了逃離。"他感慨道,閉上了眼,開始回憶:“屍體的腦袋不見了,其實是謝聰把它扔進山裏,送給野狗喫了。當晚也是謝聰模仿張一翔的聲音,去你家買的麻醉藥,之後約他出來,將他麻醉,換了他的衣服,把他扔在鐵軌上。謝聰親眼看着火車駛來,張一翔掙扎着要起來,然後被撞得四分五裂。”
“你的意思是,你是謝聰。”我回過頭來,喊道:“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他外婆是個瞎子,我當時最會模仿張一翔的聲音,聽聲音她完全以爲我就是他的親外孫,而且他的媽媽爸爸從來沒見過我。”
“亂了,亂了。”我彷彿失了心智。
“感謝張一翔吧,讓我得以重生。我這次回來,就是要好好地祭拜他,他葬在哪裏?”
我晃過神,看了眼車窗外,正前方旁邊的一大片荒草中,隆起一座小土堆。
我指給謝聰,說:“在那!”
謝聰這才注意到我們的車正停在鐵軌上,他警惕說道:“這裏很危險,趕快開走。”
然而車子的引擎這會兒卻離奇地停住了。我試着發動,卻毫無反應。
“怎麼了?”謝聰焦急地問。
“車……車壞了。”
剛說完,原本打開的車窗自動合上了,我擰了擰門,卻發現怎麼也打不開。
“見鬼了,見鬼了。”謝聰喊道。
我全無反應,視線被眼前那隆小土堆吸引住了,我感覺,是它要把我們留在這裏。
然而此刻,耳畔響起一陣刺耳而又熟悉的火車汽笛聲。
(往期精選文章,點擊下方鏈接可直接閱讀)
逃離動物園
密室逃脫:逃離別人的意識海
地鐵異物入侵事件
黑雪丨警察和妓女的罪與罰
淘汰丨沒用的人早點去死
每個作者每天可投三票,動動你的小手指,圓過氣作者一個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