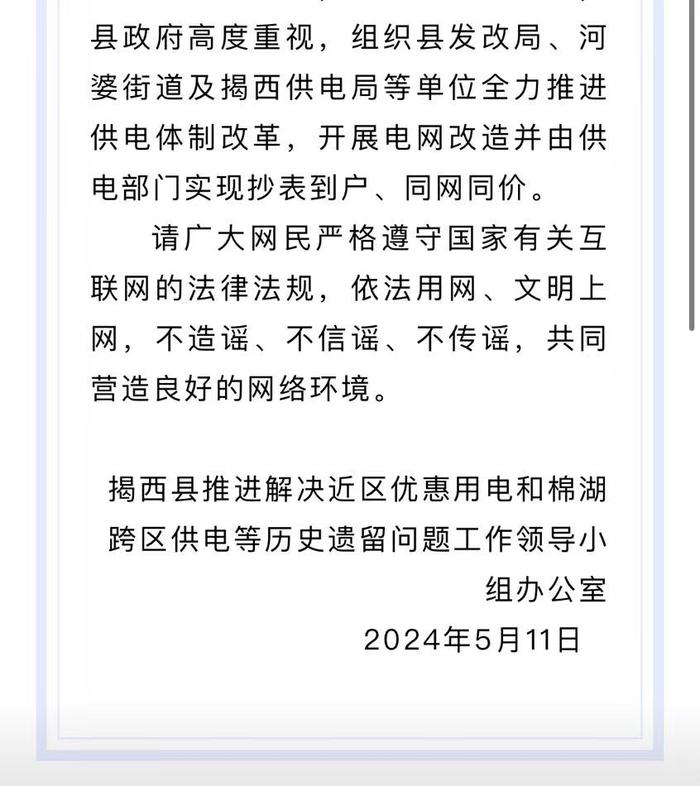環境調查 | 小村水事——14年求水路在何方?
今日起,我們將一個傾力打造的全新欄目——《環境調查》呈現給您。
這是一個深度新聞調查欄目,直面問題,揭示真相,以新聞的力量推動進步。
您最關心的,就是我們最關注的。我們將深入調查侵害您的環境權益、影響綠色發展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全面反映制約生態環境保護、污染防治攻堅、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障礙。
記錄歷史,引領未來。我們將爲您呈現環境背後的新聞,告訴您是什麼、怎麼樣、爲什麼,以我們一次次的努力,爲推動污染防治攻堅和美麗中國建設貢獻力量!
14年前,一座規模化養豬場的興建和運行,成爲下游村民飲水問題的分水嶺。
打從養豬場在上游運行起來以後,李洪和周圍71戶村民就開始了和養豬場的各種“交鋒”。戰線從2004年至今,足足折騰了14年。飲水管架設了一茬又一茬,村民的訴求只有一個:還我乾淨的飲用水。
一夜之間死了2000尾魚
李洪的家在大山深處,位於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水布埡鎮銅鈴巖村,離清江水布埡庫區直線距離約兩公里。清江水寧靜開闊,爲長江一級支流,古稱夷水,因“水色清明十丈,人見其清澄”而得名。清江全長423公里,流域內山明水秀,兩岸山巒疊翠,號稱“八百里清江畫廊”。銅鈴巖村,就在清江以北的大山之中。
在養豬場運行前,李洪和村民們喝着山泉水。“沒想到,養豬場建起來以後,我們喝的水還沒有豬喝的乾淨。”
李洪口中的養豬場興建於2002年,2004年底投產。當時,縣裏招商引資,把村子上游直線距離約1公里內的廢棄水泥廠改爲規模化養豬場——巴東縣福源養殖有限公司(2015年底更名爲巴東縣福臨養殖有限公司)。
關停水泥廠是爲了保護當地的生態環境,引進養殖場也有另一層深意:巴東縣是深度貧困縣,扶貧攻堅任務重,規模化養殖場入駐或許能爲周遭農民脫貧增收帶來曙光。不過,曙光一直沒見到。
李洪永遠記得2006年的正月初一,他推開門到自家魚塘裏一看,大喫一驚:2000條長到三四斤重的魚,一夜之間全死了。魚塘裏的水又髒又臭,“山上的養豬場排出來的糞污,把水塘裏的水污染了。”李洪又急又氣,“殺他們的心都有了”。
他一怒之下衝到山上的養豬場門口,養豬場大門緊閉。他徘徊着,盤算着,腦子裏很亂,想着“如何討個說法”。他喊了叫了,大門依然緊閉着。最終,沒人出來交涉。“我真是該背適(編者注:指倒黴)。”李洪悲憤交加。
買一尾魚花1塊8毛,好不容易養到三四斤,一斤能賣3塊錢,2000尾魚就是6000斤。一夜之間,18000元打了水漂,還沒地方說理去。新春佳節,眼看着鄰家張燈結綵、喜氣洋洋,李洪獨自依在牆角抽悶煙。
銅鈴巖村第6組組長李洪指着福臨養殖有限公司的排污口,一臉凝重。上方白色建築就是豬舍。張春燕攝
從養豬場拉了一根直徑15毫米的鋼管
漸漸地,養豬場帶來的水生態問題開始蔓延。
“2006年起,種田的時候怪事連連,以往能長1人多高的水稻,再也結不出果實了。田裏臭氣熏天,跑到小溪邊一看,水裏有米糊一樣的東西,黑黑的一團。撈起來一看,那就是糞水啊,可以直接灌田了。”覃大姐的家與李洪家僅一路之隔,說起養豬場的影響,她憤憤不平。小女兒嫁到宜昌,生下小孫子後,都不願回孃家來,“他們說太臭了”。
覃大姐把田裏的變化歸咎到養豬場的排污,她說村裏已經不種水稻了,改種玉米,“米也要自己買了”。
豬場上游的8組、再下游的12組共300多人的飲用水,都受到影響。村民反映到鎮政府、縣政府,最後在村幹部協調下和養豬場達成共識:從養豬場裏接一根直徑15毫米的鋼管出來,作爲新的飲用水水源。
“這根水管沒用多久也不行了,大概兩三個月就不用了。”12組的村民劉美權回憶說,“養豬場說自己也缺水,有時有水、有時沒水,斷斷續續。”後來,劉美權家只好到附近約3公里的另一個水溝引水下來。
李洪的哥哥李階認爲有人把閥門關了:“那根水管接在養豬場沖洗豬圈的閥門上,本來承諾我們一定有水的,誰知道他們有時還是把閥門關了。沒水的時候,我們只能又走幾公里的山路到養豬場,找在裏面打工的老鄉,把閥門打開。”
村民始終認爲,自己喝水的“生殺大權”掌握在養豬場那方。“而養豬場很強勢,就算去溝通,通常連門都進不去。”
可在福臨養殖有限公司廠長王傳國這裏,他也一肚子苦水。“以前,村支書過來協調過,我們就把自己場區內的一口井全給村民用了。遇到枯水季,我們也要上山找水,根本沒有什麼閥門之說。”
被動的排污整改
2011年,爲了解決村民飲水難問題,在村幹部的協調下,村民做出妥協並和養豬場達成協議,從新的一根水管取水,村民又能喝上乾淨水了。
這是銅鈴巖村飲水的第三根水管。
儘管這根水管取水口在別處,但中後段順着村民的房屋延展下來,最終還是和開始那兩根廢棄的水管並排在一起。3根粗細不同的水管組合在一起,有的被泥土蓋住,有的裸露着。公路一側的溝壑內、村民屋後自建的蓄水庫邊,只要留心,都能見到這些水管。有的已經斷了,不知下一段又從哪裏冒出來。水管就像繩索,把村子、養豬場和大山捆綁在一起。
同樣覺得委屈的,還有導致村民飲水難的“始作俑者”——巴東縣福臨養殖有限公司。“我們是外鄉人,老家在福建,大老遠到這裏來投產養豬,錢沒掙多少,麻煩不少,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老闆娘林雪英50歲開外,身材瘦削,說到和村民的衝突,眼淚一下湧出來。“縣環保局讓我們整改,我們也改了啊。”
由於養豬場對下游村民造成的飲水影響,村民在2014年底又再次舉報了養豬場。在巴東縣環保局出具的責令改正違法行爲決定書(巴環改字〔2015〕1號)裏清楚地記錄着:“縣環保局於2015年1月14日對養豬場進行檢查發現,公司污水處理站一級強化池管道堵塞,生豬養殖場區產生的污廢水從污水處理站進水口排入環境。公司污水處理站人工溼地無溼地植物,人工溼地墊層內積澱大量污泥,失去人工溼地的污水處理作用。”
縣環保局責令公司於2015年3月15日前改正上述環境問題。直到4月15日巴東縣環保局再次到現場勘查發現,污水沒有經過場外污水處理站,依然直排環境。場內的糞便、污水沒有進行乾溼分離。污水直排嚴重污染了環境。
同年5月12日,巴東縣環保局污染源現場監察記錄表上,反映出福源公司的整改進展。監察結論爲,“公司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整改,對場內廢水增加了乾溼分離機,對沉澱池進行了隔區,搭建了陰雨棚。場外污水處理站外排水不帶幹糞,但污水處理厭氧池內幹糞需進一步清理,人工溼地內植物生長效果不好”。
“我們真的努力了”
2015年1月1日,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正式施行。
銅鈴巖村村支書張自權的上任時間,也恰好是2015年初。“我一點都不喜歡養豬場。”午後兩點,他剛結束一個會議,到辦公室工位上坐下,打開方便麪,開水剛倒下,面還沒泡好,老百姓又上門來了。不用問,又是爲“水”的問題。
“養豬場就像一枚定時炸彈。你說它能拉動就業,但實際上在裏面打工的也沒幾個人。你說它能給當地政府帶來多大的稅收收益,但國家又對生豬養殖有補貼。總之,老百姓天天找我要水。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隱患。” 張自權皺着眉頭說。
成爲衆矢之的的福臨養殖有限公司卻認爲,“我們一直在努力”。
“2015年,(環保的)事就來了。我們按照縣環保局的要求建了厭氧池、人工溼地。但不知道爲什麼,糞排放進去,卻消化不了。”王傳國認爲是排污設備設計之初,把生豬的出欄量考慮太少的緣故。“規劃的時候按照1500頭豬規劃,實際最多時每月出欄的豬有3000多頭。”
而縣環保局不認同。“厭氧池是國家幫扶建設的項目,建成交付給業主單位以後,本應該由業主自身加強污水處理設施管理。加強幹溼分離處理後才能排入廠區內污水處理站。”
王傳國特別留心過當前畜禽養殖資源化利用的新技術,也曾經給老闆林某建議過,可以考慮使用現在國內比較流行的發酵牀。
也有發酵牀公司的技術人員到現場來考察過。一看是廢舊的水泥廠改建的豬場,連連搖頭。由水泥廠改建的豬場,每一個豬舍單元的長寬不規範。公司給出50萬元的報價。但由於廠區不規範,需要大規模地重建豬舍和配套設施,測算下來約要投入500萬元。
“光是發酵牀的菌種培養,一年就要幾十萬。”王傳國說。“據說發酵牀冬天還用不了,那我的污水又怎麼排?”老闆娘反問。
後來,王傳國又專門去了解了糞污零排放設備的投入,“成本太高”。再後來,尋求資源化利用的道路就不了了之。
當然,養豬場日常上千頭豬的糞污也要解決。廠裏最常見的做法是,僱了8個工人每天來撿拾幹糞。“50~60斤能裝滿一包。每人一天能撿出5包來。8個人一天可以撿2.5噸~3噸左右,然後再賣給村民。”王傳國解釋說。
“定時炸彈”終於炸了
2018年9月29日下午,李洪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是村支書熟悉的嗓音:“養豬場直接負責人林某被抓了。”那一瞬間,李洪不知道怎樣形容心中的感受,百感交集。倒是覃大姐心直口快:“高興,我是真高興。”
如同村支書張自權預感的那樣,這顆“定時炸彈”在2018年的5月徹底炸掉了。
一天,李洪從第3根水管裏接出水來,茶色的水質一下子點燃了他敏感的神經。和養豬場“鬥智鬥勇”多年,他早就練就了通過肉眼判斷水質是否被污染了的技能。這不正常的茶色提示他,“水又被污染了”。
環保部門現場檢查印證了李洪的判斷:廠區牆角外的水泥排水溝末端有養殖廢棄物外溢痕跡,下方農田內流淌有大量養殖廢棄物,延綿至場區東側的將軍山溪水溝。巴東縣環境監測站對養殖場廢水排口出水進行了監測取樣,並出具監測報告顯示,出水水質超過《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標準》限值要求。
縣環保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擬作出“責令停產整治”的決定。8月26日、9月18日,縣環保局又到現場督辦,福臨公司拒不執行,也沒有停止違法排污行爲。
同時,巴東縣環保局現場檢查又發現新情況,勘查發現養殖區有一個未完工的建築房區,裏面挖有幾處深坑,存有大量的廢棄物。福臨養殖有限公司承認,這是他們放置的, 打算把豬糞放裏面曬乾後運走。
巴東縣環保局認爲,在現場督辦中發現場區內挖有新的深坑和滲坑,“性質較爲惡劣,屬於逃避監管”,並依法將案件移交給公安機關。
相關知情人說,巴東縣地處湖北西陲,喀斯特地貌特徵明顯。地下巖洞的岩石具有一定的孔隙和裂隙,而一旦污水滲透入岩石的空隙中,就會在地下管道里橫衝直撞。
也就是說,村民賴以生存的第三根飲水管又不能飲用了。
“這次是怎麼回事,我們不知道啊……”10月10日,老闆娘在老闆被行政拘留的第10天前去探視。回到養殖場內眼睛紅腫,時而背過身去嚶嚶地抽泣。
覃大姐卻依然不解氣:“我們現在沒水喝了,每天都要用麻木摩托(當地改裝後的三輪車)到附近幾公里外運水喝。”李洪點頭,並指着自家一次能裝200斤的膠質袋說:“我們可以自己擔水喝,村裏那些留守的老年人怎麼辦呢?”
當“錢袋子”VS“菜籃子”
“養豬傷透了心。”福臨養豬場老闆娘說,“就算政府不關停,我們也不想養了。”
福臨養豬場直線距離兩公里開外,就是清江風景區。作爲國家生態功能區,巴東縣“關停並轉”了一批工業企業,爲的就是守好一江清水。但同時,巴東縣仍是深度貧困縣。
“我們當地政府也在開動腦筋,瞄準貧困戶,探索既能保護生態又能讓老百姓增收、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巴東縣委相關人士說。
客觀事實也一目瞭然。對當地老百姓來說,要深度脫貧離不開兩條路,一是外出打工,二是發展養殖業。留在農村的老百姓大多選擇生豬養殖這條路。
養豬能脫貧嗎?以飼養20頭母豬的豬場計算,一頭母豬一年可以產2.2胎,每窩生產約10頭小豬,一頭母豬一年可以出欄20頭育肥豬。每頭肥豬可以賺到350元~500元。20頭母豬一年可以出欄400頭育肥豬,基本上能賺到14萬元以上。巴東縣野三關鎮一家貧困戶從事生豬養殖,1年後賺了20萬元。同時糞污還田,養殖和周邊農戶種養結合也得當。
俗話說,“民以食爲安,豬糧安天下”。豬肉是我國城鄉居民生活消費的必需品,其價格的浮動直接影響着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可以稱爲養殖戶的“錢袋子”,老百姓的“菜籃子”。
同時,生豬行業卻深受“豬週期”困:豬肉價格上漲會刺激農民積極性造成供給增加,供給增加造成肉價下跌,肉價下跌打擊了農民積極性造成供給短缺,供給短缺又使得肉價上漲,週而復始。
這一經濟現象背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我國生豬行業規模化養殖的佔比相對較小。國外經驗表明,當規模化養殖佔比越高,豬肉價格就會趨於穩定,產業風險也將可控。作爲調控“豬週期”的重要手段,規模化、標準化養豬將成爲穩定豬肉價格的有力探索。
“近年來,我國生豬養殖規模化水平提升比較快,但比重仍偏低,規模化佔比還不到一半,2016年纔到45%。”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祖力表示。
國家鼓勵規模化養殖,但如前文所述,當養殖和環境產生矛盾時,在“錢袋子”和“菜籃子”中該如何抉擇呢?
◆ ◆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於法穩介紹了我國畜禽養殖污染相關情況和解決模式。
除了關停還有別的辦法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於法穩介紹說,近年來,我國畜禽養殖總量不斷上升,2016年大牲畜年底存欄頭數爲11906.41萬頭,產生大約30億噸畜禽糞便。“這些畜禽糞尿資源化利用還沒有找到有效途徑,導致畜禽糞尿污染嚴重。同時,由於畜禽糞尿處理率較低,大部分進入環境,造成環境污染。”
一方面是讓百姓增收的畜禽養殖產業,另一方面是亟待保護的生態環境,兩者能否兼顧?其實,銅鈴巖村村支書張自權一直有他的思考。他曾和養豬場老闆溝通並提出一個解決方案。比如建造沼氣池,把產生的廢棄物循環利用起來,輸送沼氣給村民用。他還想“藉助精準扶貧的路線,讓老百姓共同致富”,“如通過養殖大戶和村民進行利益捆綁的模式,養殖場作爲技術指導,指導農戶養豬”,但因爲種種原因,想法沒能最終落地。
在於法穩看來,這些設想其實已有成功案例。另外,畜禽養殖大戶也可以和當地農民建立互惠互利的模式,於法穩把它稱爲利益聯合體:“通過村集體成立一個合作社,村集體和公司共同經營。在新型合作社經營下,集體經濟抗風險能力強,也能實現農民增收。”
於法穩以山東棲霞蘋果生產舉例,當地村子就是採用上述合作模式,在畜禽糞便等有機肥資源豐富的區域,鼓勵種植大戶和專業合作社集中積造利用堆肥,削減養殖場產生的糞污。
事實上,從全國情況來看,畜禽養殖業資源化利用已有成熟的模式。根據農業部畜牧業司2017年的相關統計,我國目前在畜禽糞污資源化處理上主要有7種典型模式,分別是糞污全量收集還田利用模式、糞污專業化能源利用模式、固體糞便堆肥利用模式、異位發酵牀模式、糞便墊料回用模式、污水肥料化利用模式、污水達標排放模式。
不少養殖場戶糞污管理水平低,也沒有找到低成本治理糞污和“有利可圖”的資源化途徑,因而大量糞污得不到有效處理和利用直排導致污染。針對這一問題,廣西壯族自治區環保廳廳長助理孔源博士認爲,一方面,政府要加強組織、監管和引導,推動養殖場戶配備糞污腐熟和糞肥貯存池等必要設施,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導構建糞肥收運還田的市場化機制。
“以銅鈴巖村這家養殖場爲例,可以採用‘全混原漿、就地腐熟、就地貯存、就近利用’的方式,推動規模化養殖場配備足夠1~2個月糞肥產生量的貯存池和收運噴施車輛,並與當地的種植基地或需肥農戶結成糞肥供需市場化關係,解決糞污資源化問題。1臺收運車、1~2個工人,將積存的沼液糞肥賣給種植戶並噴施到位。”孔源說,這樣不僅能大大降低養殖場糞污治理的成本,又能大大降低種植戶施用有機肥的勞動強度,免去購買和施用化肥的成本。對養殖戶來說,只需配備腐熟池(沼氣池或化糞池),不需要“乾溼分離”等複雜的設備和處理工藝,就可以實現糞污“用得掉、不排放”;種植戶用購買化肥一半的價格買到了糞肥和施肥服務,便捷省力,提質增產。如果周邊種植戶一開始不能普遍接受沼液糞肥還田,可以嘗試示範戶先行。
條條道路通羅馬,如果真的有心,養殖業和環境保護並非是對立項。破題的關鍵,取決於政府的智慧和企業的責任擔當。
太陽之下,大山之中,一個跑長途運輸的司機開着貨車經過這裏。經過村口附近,他掃了一眼路邊立着的一個牌子,上面寫着:喫住圍欄壩,暢遊清江河。而清江,就在不遠處。
(截至記者發稿前獲得的最新消息顯示,福臨養殖有限公司承諾將於今年12月15日關閉清場。水布埡鎮政府指派水務中心於10月10日組織實施村民取水工程,16日已完成施工。目前村民已經喝上乾淨水。)
來源:中國環境報
作者:張春燕 童克難 王珊
編輯:周亞楠
更多精彩,請關注中國環境APP
長按識別左邊二維碼關注我們
蘋果版+安卓版
中國環境新聞投稿
長按二維碼關注我們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