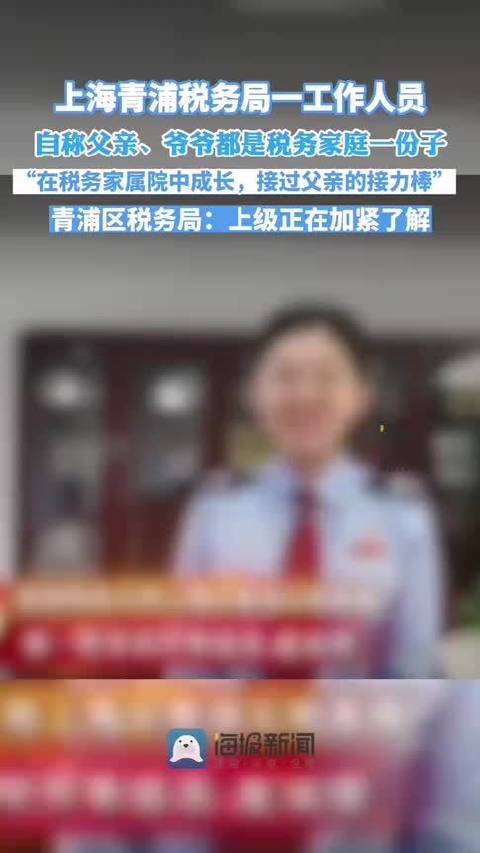作爲悖論的“家園”揭示了一種靈魂的狀態
8月20日,爲期一週的第十六屆上海書展落幕。在同期舉辦的第九屆上海國際文學週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幾十位作家和藝術家聚在一起,共同討論了一個意涵豐富而又含混的詞語——家園。這也是今年文學周主論壇以及書展多項活動的主題。
近年來,隨着城鎮化和現代化的突飛猛進,越來越多的討論被引向“逃離北上廣”、“田園將蕪胡不歸”這樣的話題中,箇中原因固然有城市生活壓力所投下的巨大陰影,但其背後或許還隱藏着“出走與返鄉”這一原始心靈結構的影響。在今天,很多堅固的東西都如哲學家所言煙消雲散了,家園也正在失落,不管是鄉村還是城市,都處於一種斷裂、消逝的狀態。除了“形而上”的家園,“家”這一相對“形而下”的具體的概念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變革。有人因此提出——網絡時代,何以爲家?人們理想中的家園,可能是不斷追尋而不得的桃花源,也可能是被迫遠離只能懷念的原鄉。
每個人都有探尋生命原點的渴望,因此有了回望的姿態,有了歸鄉的動作,有了書寫的訴求。在這樣的一種努力中,“家園”揭示了一種靈魂的狀態。
2019年8月14-20日,上海書展在主會場上海展覽中心和衆多分會場舉行。
在探討家園的意義時,我們或許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是——家園是什麼?
這是個初聽起來簡單明確、深思起來卻雲遮霧繞的問題。要知道,在很多語言裏,並沒有“家園”這個詞語,它通常被解釋成家、家屋、家鄉、故鄉、故土、鄉關等等看起來面目相似卻充滿歧義的語彙。
對每個人來說,家園都有着不同的定義。它充滿了不確定性,也因此充滿了無限的闡釋可能。在今年的上海書展上,許多作家與藝術家分享了自己對於家園的理解,以及各自的家園故事,這些理解或具體,或抽象,我們也得以感受到個體生命之豐盈,語言世界之廣闊。
家園,一個浮動的語詞
家園的不確定性,首先來自於“家”這個詞語在物理空間上的位移與變化。很多人的一生都在不斷遷徙,從故鄉到異鄉,從此處到彼處。從前,古代的遊牧民族隨着自然變遷而東奔西走,而今,現代的城市居民因爲社會經濟的原因而顛沛輾轉。
我們習慣於把自己出生的地方稱之爲家園,但對於作家馬原來說,他很小就離開了自己的出生地,已經忘卻那個地方的樣子。所以他將後來在他精神世界中留下重要印記的三個地方定義爲家園——下鄉插隊時的遼寧農場,寫作爆發時期的西藏,晚年安居終老的南糯山姑娘寨。它們都不是他的故鄉,卻是他的家。
另一重變化來自於時間。世界在變,我們的居所也在變,當它終於變成了我們所不認識的模樣,我們是否還可以稱其爲家園?當城鎮化和現代化迅速吞噬我們原來的居所,我們是否正在失去我們的家園?而對於已經走出家鄉的人們,家園究竟是在擴張還是在消亡?有時候,不僅是被我們稱作家園的事物在變,我們對家園的認識也在變。通過寫作“發明”了一個敦煌的葉舟覺得,中國幾千年裏沒有人能準確說出自己的根在哪裏,家園兩個字,歸鄉兩個字,是隨着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
如此,家園似乎成了一個空蕩蕩的詞語,一張空頭支票,在某些人的心中,它很可能被簡化成戶口簿上的一個籍貫。
被迫離開家園。安哲羅普洛斯《哭泣的草原》劇照。
家園,一個恆定的語詞
但是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家園是某處永恆不變的場所,一個不會因爲時間飛逝而變得面目全非的場地,一個不會因爲場景改變而寂寞荒蕪的地方。
這更多關涉到家園的精神意義,而非物理意義。物理意義上的家園存在於家屋之中,但其中也必然包含着穩定的精神,比如托爾金筆下的霍比特人的家園——夏爾。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裏將家屋比爲宇宙,他形容道:“一座龐大的宇宙性家屋潛藏在一切關於家的夢中。大風從它的中心擴散開來,海鷗從它的窗裏飛出。這樣充滿動力的家屋讓人能夠居住在宇宙中。或者,宇宙來到他的家屋中居住。”這個家屋是夢想的中心,充滿了永恆的琥珀色的溫暖。
作爲美好家園象徵的霍比特人家鄉夏爾(The Shire)。
法國作家白蘭達·卡諾納認爲,家園深深印刻在兩個地方。一個是有形的區域,人們通過內心、精神和時間的選擇將其據爲己有。她將自己在諾曼底買的房子稱爲家園。它孤零零地佇立在田野中間,田野之中還有一棵孤零零的橡樹,這棵橡樹經常有些細微的變化,它使白蘭達時常保持一種警覺的日常練習,一心一意,集中精神,並提供所有的靈感來源。在她的眼裏,這棵橡樹便是世界的中心,並非幾何學意義的中心,而是情感的中心。通過她的命名,家園擁有了不變的心靈原點。
另一個純粹精神性的家園則存在於語言之中。對於白蘭達而言,這個家園便是她的母語法語。每個人都熱烈地生活在自己的語言當中,它覆蓋着所有人居住的土地。當我們寄居他鄉時,是語言的懷抱在那個時刻緊緊地將我們摟抱在一起。作爲母語的語言,以及作爲書寫文字的語言,將家園固定爲一個永恆的形象。
家園要有安心的感覺,角田光代如此認爲。因爲愛讀書,她在翻開書頁的那一瞬就能感到自己的身體進入了書的世界。書中世界的體驗越強烈,對我們的影響越大,不管過去多少年,不管長成什麼樣的人,都不會改變。因爲體內有我們所閱讀過的世界,我們甚至不用翻開書頁,僅僅通過回憶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迴歸家園。
對於作家而言,這似乎是一個無比正確的答案。它將家園的精神奧義無限提純,濃縮到了一個幾乎不會改變的世界裏。
家園,一個想象的語詞
或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家園已經具有了想象的質地。描繪創造了中州世界裏的袋底洞的插畫家約翰·豪認爲,家園是一片故事被講述的土地,也是一片想象的土地,那裏孕育出故事,孕育出圖像。
托爾金的中州世界是一個基於現實的想象的家園。
我們總是用書寫和想象的方式對家鄉進行“翻譯”,或者說重構。通過想象,地圖上的原點被展開爲一個可以抵達的事物,一個嶄新的家園。
在單純的想象力領域裏,回憶中的冬日與風暴甚至增加了家園的魅力。它建設在充滿霧氣的想象中,包含着種種非現實的色彩,在現實與非現實的交界處震盪。
在劉亮程的眼中,一個人的家鄉是他自己不斷創造出來的。家鄉的那個原點在我們出生的那一瞬間把這個世界的陽光雨露,把這個世界的風聲、太陽、月亮和水,把我們從祖先接續過來的那一秒呼吸全部給了我們,當它給了我們這些的時候,家鄉已經一無所有,所以我們只能在自己的成長當中不斷地建構家鄉。
劉亮程認爲,中國人不像西方人,在上面構築了一個天堂,我們是在子孫萬代的厚土中構築了一個家園,地下有厚實的一個祖先存在,而在地上又有蓬勃的千秋萬代的子孫。所以每個中國人其實都是這樣的生活,他的家園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他所理解的家鄉就是我們地上的生活家園,而故鄉則沉入地下,變成了我們的骨脈。
另一方面,當一個人開始閱讀文學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在內心塑造他的家鄉,這個家鄉不斷變大,不斷變得廣遠,但是又不斷地在縮小。到最後,家鄉縮小到那個我們出生的原點上,縮小到我們內心中那個叫做靈魂的地方,這就是一個人從現實的家鄉出發最後回到內心的故鄉的過程。無論是《一個人的村莊》還是《捎話》,劉亮程所塑造的,都是一個文字裏的故鄉。
《何以爲家》劇照。
家園作爲悖論
但家園也是一個悖論。只有當我們客居他鄉時,才能更深切體會家園的存在力量。在約翰·豪的心中,家園是我們心嚮往之卻永遠無法抵達的地方,它具有“靈魂深處的渴望、精神存在身體卻不在的神聖以及時空角度的偏差”。
另一個有意思的悖論由金雯提出。她提到了引力的概念,它使我們感到踏實但也同時束縛了我們,給了我們不可見的壓力。家園和引力相似,它是我們安全的歸屬,也可能是我們步履不前的阻力。永遠似乎雙腳着地、但永遠無法停下的“墜落”意象生動詮釋了家園的定義。
這些悖論似乎在哲學的意義上回應了那個關於“何以爲家”的問題。家園總是和追尋的動作聯繫在一起。作爲我們心靈中的一個原點,理解家園意味着理解我們是誰,我們駐守何地,我們去向何處。這是一切的根本。這座想象的家園、浮動的家園、恆定的家園,通向的是詞語背後不具名的形形色色的“我”,揭示了各自不同的靈魂狀態。
或者說,家園是人類生存方法的顯現。在德語中,“家園”一詞約等於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和氛圍。在漢語中,“家園”一詞是農耕文明時代的剪影。陶淵明那句“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顯現了所有追尋家園不得但又永遠追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