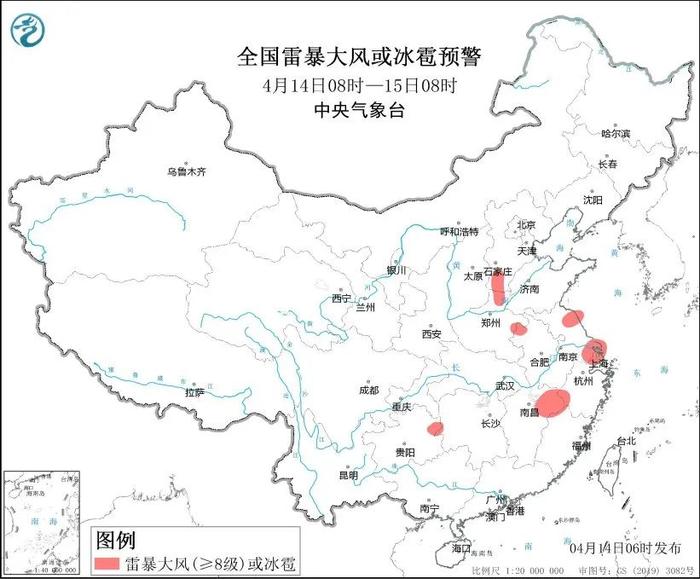我的筆深深扎入故鄉的土地——訪作家徐兆壽
徐兆壽作品
蘭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華靜文/圖
徐兆壽
1968年生,甘肅涼州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教育部新世紀人才、甘肅省“四個一批”人才。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全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甘肅省首批榮譽作家。
1988年開始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詩歌、小說、散文、評論等作品,共計500多萬字。長篇小說有《非常日記》《荒原問道》《鳩摩羅什》等8部,詩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麥穗之歌》等3部,學術著作有《文學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學的困境與超越》等20部,獲“全國暢銷書獎”、“敦煌文藝獎”、“黃河文學獎”、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十多項獎,在《新華文摘》、《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小說評論》、《文藝爭鳴》等刊物上發表文學評論百餘篇。
記者眼裏的徐兆壽先生,談吐優雅,舉手投足間彷彿蘊含着悲天憫人的情懷。與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很多人一樣,徐兆壽在小時候也經歷了飢餓和貧困,因爲是家裏的長子,他過早地擔負起家裏的責任。“上世紀80年代初,我還讀小學的時候,因爲家裏太窮,父親便要出去拿清油換些零錢,以貼家用,我便常常會頂替父親去充當勞力,那時我的心裏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拼命讀書,將來擔起家裏的責任。”徐兆壽對記者說。
到了中考的時候,徐兆壽成績考得很好,很多人勸他讀高中,但是他爲了減輕家庭的負擔,沒有選擇讀高中,而是去了師範,“至少畢業後有工作了。我不想給父母親帶來太多的壓力。”徐兆壽淡淡地說,“雖然選擇師範是客觀原因造成的,但是在師範的三年卻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有幾個初中同學後來去讀了高中,一見面就說學習壓力如何大,而我們上師範的同學呢,每天都在愉快地學習文學、音樂、美術,甚至體育。我們當時沒有升學壓力,畢業後就可以就業,所以藝術興趣得到極大地發展。我那時喜歡唱歌,儘管唱得不是最好,但仍然興趣極大。在校期間,我學習了二胡、笛子、鋼琴,還練過聲……”在輕鬆愉悅的學習環境下,徐兆壽很快就喜歡上了寫作。“那時我每天都拼命地讀書、寫作,後來學校推薦我去參加由西北師大中文系和甘肅省語文教學學會舉辦的甘肅省首屆語文夏令營活動,那一次活動對我來說是人生的轉折,因爲我認識了很多高中生朋友,他們的目標是北大、清華、復旦,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暗淡無光,於是萌發出對外面的世界的無限的嚮往。”也就是這次活動回去後,徐兆壽聽說師範生可以保送上大學了,於是,他的願望更加堅定。
可是,由於家裏太過貧窮,徐兆壽的父親並不同意他讀大學。“其實我很理解父親當時的壓力,一點都不怨恨他,後來在親人和鄉親的勸說下,我也保證上學不要家裏提供費用,父親才勉強答應了下來。那個時期,我們村裏只出過兩個大專生,三四個中專生。”當時,徐兆壽是家鄉唯一的大學生。
進入大學後,徐兆壽如願以償地讀了中文系。“一拿到教材,我發現一年級甚至二年級的很多內容我在中師時就學習過了,於是,我便開始讀大量的外國文學、哲學,開始真正地寫作了,我夢想要成爲一個詩人或作家。同時,學校組織聯歡晚會,動員有藝術才能的同學表演節目。那時,最流行的樂器是吉它,我因爲之前學習過鋼琴和二胡、小提琴,便在一個晚上學會了吉它的指法,又花了一天便學會了一首很簡單的樂曲。我以爲大家都在報節目,便報了吉它獨奏和電子琴獨奏兩個節目,誰知道最後上演時只有幾個節目,我上了兩次。我想我當時的才能都是師範生活給我的。幸運的是,我擁有了更多的才能,也葆有了更爲自由而飽滿的性情。這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徐兆壽麪帶笑容地說。
徐兆壽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圖書館讀書、寫作,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做學生工作,剩下三分之一的時間上專業課。畢業之後,徐兆壽順利留校並保研。徐兆壽說,那時我們同一級中的師範生很多都留校並保研,這與當時的教育背景是分不開的。
2010年,徐兆壽來到了復旦大學,開始了新的求學之路。“那時我沉迷於西方哲學與科學。尼采、薩特、海德格爾、康德、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牛頓、愛因斯坦、霍金……文學方面的閱讀更不必說了,我也會經常翻閱《論語》《道德經》《莊子》《史記》……”在復旦上博士後,來自不同文化的衝擊讓徐兆壽深感震撼:“我知道,很多人對西部,乃至甘肅的誤解很深,他們認爲這裏貧困、愚昧、落後。我曾爲此黯然神傷。我開始站在上海重新仰望自己的故鄉,眺望古絲綢大道,自然也開始重新理解我的故鄉涼州。”原來徐兆壽是準備留在上海的,但有一年回家時,從飛機上看到荒山野嶺、一望無際的大西北時,他禁不住忽然間熱淚盈眶。他聽到飛機上有人譏笑說,太荒涼了,連草都沒有,人怎麼生活呢?徐兆壽在心裏默默地回答着,你們根本不懂這片山川和荒漠!於是,徐兆壽下定決心回到大西北,回到自己的故鄉,也開始把筆緊緊地紮根在大西北。“我開始寫絲綢之路,便是從古印度傳來的‘佛教’。我第一次深入地領會了佛教如何匯入中國文化併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於是後來有了《鳩摩羅什》這部著作。”徐兆壽說。
談起《鳩摩羅什》這部作品,徐兆壽很是感慨:“其實這部作品的創作離不開我的故鄉情結,更離不開我的奶奶對我的影響。她信佛,雖然自己也貧困,但是樂善好施。小的時候,奶奶的很多做法經常讓我不能理解,但是人到中年之後,我越來越懂得了她的慈悲,也爲我日後研究鳩摩羅什打開了一扇心門。”
鳩摩羅什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座高峯,他不僅是佛學經典的翻譯巨匠,更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功臣。而文化的交流不僅僅是知識在不同地區的傳播,更加深遠的影響是使得文化的火種得以保存,保存的是“星星之火”,日後留給我們的就是“燎原之勢”。信仰的力量讓他雖百難而不辭,敢於赴死,敢於忍辱。鳩摩羅什的降臨把天竺、西域和中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潛心修行的父母給了鳩摩羅什一個信仰,一個一生的信仰,這個信仰成爲了鳩摩羅什畢生的追求。徐兆壽說:“在我看來,在一千六百多年後的今天,‘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鳩摩羅什彷彿又回到了人間,就像他從來沒有離開一樣。漫天的黃沙已然消失不見,‘一帶一路’的‘路’日漸清晰,鳩摩羅什作爲連接中印兩大民族的歷史人物理應被我們銘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鳩摩羅什對絲綢之路的繁榮做出的貢獻理應成爲今天‘一帶一路’倡議的座標,以此來丈量‘一帶一路’的前世今生。”
昔日佛國聖景的涼州今天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城市。鳩摩羅什在涼州的經歷至關重要,就是在這片土地上,鳩摩羅什學習漢字、研讀經典、弘揚佛法。在鳩摩羅什離開涼州時,信衆上至王室,下至村舍,一派佛國聖景,令學佛之人心嚮往之,也爲其日後在後秦的大規模譯經和向中原地區弘揚佛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如此重要的時期,可是史料記載卻寥寥無幾。在創作這部著作時,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徐兆壽不辭辛苦,多方求證,研讀佐證史料,發揮作家的想象,才使得鳩摩羅什躍然於紙上。
近些年,徐兆壽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教學上,同時也參加很多公益性的講堂。在一次金城講堂的講解中,徐兆壽花了大篇幅分享了孔子《論語》的部分經典。記者問他爲何對此感受頗深,他說:“孔子開創了儒學,是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我在曲阜時,用兩個半小時的時間走完孔林。在那裏,我看到的是一種震撼,世間僅此一人,被人紀念了幾千年。一座墳頭接着另外一座墳頭,有碑的,都是孔子嫡系子孫;有墓的,盡享受了孔子的榮耀。孔子的思想,掩蓋了他的子孫的光芒,甚至是所有人的光芒。不可否認的是,因爲孔子的出現,中華民族有了一盞明燈。”
採訪到了最後,徐兆壽總結道:“不管是作爲作家,還是作爲一個教育工作者,要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而這一切的精神的匯聚地,正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我記得季羨林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在當今世界上,人類所有偉大的文明共生的一個地方,就是以敦煌爲中心的西域。我有理由和責任回應來自世界的種種疑問,我也必須以這樣的方式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權,把話題引到中國,再引向絲綢之路這個古代歐亞交流的廣闊場域中,來重新探討中國與世界的命運。”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