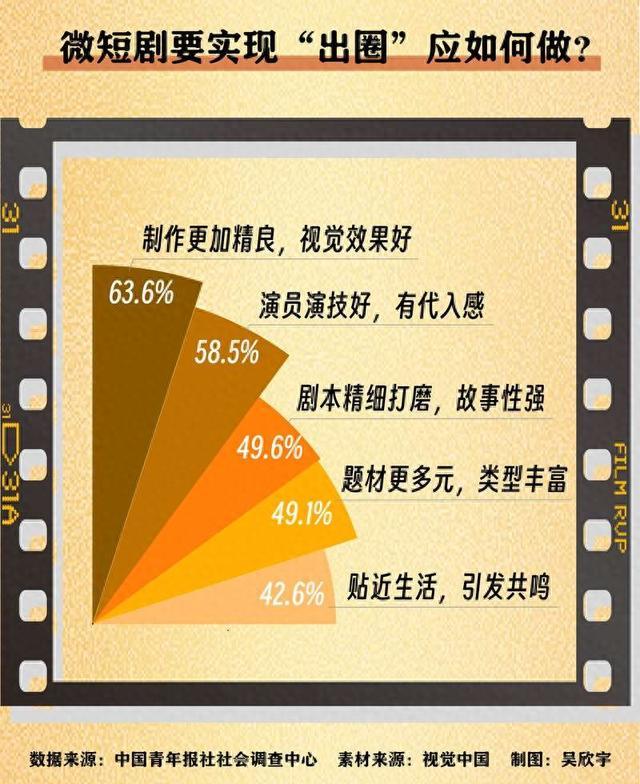阿來:《攀登者》劇本中的人物和細節,都來源於真實
摘要:澎湃新聞:看劇本時候印象很深的一點是,你花了很多筆墨去寫那些因爲各種原因沒能登上珠峯的人。澎湃新聞:那在接觸、採訪這些人的過程中,是否有把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真實細節、故事寫到劇本中。
國慶期間,《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中國機長》三部主旋律影片“三足鼎立”,扛起了國慶檔的票房。其中,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攀登者》將關注點放到“登山”這個國內不常見的電影題材上,尤其引入關注。
《攀登者》中的兩個時間點均有真實歷史可依。1960年,中國登山隊貢布、王富洲、屈銀華3名隊員完成世界上首次從北坡登上珠峯的壯舉,但由於沒有留下影像資料,一直不被國際承認;1975年,中國登山隊再次衝擊珠峯,共有9人成功登頂,其中包括一名女隊員潘多。
《攀登者》
這兩段登山歷史交錯閃回,構成了《攀登者》中激動人心的故事。除了強大的明星陣容,《攀登者》還請來了茅盾文學獎得主、藏族作家阿來擔任編劇。電影上映之際,他創作的文學劇本《攀登者》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一直都關注這段歷史。”由於拍攝週期緊張,留給劇本創作的時間十分有限,接到創作邀請後,從起筆到完成初稿,阿來只用了兩週時間,堪稱“神速”,阿來坦言速度背後源於自己長期的積累。他自己熱愛登山,前輩登山者的事蹟他也早有了解,甚至找機會見過許多當年的登山者,阿來和他們握手,經常伸出手,卻發現對方袖子是空的。
這些多年來阿來傾聽過的故事,以及積累下來的真實可感的細節和感受,成了《攀登者》中的脈絡和素材,“書中的很多細節都是真實的,瞎編不來。而且我覺得,對於這些平凡人的英雄事蹟,胡編亂造本身也是對他們的一種冒犯。”
9月29日,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阿來,雖然電影已經開始上映,但他坦言自己打算過一段時間再走進影院。最終上映的影片和阿來寫成的文學劇本不盡相同,阿來表示出版自己的劇本,是想要“保留一個能更充分展示自己個性的劇本”,“大家也可以把電影和原始劇本兩相比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阿來 資料圖。 來源:@阿來
【對話】
兩週時間完成劇本
澎湃新聞:寫劇本只用了不到兩週,也可以說是一氣呵成了,爲什麼這麼快?
阿來:去年這個時候我剛寫完《雲中記》,上影的董事長任仲倫突然找到我,說要拍《攀登者》這個戲,希望我寫劇本。當時這個電影已經確定要在今年十一期間上映,時間非常短,從寫劇本到拍攝完成上映只有一年時間。留給我總的寫作劇本的時間只有一個月多一點,因爲電影中冰雪的場景太多,只能在冬天拍攝,當時馬上要進入拍攝,到11月中旬就開機了。
劇本寫好之後,我後來還修改過一版,但當時那兩週確實是用了很多精力集中寫作,連出國都帶着寫。
澎湃新聞:之前連自己的小說影視劇都拒絕當編劇,爲什麼這次同意了?而且是創作一個全新的劇本。
阿來:如果改編自己的東西,故事之前已經講過了,再講一遍就沒有興趣了,純粹是碼字換錢。我還是希望寫一個新故事,《攀登者》只不過是用劇本的形式去寫。寫作一個新故事這件事有吸引我的地方,能夠發現故事中蘊含的值得發掘的東西。但如果是寫過小說之後改成劇本,多半我還是讓別人改。
接下這個劇本一方面是因爲我自己比較喜歡山,在登山技術方面也比較熟。登山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事情,怎麼解繩索、怎麼用工具,都有專門性的知識,我雖然沒有爬到珠峯那麼高過,但還是有登山經歷,有專業知識。
澎湃新聞:我看劇本的時候注意到你描寫到很多關於登山非常細節性、專業性的東西,當時也很好奇你是事先做了很多功課還是你自己本身就登過山。
阿來:作爲經常在山上走的人,這些細節還是清楚的,不然上去下不來。
澎湃新聞:你自己登過最高的是什麼山?
阿來:每個人登山的目的不同。有的人就是爲了創造登高紀錄,我們在山裏是爲了更廣泛的考察。我登山一般不會超過6000米,因爲超過5000米,山上一般就沒有什麼生命痕跡了。我自己是希望在生命世界去觀察動物、植物。每個進山的人目的是不一樣的,追求也是不一樣的,我主要是去觀察高海拔頑強的動植物生命,而不是爲了刷新登山記錄。五六千米的山有時候就爬上去了,但我沒有刻意去登頂。
《攀登者》劇照
始終關注中國登珠峯這段歷史
澎湃新聞:是接到劇本創作任務就馬上開始寫了是嗎?
阿來:我剛好自己熱愛登山,前輩登山家的事蹟我之前就都很熟,而且其中很多人我都有接觸,比如1960年衝擊頂峯的4人組,3個人登頂成功,一個人差點上去,4個人我都接觸過。最後一次採訪過他們之後,不到一年時間就走了3個。後來那些登山者見到的就更多了,我不光了解他們是怎麼登山的,他們的性格、經歷,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我都多少了解。如果沒有這些平時的積累,一下子是憋不出這些東西的。
澎湃新聞:那在接觸、採訪這些人的過程中,是否有把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真實細節、故事寫到劇本中?
阿來:那些生動的細節是編不出來的。比如書裏寫到李國樑犧牲以後,他的戀人後來登珠峯,把他骨灰帶上了山頂。這就是後來我採訪西藏一個女登山家瞭解到的故事,雖然不是發生在1975年登珠峯那次。西藏登山隊後來成功登上了所有14座高於8000米的山峯,其中就有一對夫婦,丈夫在登其中一座山過程中犧牲了。後來這位女登山家去攀登她丈夫失去生命、沒有成功登頂的這座山峯的時候,就把丈夫的骨灰帶到山頂幫助他完成心願,還把一部分骨灰留在山頂。
書中的很多細節都是真實的,這些瞎編不來。而且我覺得,對於這些平凡人的英雄事蹟,胡編亂造本身也是對他們的一種冒犯。
澎湃新聞:劇本中涉及了很多真實人物,比如夏伯渝在當年登珠峯的過程中失去了雙腿,去年5月他以69歲高齡,成爲第一個無腿登頂珠峯成功的人。在劇本結尾處,你寫到的“夏伯陽”這個人物多年之後也登上了珠峯。
阿來:對的,我把這個人物命名爲夏伯陽,是因爲夏伯陽是蘇聯的戰鬥英雄,那時候很多人是很崇拜他的,後來劇裏面把這個名字改掉了,其實是很有時代氣息的一個名字(注:即胡歌扮演的楊光)。
我在寫作期間認識了老夏,他通過現在商業化登山成功登頂了,我也把這段寫進了劇本結尾,這和當年的國家使命是不可同日而語,但商業化登山確實也是一種方式,讓當年未能登頂心懷遺憾的人現在有機會衝擊珠峯。
《攀登者》劇照
澎湃新聞:你對登山這段歷史的關注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阿來:我始終都關注。現在有些人是需要寫作纔去臨時蒐集資料,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去了解這個世界,不要那麼功利。現在大家都關注娛樂圈八卦,我覺得倒不如多去了解一些這些東西。
我之前就知道很多關於登山者的事情,也見過很多人。他們都爲登頂珠峯付出了很多,我和當年登珠峯的人握手,經常伸出手去發現(對方袖子)是空的。到這個劇本找到我,距離我最後和那些登山者見面、告別已經五六年了,當時我去了解他們的故事,並沒有說是爲了去寫點什麼,就是出於興趣。
不該忘記未能成功登頂的人
澎湃新聞:現在出版的這個劇本是最初的版本嗎?
阿來:這是第二稿。爲什麼我想出這個書,是因爲我知道劇方拿到劇本到拍成電影,最後肯定還是要做改動。我想保留一個劇本的原始面貌,保留一個能更充分展示我的個性的劇本。大家也可以把電影和原始劇本兩相比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澎湃新聞:看劇本時候印象很深的一點是,你花了很多筆墨去寫那些因爲各種原因沒能登上珠峯的人。趙軍釗燙傷了,還有隊員因爲襪子沒烤乾凍傷,夏伯陽則是因爲把睡袋讓給別人凍傷了。到最後一次真正登頂成功反而只有簡單幾筆。爲什麼把焦點對準這些人?
阿來:對,這個劇本我始終堅持一種比較現實主義的風格。對文學而言,付出努力而未能成功的犧牲者,他們的故事命運有更多打動人的力量。
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只有成功,登山本身就是一個團隊的事情,一些人成爲英雄,背後有無數人的犧牲和付出去支撐。比如1960年中國第一次成功登頂珠峯,做出很大貢獻的是未能登頂的劉連滿。他在陡峭的第二階梯處搭人梯把其他3個人送上去,把自己體力耗盡了,只能留下。在那麼高的海拔,又冷又餓,大家都以爲他要死了。他自己也覺得自己肯定要死了,隊友留給他的氧氣他也沒有用,寫了紙條說把氧氣留給隊友們下山時候使用,然後把氧氣關掉,在那裏等死。後來隊友下山之後他奇蹟般地活下來了。但最後得到更多獻花掌聲的,是那3個成功登頂的隊友,不是說他們不應該(得到這些),但我們也不該忘記未能成功登頂的人。
澎湃新聞:你是個自然愛好者,經常關注動植物,但登山似乎更偏向於人如何去挑戰自然,你怎麼看其中的區別?
阿來:1960年的登山和現在不一樣,不是簡單的戶外運動,是我們要在自己的領土上打上印記。那時候登山,有宣誓主權的含義,意義非常重大。1975年那次登山,同時是對珠峯大規模的科學考察,有些科學家都犧牲在那裏。
當然今天登珠峯已經是很商業化的活動,登珠峯的人都有錢,確實也會製造大量的垃圾,今天要提倡環保,就是希望登山的人顧及環境,把帶上山的垃圾再帶下來,並不是說珠峯就不能登。
今天登山的人動機都非常複雜,但不管什麼動機,通過登山達成動機的同時,要記住在完成自己傳奇的同時,不能像之前那樣把垃圾扔在峯頂一拍屁股就走人,這確實對珠峯環境造成了負擔。尤其是現在全球變暖之後,很多垃圾隨着冰川融化開始向山下的水源滲透,這確實需要引起注意。但我也反對原教旨主義認爲珠峯不能登的態度,珠峯也只是一個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