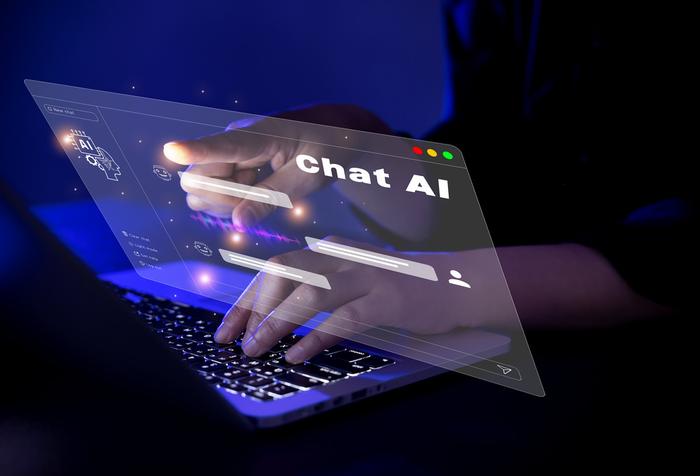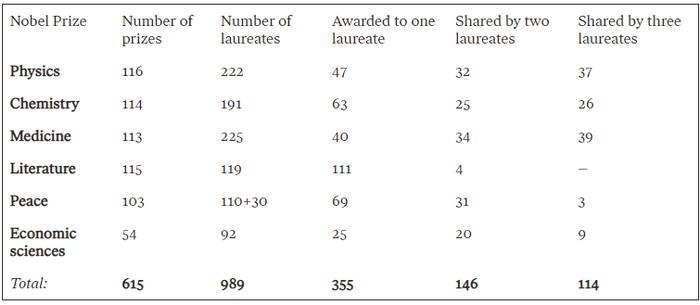故事:我和二奶是同行
文/龔清楊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佈】
我是在一家酒店認識阿青的。那天中午,大款趙江請客。到酒店後,我注意到趙江又換了一個情婦,趙江換情婦就像換衣服一樣非常勤。與他以往那幾個妖里妖氣的情婦不同,這個情婦的氣質很好——她紅潤的嘴脣上懸掛着一種恬靜的微笑,大大的眼睛初看起來很清澈,可仔細看卻很深遂,有一種蒙娜麗莎的味道。
趙江介紹我時顯得很突兀:“這是我們市著名作家周旋,寫黃色小說的專家,哈哈哈!”冤枉呀!我從未寫過黃色小說。當着一桌子客人,我窘得臉發燒,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接着趙江又指着她身邊的情婦說:“這是我的二奶阿青,別看她長得文文靜靜的,可牀上功夫絕對是一流的。哈哈哈!諸位如果有興趣可以試試,我趙某人絕對不喫醋。”阿青既不羞澀,也不憤怒,她若無其事一樣微微一笑。
我沒有想到阿青竟然會是這樣一個恬不知恥的人!一剎那,阿青給我的良好第一印象蕩然無存……
當我的記憶幾乎把阿青擦掉的時候我又一次見到了她。那天下午,我正在街上走着,一輛嶄新的桑塔納突然在我身邊嘎然而止。車剎得很急,剎車聲像一柄鐵錘驟然砸在一口大缸上一樣一樣刺耳。我嚇了一跳,還以爲是黑社會的人來綁架我呢。車窗打開了,一個時尚女郎探出頭說:“周作家,去哪裏?我送你一程。”我一看,愣了,是阿青。我當時想說不,可是,瞅了一眼她那嬌美動人的臉蛋後,卻鬼使神差般上了車。
阿青把車子開得飛快,讓我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我萬萬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嬌滴滴的姑娘開起車來,竟然像個瘋子一樣。約半個小時後,阿青把車開到市郊區的一個湖畔停下來了。
此時已近黃昏,夕光金子似的在碧波盪漾的湖面上跳躍,看上去很美。我和阿青在湖邊緩緩散散步,我想,不瞭解底細的人一定會認爲我們是一對情侶。
“周作家,我現在內心很矛盾,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所以就想請你爲我指點一下迷津。”阿青仰起臉,用她那清澈而深邃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我。
我弄不明白阿青的意思。良久,我說:“你現在不是過得挺好嗎?有房子,有車子,還有錢。”
“不,你不明白!”她頓了頓,彷彿下了很的決心似的說,“周作家,其實我很早以前就認識你。那時候我還是個文學青年,寫小說、寫散文,我那時的筆名叫小草。你記不記得,五年前你在報社當副刊編輯時發過一篇《清貧的生活》的文章?就是我寫的。”
剎那間,我的內心中湧起一種異樣的感覺。我記得,我當時爲作者清麗的文筆和巧妙的構思所折服,認爲她是一顆很有潛質的文學新星。阿青在文中寫到,一個小女孩高考落榜後在家務農,她選擇了用文學創作來向命運抗爭的方式。她生活得很清苦,可是她卻很有信心。之後,我又陸陸續續發表過她的幾篇作品,並給她寫過一封信,寫了一些鼓勵的話,憒憾的是她沒有回信。
“你曾經還給我寫過一封信,現在這封信我還保存着。它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個燈塔,每當我痛苦和迷茫時我都要看這封信,每次看完信後我都充滿了與苦難抗爭的信心。”說完後,阿青從手提包裏拿出一封信,上面正是我的筆跡。她又說,“當時我已經出門打工去了,當我回來看到這封信時已經過了一年多了,之後我專程去縣報社拜訪你,然而,你不在。後來我又出門打工了。”
我忽然脫口而出:“你什麼時候和趙江混在一起的?”這句話說出口後我就後悔得直抓頭。
這句話引起了阿青痛苦的回憶。半晌,她幽幽地說:“一年前我的弟弟得了心臟病,如果不及時動手術,就有死亡的可能。動手術需要十幾萬,爲了挽救弟弟的生命,我主動找到趙江說願做他的情婦,就這麼簡單。”
“對不起,我讓你想起了痛苦的往事。”我訕訕地說。
“沒什麼,我當時給趙江說好了,在一年之內,我是她的情婦。昨天,正好一年到期了,我現在已經自由了。”
“噢,這是件好事!”
“可是我現在很迷茫,我不知道我今後做什麼?”阿青一臉痛苦地說。
“你可以重新拿起你的筆來創作呀,你的靈魂是清白的,我相信你一定會在文學上取得成功的。”
她冷冷一笑說:“多年來我一直有一個理想,就是攢一筆錢出版一本自己的文學作品集,現在我有錢了,可以輕易而舉地出版一本書了,可是我卻決定放棄了。”
“爲什麼?”我大惑不解。
“自從我看到你爲趙江寫的那本報告文學後,我的心就冷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一個我最尊敬的作家,卻寫下了如此不堪入目的文字。”阿青淡淡地說。
我就像高燒四十度的人一樣,臉發燙,腦袋裏一片亂響——前不久,我爲趙江寫的那本歌功頌德的報告文學出版了,趙江爽快地兌現了他的諾言:付給我了20萬元報酬。我記得,我接到20萬元的支票時,一直懷疑是在做夢。當我把錢從銀行裏取出來後,差點像范進中舉一樣發瘋呢。
“這封信現在我不想再保留了,還給你吧!”我就像夢遊者一樣迷迷糊糊地接過阿青遞過來的信。
在一片恍惚中,我又聽到阿青如刀子一樣冰冷而銳利的聲音:“其實,我們是同行,我出賣的是肉體,而你出賣的是文學和靈魂……”
(圖片來自於網絡)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