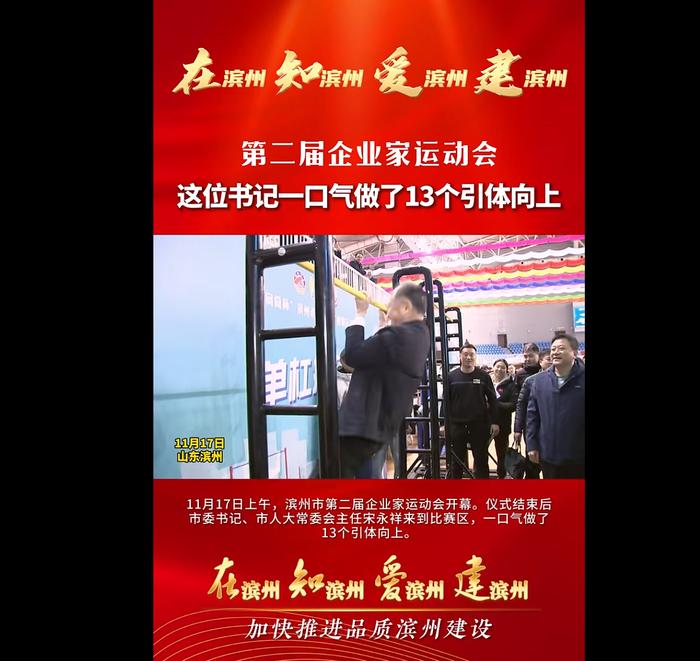大平原(二十五)|風自故鄉來
風自故鄉來
王冬良
年少時讀到唐朝詩人崔顥的詩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一直不解其意,怎奈時至今日遠在他鄉的我雖有些感觸,卻已是人近中年。
(一)咣咣花
早晨去體育公園跑步的時候,再次看到了路旁的那幾棵“咣咣花(學名蜀葵)”。這是老家最常見的“百姓花”,花朵豔麗、潑辣、好養活,種上一年後,每年春天都會長出很多。花朵有白的,有紅的,有粉色的,一叢叢咣咣花一起盛開時,也是相當有氣勢吸引眼球的。因爲樸實的鄉親們格外喜歡“紅花”,所以村裏的咣咣花也就以紅色爲主,很多人家的門口、小院花池裏都栽有紅色咣咣花。
不知道別人看到路邊這些咣咣花有何感想,但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讀小學時的那座老學校。老學校建於1984年,由老書記王相林帶領村民集資建成。學校教學樓由一座二層小樓和一排平房構成,小樓在北,平房在南。平房又分爲東西兩處,中間是一條南北馬路,西側教室是學前班(習慣稱之爲“育紅班”),東側平房是一年級教室。學前班前面的空地是操場,一年級教室前面是一塊菜地兼做花池,種的就是咣咣花和馬蓮花。每年六月,咣咣花就開始開花了,整個校園也就成了花的海洋。下課後,我們這些調皮的男孩子偷偷把花摘下來戴在頭上,在教室後面玩捉迷藏、老鷹抓小雞的遊戲,引得那些同齡的女孩子哈哈大笑。
我在這裏度過了寶貴的五年求學時光,從一個調皮的孩童,慢慢成爲了一個愛勞動、愛學習的好少年。雖然班裏只有17名學生,但我每年都會努力考取前兩名,這五年的求學時光培養了我的自信,讓我有勇氣去面對外邊和未來一切的挑戰。我堅信“天道酬勤”,只要自己不拋棄、不放棄,比別人多付出、多努力,遲早會有所成績!
(二)王家庵
2018年大年正月初六,全家人一起回濱州經濟開發區老家探親。中午在村西頭的姑姑家喫飯,飯後孩子吵鬧着非要出去玩一玩。姑父說,想去哪裏啊,我開車和你去。正在玩手機的我,忽然發現文友侯磊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條消息“王安村春節文藝節目匯演,威風鑼鼓敲起來,大秧歌扭起來”,下面是九張活動現場的照片。圖中有很多表演者都是我的長輩,表演的是“懶漢娶妻”“王小趕腳”等經典劇目。我對姑父說,要不咱仨都去老學校門口吧,那裏有“鬧玩”的。
我們到達現場後,演員們正在休息、換場,一個認識我的大媽告訴我接下來要表演“街舞”。我環目四周看到在廣場上看熱鬧的人羣中,有許多是看着我長大的老鄰居,他們也看到了我,一個個走過來和我說話,“什麼時候回來的,今下午走嗎”“你媽也跟着回來了?老小多大了?”……一句句久違的鄉音,喚起了我深藏的記憶,許多往事像電影鏡頭般在腦海裏呈現,好像我未曾離開村莊一般。
音樂響起,五個年輕人走上舞臺,伴着音樂的節奏,奮力表演着街舞。看年齡也就是十五六歲的年紀,標準的00後,我一個也不認識。於是低聲問姑父,他笑着一一給我介紹,左邊是大牛家的小子,右邊是柱子家的老大,那兩個戴帽子的是你文明叔家的歡歡、樂樂。小夥子的表演都不錯,舉手投足有板有眼,人也陽光、精神,他們就是村子的未來啊。我呢?多年不曾回家,漸漸成了村裏熟悉的陌生人。能喚出我乳名的老人越來越少,故鄉慢慢也就變幻成了一個符號。
因爲下午還要回鄒平,妻子發來短信要我們早些回去收拾行李。孩子依依不捨地跟我們上車,他忽然指着車窗外對我說:“爸爸,那紅色橫幅上的字有一個我不認識。”我問:“哪一個?你指給我看。”原來,他說就是那個‘庵’,我說那就是‘安’的簡化字啊!
回到鄒平,我的內心卻久久不能平靜。我所在的這個村子,被村裏人及附近村民喚作“王家庵”,我們身份證上寫的卻是“王安村”。與其他村莊不同的是,我們這個村子在2017年之前一直沒有村頭碑。小時候只知道玩,不曾關注這些。長大後參加了工作,也結識了一些文友,茶餘飯後就經常討論一些村子村名的由來。比如,我岳父家所在的鄒平縣孫鎮霍坡村,在村頭就有介紹村子由來的石碑。我工作的地方-西王集團所在的西王村甚至都出版了《西王村志》,建起了村史館。文化需要傳承,村子的歷史也需要儘快查清、梳理,讓更多的年輕人去了解村莊、熟知她的過去變遷、把一些精神傳承下去。特別是拜讀了李登建老師的《血脈之河的上游》後,這種查清村莊來歷的緊迫感越來越強,甚至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
《王氏家譜》是找不到了,問起一些祖父輩經歷過的陳年往事,父親回答的也是模棱兩可,我只好寄希望於查閱檔案館的《濱縣縣誌》。在一個溫暖的春日,我即興找了一個在開發區工作的教師朋友去檔案館,不巧的是被檔案館告知,需要所在工作單位開具介紹信才能查閱。查閱檔案碰到了障礙,我便改變思路在網上查閱,一遍遍的輸入相關關鍵詞進行百度搜索。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中國濱城區情網-數字方誌”查到了有關裏則鎮鎮名的一些資料:裏則鎮(li zei zheng),隋代立村,名黑風鎮,因鎮中關爺廟下有一距濱州城25裏之石標,曰:裏測鎮。後因測字有三水不吉,改稱裏則鎮。明代《濱州志》曰李則鎮,後仍名裏則鎮……
濱城區情網中也有部分村莊的具體介紹,唯獨沒有我們王安村的相關文字介紹。怎奈“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時候,無意中在《濱州文學》讀到了沙河辦事處王弘大姐寫的《濱州中游村傳奇》系列文章。看到文中的許多資料圖片,我頓時眼前一亮。我思索再三給王姐發了條微信。
一週後的一個晚上,我剛打開手機微信就看到了王弘姐發來的三張圖片,當時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動!我要找的就是這些!第一張圖片上拍的是書名《山東省濱縣地名志》,落款日期是1984年10月,離現在已經整整34年了!另兩張圖是關於“王家庵”村的詳細介紹:“王家庵,曾名:王庵、王安。位於新濱城西南37.5華里,區駐地西北5華里,西2華里界惠民縣。元末,王宗禮由惠民王判鎮遷此,因村東古有一庵,故名王家庵。訛爲王安。”
我立即把圖片發給同村幾個一起長大的發小,他們收到後也是驚喜不已,更沒想到我們的村子也有着600多年的歷史了。想想村子裏的那些老棗樹林子經過了多少風霜,想想村南的大水灣養育了多少代人,我們就能夠更好的理解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中描述的那些農村生活細節,表述的那種思念故土情懷!村子在,根就在!走得再遠,我們也是有家的人。想到這些,我們的內心便不再慌張,雙腳踏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說話做事纔會更加有底氣。
近些年,村裏一部分人靠着加工篩網、銷售篩網走上了致富路。還有許多年輕人和我一樣,從學校畢業後走進了車間工廠,在新的舞臺上奮力打拼。村子裏的二層小樓、家庭汽車越來越多,再加上國家取消了農業稅,莊稼風調雨順,鄉親們也過上了期盼許久的好日子。去年冬天,村裏家家戶戶通上了天然氣(享受政府補貼),即可取暖也可做飯,街道變得更加整潔,村莊舊貌換了新顏!一個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新農村正在慢慢形成。
(三)在韓店
2003年5月的一天,18歲的我揹着簡單的行囊來到鄒平西王集團參加工作。在企業裏,領導同事百般愛護,工作中遇到困難,他們都會熱心幫助;上班有着免費的工作餐,頓頓熱湯熱水讓我們這些遊子慢慢有了家的感覺。我從一名普通的車間操作工,一步步成長爲一名基層管理幹部。
今天我已成爲兩個孩子的父親,夫妻雙雙在西王工作,在這裏買了房,買了車,孩子也在這裏生活、上學,這裏已成爲了我的新家。每逢節假日,我們都會開着車,領着孩子去附近的伏生公園、禾和溼地去逛逛。曾有鄰居打趣的問過孩子,你家是哪裏啊?兒子則高興地回答道:“媽媽說我有兩個家,老家在濱城,新家在韓店。”是啊,我好幸福,我有了兩個家,一個在黃河北,一個在黃河南。我有着雙份的愛,愛與被愛充斥着我的生活。
春天的風總是柔柔的、暖暖的,吹遍大江南北。鄒平櫻花盛開的季節,濱城老家的海棠也在同時綻放。我衷心祝福兩地的父老鄉親在黨的好政策下,通過自己的勤勞、奮鬥,過上更加美滿幸福的新生活。
作者簡介:王冬良,山東濱州人,供職於西王糖業有限公司,系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濱州市作協會員。熱愛文學,喜愛讀書,作品以鄉土散文爲主,有文章散見於在《齊魯文學》《鄒平羣文》《梁鄒文化》等刊物以及齊魯網《西王文苑》《濱州文學》等文學公衆號平臺。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