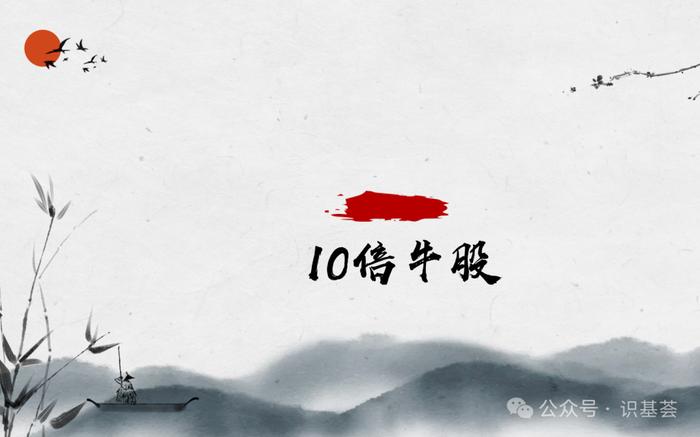泉港事故追蹤:千億石化產業何去何從
(原標題:【泉港事故追蹤】千億石化產業何去何從)
泉港的石化產業發展不會因此次碳九泄露事故而終止,但事故暴露出的安全隱患、監管不力、社會信任、拆遷矛盾等問題必須加以解決
《財經》記者 韓舒淋/文 馬克/編輯
11月25日,在泉港碳九泄漏事故發生20天后,泉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了碳九泄漏事故調查及處置情況。事故企業東港石化存在瞞報,實際泄漏69.1噸,是最初公佈泄漏量6.97噸的近10倍,事故系主要企業生產管理責任不落實引發,也有地方政府部門履職不到位的問題。
對於事故的影響,調查組定性爲:由於突發短期接觸,此次裂解碳九泄漏對周邊居民區影響有限。監測結果顯示,事發地的環境空氣質量迅速恢復正常,目前肖厝海域水質已恢復至第一(二)類海水水質,符合養殖區域海水水質標準。
在追責方面,生產企業東港石化和接收碳九的“天桐一號”郵輪公司被定義爲主要責任,兩家公司共10人被採取強制措施,其中7人已被批捕。而在屬地和監管責任方面,泉港區政府、區交通局、區安監局及湄洲灣港口管理局有關官員均受到不同程度處罰,並接受進一步調查。
至此,其主要事故原因、影響及主要責任人的追責初步告一段落。此次事故本身,影響相對有限,然而對於化工產值佔到工業總產值一半以上的泉港區而言,此次事故本身及處置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對於當地繼續發展化工產業,提出了諸多警告。
環境影響基本平息的情況下,靠海喫海的當地居民最擔心的是海鮮生意什麼時候能夠恢復。有泉港當地居民11月28日向《財經》記者發來的視頻顯示,當天有當地村鎮官員公開試喫海鮮,試圖打消漁民對海產品的疑慮,恢復本地海產品市場,然而這一舉動並未贏得信任,反而被許多漁民質疑海鮮是從外地運來,並非本地打撈。亦有事故附近肖厝村的村民在11月30日告訴《財經》記者,目前當地海鮮市場依然沒有恢復,有出售的海鮮都是外地運來。
“指標可以恢復,但人心難恢復”,一位當地居民在事故調查結果出來之後對《財經》記者如此感嘆。《財經》記者在當地採訪發現,圍繞環境影響、化工產業拆遷徵地、事故信息披露等多方面,當地居民對政府依然存在不信任感。泉港區有多年煉化產業發展的基礎,也具備繼續壯大的條件,然而如果不處理好與本地居民的關係,這將對其化工產業的未來發展蒙上陰影。
對泉港政府和相關化工企業而言,此次碳九泄漏事故,是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預警。
石化產業撐起泉港
對泉港區的地方經濟而言,石化產業是絕對支柱。
從離泉港區最近的仙遊高鐵站驅車前往泉港城區,沿路可以看見“海西綠色石化城歡迎您”的醒目招牌。當地最大的煉化企業是福建聯合石化,其規模龐大的廠區及廠區內高聳的煉化設施,很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泉港區政府對《財經》記者介紹說,2017年泉港石化工業總產值815.26億元,佔全區工業總產值的56.3%。目前入駐石化園區企業37家,已投產石化企業18家,其中化學生產企業14家,石化倉儲企業4家,在建項目7個,在辦前期手續項目12個,2018年1-9月石化產值811億元。
超過800億元的石化產業產值規模,在全國範圍內都位居前列。其中,最核心的企業莫過於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福建聯合石化。
上世紀80年代,中石化與福建省石油化學工業公司以50:50的比例合資成立福建煉油化工有限公司,1993年全面建成投產。2007年,該公司與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聯合成立合資公司,三方持股分別爲50%、25%、25%。如今,福建聯合石化的煉油能力達到1200萬噸/年。而截止2016年底,我國千萬噸級以上的煉廠一共只有24座,且主要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這兩大央企。
福建聯合石化官網資料顯示,它每年向國內市場提供700多萬噸高品質煉油產品、160多萬噸聚烯烴塑料、180多萬噸化纖、橡膠、聚酯及其它化工生產所需的基礎化工原料。一位化工領域相關專家告訴《財經》記者,國內大型煉化廠一般都是燃料型煉廠,生產交通、工業用燃料,然後會逐步擴張到生產化工產品,主要以乙烯爲主,也包括其他化工產品。但大的煉化一體企業並不會包攬所有化工產品的生產,許多細分的塑料、化纖原料產品往往由產業鏈的其他中小公司生產,大的煉化企業的化工產品會是這些中小公司生產的原料。
也因此,在有了福建聯合石化這一家大型煉化廠之後,泉港當地圍繞該廠,逐步發展起來了數十家煉化企業,並逐漸成爲佔當地工業生產總值一半以上的絕對支柱產業。當地官員介紹,因爲有聯合石化,纔有其他下游企業進來。產業鏈延伸的越長,效益纔會越體現。
此次事故方的東港石化,由福建德和集團100%控股,工商信息顯示,其經營範圍包括3萬噸級、2000噸級液體化工公用碼頭及配套倉儲設施、經營;煤油(包括三號噴氣燃料)、汽油、柴油批發業務。此次事故發生地,即在東港石化所屬的2000噸級碼頭上。
東港石化是當地的民營企業。法人代表爲黃天仁,據當地政府通告,事故後已經被批捕。福建德和集團法人代表爲林森,他同時也是德和集團持股85%的第一大個人股東。工商信息顯示,德和集團除了100%控股東港石化之外,還全資控股了另外3家公司,其中包括控股福建德和房地產開放公司,開展房地產開發業務。
對泉港區而言,由於石化產業的發展,還帶動了原油及相關煉化產品進出口,使得當地關稅成爲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位當地政府官員11月9日對《財經》記者介紹,泉港一年上繳中央的國稅與關稅共計大約250億元,其中關稅超過160億元,佔泉州市關稅的90%以上,主要都是由於石化產業的發展帶來。
政策層面,國家與地方也將泉港定義爲石化產業基地。2009年,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提出,以廈門灣、湄洲灣爲依託,建設以石化、船舶修造等爲重點的臨港工業集中區。規劃中的湄洲灣,就是泉港所在地區。2011年,國家發改委《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要求培育壯大湄洲灣集中發展區,推動石化產業聚集發展,建設臨港重化工業基地、能源基地。地方層面,泉州市2010年曾發文明確將泉港區的城市性質定爲:以石化工業爲主導的現代化港口新城。
廠居混雜難題
超過30年石化產業的發展,圍繞核心煉化廠建立起來的成熟產業鏈,讓石化產業成爲泉港區地方經濟發展的絕對支柱。但也正因爲石化產業起步較早,當地長期存在遺留下來的廠居混雜問題,並隨着規模不斷擴大,地方經濟不斷發展,廠居混雜越來越密集,安全隱患突出。
“泉港是先有廠,再有園區規劃,(規劃)相對滯後”,一位當地政府官員在11月9日對《財經》記者介紹拆遷計劃時坦言。據他介紹,1988年福建煉油廠先啓動,徵用了一些地,當時就存在廠居混雜的矛盾,2003年有過一次大的拆遷,最近幾年矛盾越來越突出。
和所有大型項目一樣,拆遷是一個難以讓各方滿意的爭議難題。多位當地受訪的村民都對《財經》記者表示了對拆遷計劃的不理解和補償方案的不滿意。
2015年漳州古雷和天津先後發生危險化學品爆炸事故,其後,地方政府開始逐步推動解決廠居混雜的問題。2015年12月,泉港區人大批准當地五年規劃發展綱要,其中提出逐年實施環石化園區1000米範圍內衛生安全防護隔離帶村莊的搬遷。
其後,經由相關設計院規劃,泉港區政府確定了在石化園區周邊550米範圍爲安全控制區(下稱安控區),計劃從2016年至2020年完成安控區內的拆遷。爲此,泉港區政府成立了安控區安徵遷指揮部綜合辦公室,來專門推進此項工作。而確定拆遷範圍基礎的石化園區,則是依據2012年福建省政府批覆省發改委保送的《福建省湄洲灣石化基地發展規劃(2011-2020)》,其規劃面積29.6平方公里,包括泉港區界山鎮、南浦鎮的部分區域,其後又加入了界山鎮東涼村。
需要指出的是,根據《財經》記者在安徵區拆遷辦看到的安控區拆遷規劃圖,規劃的石化園區遠大於目前泉港現有石化企業所佔據的區域。除福建聯合石化的全部廠區在規劃區內,石化園區範圍還也包括部分城區居民區及多個鄉村。如果加上550米範圍的安控區,涉及面積更大。整個區域被劃分爲7個片區,據當地官員介紹,石化園區面積爲29.6平方公里,周邊550米的安控區面積約爲11平方公里,其中的居民區都需要進行拆遷。
《財經》記者在11月9日獲得的一份安控區徵地拆遷工作進度表顯示,七大片區拆遷面積共計553.7萬平方米,涉及5萬2千餘人,建築1萬3千餘棟。截止11月8日,拆遷協議簽訂情況完成65.8%。
根據規劃,此次發生事故的東港石化碼頭未在石化園區內,但處在安控區範圍。因海水受污染而遭受最直接漁業損失的肖厝村,其村西小部分區域位於安控區內,需要拆遷,大部分居民則依然位於安控區之外。
拆遷矛盾重重
這份石化園區及周邊安控區的拆遷規劃,對被拆遷區域內村民和居民的生活將帶來巨大影響,因而爭議不斷。
在拆遷範圍上,有泉港區界山鎮東涼村村民對《財經》記者抱怨,東涼村距離現有的石化工廠有3至5公里之遙,且其中相隔下朱山、下朱尾山兩座大山,可以阻隔污染空氣,然而依然被列入拆遷範圍之內,認爲拆遷是“官商勾結”,目的是掠地。
《財經》記者根據拆遷規劃圖發現,東涼村的確距離東港石化直線距離較遠,周邊目前也沒有投產的石化企業,但是根據當地規劃,它全村都被劃入了石化園區的第二片區,且村子依靠的海岸也被一併劃入,因此面臨拆遷。顯然,村民對規劃的瞭解與政府的規劃之間有明顯偏差,但是其質疑也並非事出無因。
另一大爭議是拆遷補償標準,2017年6月泉港區人民政府發佈了安控區徵遷的補償方案,補償方案頗爲複雜。簡單來說,被拆遷戶可以根據原有房屋的面積獲得貨幣補償和房票補償兩部分,在符合各種條件下最高可以在區內獲得約4000元/平米的購房補助,且購房面積根據原來住房面積和人口數有頗爲複雜的限制,而泉港區目前房價一般在6000元左右。此外,根據簽訂協議的時段不同,越往後,補償標準越低。
這些限制意味着,當地大部分被拆遷的居民要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還要爲此賠上一筆錢。有村民表示,並不反對國家的建設,但是至少希望拆遷前後,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會受到影響。也有村民擔憂,歷來靠海喫海,以後搬到泉港區的城區之後,不知道該如何生活。也有受訪的村中老人多年在外闖蕩,積累了一些財富老來回故鄉養老,並重建了村中的祠堂,如今,這座剛建成三年的祠堂和他的房子一起,都將面臨被拆遷的命運。
而更令當地人不解的是,此前拆遷的地尚未妥善利用,如今又有新的拆遷計劃,這讓居民難以接受。
有東涼村村民反映,石化園區內原南山片區有數千畝的土地,閒置了十多年都沒有業主;2011年拆遷的侖頭村、北網村的土地至今也依然閒置。
地方政府官員也側面印證了這一現象。當地安徵遷指揮部有關官員表示,安控區拆遷需要耗資大約300億元,如果能夠全部落實招商引資,能夠給地方政府帶來可觀的財政收入,但能否全部落實,現在還沒有底;石化園區內現在也有大片土地還閒置,這幾年真正招商引資的也沒有三五家,大部分地還空着,整個市場情況都很差。
對於原有用地還閒置,爲何又啓動新的拆遷,該官員表示,這是爲了從根本上解決廠居混雜的矛盾,是“政治任務”。
如今碳九事故本身的環境影響影響逐漸平息,但其社會影響將難以在短期內癒合。過往的拆遷、環境等矛盾,經過此次泉港碳九事故中先後出現的泄漏數據瞞報、信息披露不及時、記者被當地警方騷擾以及漁民漁業損失等問題的發酵,讓當地居民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繼續累積。
泉港當地是否會因此而中止化工產業?答案是否定的。有石化產業相關專家對《財經》記者表示,當地的石化發展或許短暫會受到影響,但長期來看還是會繼續,一方面全國範圍來看,符合條件的石化基地並不多,另一方面,泉港本地已有多年的石化產業歷史,有相對成熟的產業鏈,如果要搬離,成本巨大。該專家同時表示,地方政府的監管部門在面臨此類有重大環境風險的大型項目時,的確可能存在專業和能力的短板,這既需要企業自身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也需要地方監管部門不斷提高監管能力,這需要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