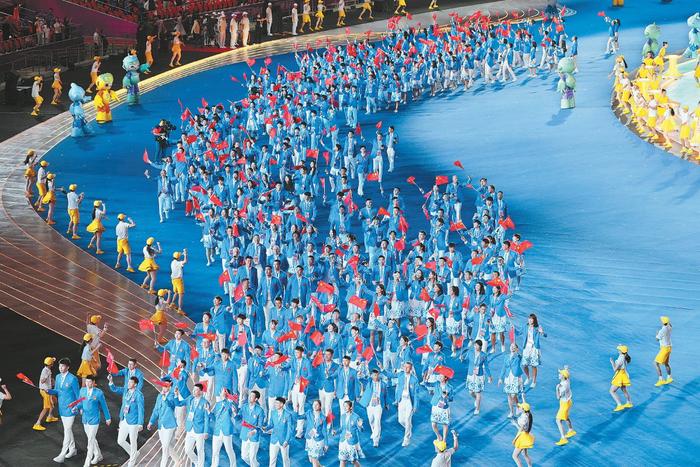真棒!北京西邊還藏着一條這麼美的千年古道!
京都猶來物產豐,西隔崇山路難通。古時商行駝騾載,道是辛苦樂其中。門頭溝區水峪嘴村地處千年京西古道要塞處,素有“京西古道第一村”的美譽。
8月11日,《北京青年報》聯合《法制晚報》,組織文字記者、攝影記者、航拍記者、視頻拍攝記者、繪畫師,並邀請了“讀者尋訪團”,一起走進水峪嘴兒,重訪京西古道,直觀感受歷史留在這裏的文化沉積。
儘管遭遇了酷暑、遭遇了暴雨、遭遇了山路崎嶇,但“北青”的讀者們紛紛表示,此次文化尋訪的收穫非常飽滿。
16年前,“京西古道”走向世界
“京西古道第一次在門頭溝區外的媒體見報就是在北青報,那時通過媒體的報道,才讓京西古道真正走出了門頭溝,走出了北京。”在水峪嘴村村委會的會議室裏,京西古道研究專家安全山向大家訴說了這段往事,手裏拿的就是一份珍藏了16年的《北京青年報》。
舊報紙已經泛黃,卻保存得十分完好,版頭印着定格的時間——“2002年10月8日”。這一天,在《北京青年報》副刊版的“一個人與一座城市”欄目上,發表了安全山書寫的《我與京西古道》一文。

安全山手裏拿着珍藏16年的報紙
“史書上其實並沒有這條古道的名字,但是我認爲這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它的文化和內涵。”安全山告訴大家,京西古道起源比較早,並不是由於某一個歷史時期或事件引出來的。而是伴隨着北方永定河流域的古人類遷移活動而產生的。
他認爲,京西古道從歷史時間長度看不輸於世界上任何一條古道,甚至可以說是最長的。從泥河灣、周口店等地古人類遷移開始,就貫穿了漫長曆史階段的全過程。“古道本身就是線性文化,可以跨地區、跨區域甚至跨國境,它的傳播意義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是文化的傳遞和延伸。”
安全山老爺子是京西古道邊上土生土長的門頭溝人。“我出生在安家灘村,就在幾條古道的交匯地王平口附近,從小就在古道上玩耍。門頭溝出煤,我們村曾因以煤矸石爲原料燒製砂鍋出名,其他地方的砂鍋大都以黏土爲原料,而安家灘村的砂鍋用的是煤窯裏的黑石軟矸,是對煤的下腳料的再利用。燒製砂鍋時,燃料是煤,砂鍋坯子也在燃燒,燒出的砂鍋金屬性能強,硬度大,敲着響。‘打破砂鍋問到底’大概說的就是我們村燒製的這種鍋,它可以百年不壞。”
半個多世紀前,安全山還是個孩子,爲補貼家用,他經常揹着自家燒製的砂鍋,去附近的村子裏賣。那時他走着去其他村賣砂鍋的路,便是這條京西古道。
在安全山眼裏,京西古道從來就不是一條簡簡單單的古代石頭通道,它記錄了永定河流域一個個鮮活生命的生活痕跡。

航拍京西古道
這是北京一座巨大的文化寶庫
京西古道,是北京以西、永定河中上游流域地區自有人類活動以來所形成的古老道路的統稱,最遠可以追溯到遠古先民遷徙時踏闢出來的山間道路和永定河廊道,到元代後,陸續形成了縱橫交錯的古道路網。
門頭溝擁有的這條千年歷史古道,全長100多公里。在沒有火車的年代,在公路貫通羣山之前,這條路就是古代的“109國道”。
山裏的煤、山外的糧、建城裏需要的木材等,全部通過這條古道,用騾馬馱運進京。古道兩旁保存着大量古蹟、碑刻、關城遺址,是京西古代文明的重要標誌和歷史見證。
安全山說,京西古道有商道、軍道和香道之分,因爲常年有馬幫馱隊運煤等物資進京,就在京西羣山之間逐漸形成了一條古商道。另外,京西寺廟衆多,又有古香道。爲防衛京畿,還開闢有古軍道。
由於近代汽車、火車等逐漸發達,這些遠古而成的道路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古道成爲“看得見,走得了”的歷史遺存。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第一條鐵路修到了門頭溝,京西古道由此沉睡了。”安全山說,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開始挖掘文化,又關注到了京西古道,特別是2002年開始,京西古道作爲文化遺存和戶外步道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中。
這星羅棋佈的古道網,在安全山眼裏是巨大的財富。“門頭溝十個鎮,鎮鎮都有京西古道的遺蹟,走到哪都有,都可以見到,都可以走,分得也比較清楚。商旅道有商旅道的模樣,進香道也是。”
近百年來,古道雖已廢棄殘敗,但有些路段仍古韻猶在。2012年,京西古道被評爲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100 項重大新發現”之首,同時也是中國的十大古道之一。
“我不是專家,只是愛家”
在安全山的家中,到處都擺放着與京西古道有關的各種圖書資料和他手寫的文稿。他利用自己多年行走古道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參與編寫了《京西古道旅遊指南》《北京門頭溝京西古道市民徒步指導手冊》《京西古道徒步路線圖冊》,如今許多驢友都還是用安老爺子編寫的版本圖來這裏徒步。
“這山道對我來說就是平的。”安全山今年60多歲了,兩年前因爲喉癌動了次大手術,說話聲音嘶啞,京西古道上的溝溝壑壑,似乎都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腦子裏。
儘管身體狀況不如十幾年前,但走起這京西古道來他還是十分輕巧。2012年,已經60多歲的安全山接到任務,作爲地方專家組的重要成員,他需要親身參與門頭溝區國家步道的規劃工作。他帶着規劃公司的專家團隊去古道上勘查,一年中在古道上走了足足680公里。他對古道的熟悉程度,讓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們都不停稱讚。

京西古道
“國家步道在美國、英國等都很成熟了,在我們國家還是新生事物,我就負責帶路。有美國、臺灣地區的研究人員過來,有研究定位的,有研究歷史文化的,有研究地質的,也有研究生物的,我就邊走邊講,這些我都能講。只有帶着客人邊走邊講,見什麼講什麼,才能讓客人有興趣。”
現在,看着京西古道發展得越來越好,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這裏並來遊玩,他覺得無比欣慰。每每有人稱呼他爲京西古道研究專家時,他總會笑笑說:“我不是專家,我只是愛家。”
尋訪京西古道
牛角嶺關城門洞
牛角嶺關城作爲京西軍事要塞,自古以來馬幫馱隊絡繹不絕,軍事通行,商旅來往,民衆進香,都要從中通過。
如今,關城雖已殘敗,門券卻仍舊聳立在山脊之上,站在道路中央的石板上,可以想象古道昔日的繁忙。門券是個拱形的門洞,洞口雖然顯得有些破敗,但仍然十分有看頭。

牛角領關城
門券高6.2米,寬4.3米,深9.3米,在山石上直接用石塊壘砌,青磚券邊,青石做腿。關城口涵洞依山勢而建,關城門券內側的兩邊都有差不多三四個方形的洞口。這是建造關城時留下的活口,建完後也可以緩衝大雨沖刷的壓力,兩側背靠山坡的涵洞很容易被衝倒,但是這裏的涵洞不會。
蹄窩
過了關城涵洞口,視線寬闊了起來,石頭路上的蹄窩也多了起來。蹄窩最集中的就在關城城券下面的一段。據說,這牛角嶺關城山頂是一整塊巨石,這一段古道就是在這塊巨石上鑿出來的,路面凹凸不平,幾百年的踏磨讓石頭的天然紋理更加光滑清晰,與光滑石頭上大大小小的蹄窩交織在一起,像是在訴說着千年的滄桑。

一連串蹄窩
這段古道不短,路隨山勢上上下下。走在這種路上,腳下十分不舒服,深深的蹄窩讓人走起來一腳深一腳淺,一不留神就有崴到腳的風險,也有可能因爲石頭太光滑而摔上一跤。
永遠免夫亭
“我到現在還記得那是個正月初五,天氣特別冷。我帶着我女婿來這邊找這塊免夫碑。我們用手把碑上的積雪扒拉掉,再手抄碑文上的字記錄下來,手都凍麻了。”安全山說。
他所說的免夫碑就在關城。據記載,這塊“永遠免夫交界碑”立於大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碑文記述了自古以來,京西鄉村“石厚田薄,里人走窯度日。一應夫差,家中每嘆餬口之艱。距京遙遠,往返不堪征途之苦”。

免夫碑
雍正八年(1730年),王平口巡檢司官員阮公將鄉民疾苦呈報縣官,縣官上奏朝廷允准免除這裏的伕役,得到皇上恩准。王平、齊家、石港三司伕役全部豁免。這塊碑所在的地方就是分界線,石碑以西的人們從此不用去城裏服役做苦力了。
古石道
由於古道少有人走,石縫間長滿青草,青草包裹着一個個歲月踏過而變得光滑的石頭。
京西古道曾經是一條有兩米多寬的官山大道,全部用石塊鋪砌而成。因山路陡峭每隔一米就會栽立石一排,以防止石塊鬆動下滑,這也是古道經久堅固的訣竅所在。雨後這一排排立石更是起了大作用,讓深一腳、淺一腳的尋訪團團員有了可以下腳、絕對不會打滑的地方。

古石道
古往今來,
歲月也許給了它滄桑與磨礪,
但古道其實從未曾消失,
它正以另外一種形式,
越發鮮活起來。
文北青報記者 雷若彤
攝影|劉暢 楊小嘉 薛冰
視頻剪輯|郭茂勇 高曌
編輯|王子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