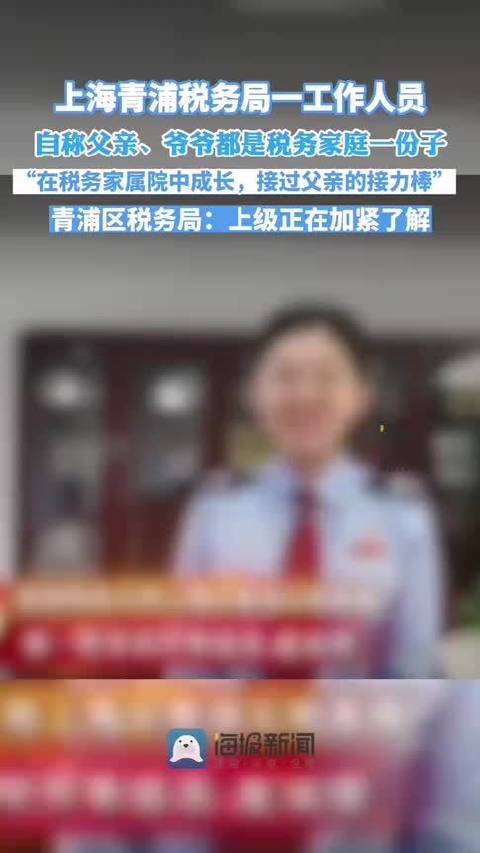阿拉伯帝國何以迅速征服廣闊的土地?
阿拉伯帝國的征服對人類歷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和成吉思汗西征相比,阿拉伯帝國的大征服直接對被征服的地區的語言和宗教產生了永久性影響。在這場大征服中,除了伊比利亞半島扭轉了伊斯蘭教的傳播趨勢,其他地區都成爲了伊斯蘭教的基本盤,也使得伊斯蘭教成爲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這場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征服,直接塑造了我們今天生活於其中的世界。
面對強敵拜占庭帝國和薩珊波斯帝國,阿拉伯人到底爲什麼能夠如此迅速地征服廣闊的土地?爲什麼這場征服的影響如此持久深遠?如今的中東亂局以及恐怖主義,使得人們很容易將伊斯蘭教與一些負面刻板印象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與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不一樣的是,在阿拉伯帝國早期“一手拿劍,一手拿經”進行征服的時候,阿拉伯人對待異文化的態度是相對寬厚的,他們並沒有強迫其他居民改宗伊斯蘭教,也很少屠殺平民、毀壞城市村莊或強徵財產。
因此,被征服地區的伊斯蘭化與阿拉伯化進程,要在征服結束後的兩到三個世紀之後纔出現。而且,這種轉化並不是征服直接導致的結果,而是越來越多被征服的居民自覺自願地認同和參與當時的主導文化,幾乎以完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伊斯蘭化。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以下摘選自英國中東史專家休·肯尼迪的《大征服:阿拉伯帝國的崛起》,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大征服:阿拉伯帝國的崛起》,[英]休·肯尼迪著,孫宇譯,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年3月版
現在,讓我們回頭再看看本書開頭約翰·巴爾·彭卡耶提出的那個問題:爲什麼阿拉伯人能夠如此迅速地征服如此廣闊的土地?爲什麼這場征服的影響如此持久深遠?
首先讓我們來討論他們征服的土地,究竟是什麼讓這些地區如此不堪一擊?一些難以詳述或量化的長期性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人口衰退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誠然,關於這段時期我們並沒有多少可靠的人口數據,但根據大部分文獻資料的描述,在540年地中海鼠疫爆發後的一個世紀中,就在穆斯林日後征服的大片土地上,人口都嚴重衰減,其中城市和鄉村的人口損失尤爲慘重。阿拉伯軍似乎時常途經荒無人煙的土地。他們對伊朗和伊比利亞半島廣大地區的征服來勢兇猛卻抵抗甚微,可以證明當時的人口衰減。戰爭中劫掠的戰利品,有許多都是戰俘奴隸,也表明當時人力的寶貴。波斯軍於540年攻佔安條克和573年攻佔阿帕梅亞時,他們將大量居民遷往薩珊帝國境內建立新的聚落或充實已有城鎮,這證明當時的薩珊帝國境內出現了嚴重的人口短缺。從北非捕獲的大量奴隸被販運至中東地區,說明人力成了某種貴重甚至稀缺的資源。
還有許多著名的古老城鎮顯然未曾奮力抵抗就被攻克,晚期羅馬帝國的三座重要城市無疑經歷了這樣的命運。大概在636年,安條克僅經歷了輕微抵抗便被佔領;698年,穆斯林軍最終佔領迦太基城時,這座城市似乎大部分已經荒廢無人了;712年,憑據天險的西哥特王國首都託雷多也沒能拖住穆斯林軍的腳步。因此,儘管有關人口衰退的歷史證據十分分散,且大多並非直接史料,但人口衰減顯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固然人口衰退並非阿拉伯大征服的起因,但它很可能削弱了抵抗的烈度,因此阿拉伯軍纔不會被有大量人口定居、駐防嚴密且居民鬥志昂然的城市所阻礙。當時可能只有在河中地區,本地居民纔會憑藉高昂的士氣積極抵抗敵人。
除以上長期性因素之外,戰爭還帶來了一些短期影響,並進而引發了動亂的局面。自克拉蘇於公元前53年率軍進攻帕提亞帝國慘遭失敗開始,羅馬帝國與伊朗帝國之間就紛爭頻傳,而602年莫里斯皇帝遇刺後爆發的那場戰爭是其中波及地域最爲廣大、損失最爲慘重的戰爭。波斯軍橫掃拜占庭帝國領土,在許多層面上對當地社會造成了深刻影響。波斯軍摧毀了拜占庭帝國對近東地區的統治,斷絕了當地與君士坦丁堡的聯繫。拜占庭帝國從此以後不再爲這些地區任命總督、指派軍隊,賦稅也無法從這些地區收齊。迦克頓正統教會失去了帝國權威的扶持,淪爲了衆多基督教支派中的一支。
早期阿拉伯大征服的示意圖
許多教士和其他精英人士都逃去了相對安全的北非和意大利地區。考古證據表明,至少在安納托利亞地區,波斯軍在進軍途中對當地的城鎮造成了巨大破壞,當地居民被迫廢棄了平原上的大型城鎮,轉而逃往山間堡壘避難。2到阿拉伯軍從麥地那開拔時,拜占庭帝國纔剛剛收復失地不過一兩年,可以說拜占庭帝國在許多地區完全沒有建立起軍事和政治秩序。
這場“古典時代的末日決戰”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在這場戰爭中,兩大帝國以同樣殘酷野蠻的手段,耗盡了彼此的國力。與波斯軍入侵拜占庭帝國相比,希拉剋略對波斯帝國的入侵同樣造成了慘重破壞。他摧毀了席茲的大火廟,歷代薩珊皇帝都曾在這座火廟中舉行加冕儀式,位於達斯特格爾德的皇宮也被他劫掠一空。更致命的是,著名的波斯皇帝霍斯勞二世(591年至628年在位)也被自己手下的將領殺死。與拜占庭帝國不同,薩珊波斯帝國是一個典型的王朝國家。希拉剋略的進攻挫敗了薩珊皇族威望,動搖了波斯統治者的信心。皇族成員的內鬥使得薩珊帝國長期國勢不穩。到伊嗣俟三世(632年至651年在位)被各方擁立爲皇帝時,阿拉伯軍已經敲開了伊拉克邊境的大門。
641年2月希拉剋略去世後,皇子的繼位紛爭讓拜占庭帝國的統治陷入了癱瘓,這場事件也爲阿拉伯征服的成功提供了條件。似乎正是由於當時帝國宮廷內的權力紛爭,拜占庭軍纔沒能有效支援埃及的防禦。假設希拉剋略去世後繼位的是一位強勢有爲的皇帝,拜占庭帝國很可能會在敘利亞或地中海沿岸地區發起反擊,在656年奧斯曼哈里發遇刺後的混亂時期尤其可能得手。然而由於拜占庭帝國的內亂,穆斯林贏得了一代人的時間來鞏固他們從拜占庭帝國奪取的國土。
拜占庭帝國與薩珊帝國都擁有一個同樣的優勢,然而事與願違的是,當國家走向衰落時,這一優勢反而變成了弱點。拜占庭帝國和薩珊帝國的軍權高度集中,兩大帝國都依賴於由稅收財政維持的職業軍隊。拜占庭帝國曾擁有一支“邊防軍”(limitanei),這些軍隊戍守在國家邊疆,國家發放土地與薪金來供養他們防守帝國邊境。六世紀前半葉,帝國解散了這些軍隊,取而代之的則是拜占庭帝國的遊牧盟友加薩尼王朝。582年拜占庭帝國與加薩尼王朝決裂之後,帝國依靠常備野戰軍來防衛邊境。當時拜占庭帝國對沙漠方向的襲擊似乎毫無防備。七世紀的軍事操典《軍略》中記載了波斯人、突厥人和阿瓦爾人的戰術,但從未提及阿拉伯人。除去當地阿拉伯盟軍之外,似乎抵抗穆斯林軍入侵的拜占庭軍隊中並沒有多少當地人。這些官兵要麼是來自帝國其他地區的希臘人,要麼是亞美尼亞人。
在薩珊帝國,軍隊的演變也與之相似。六世紀前半葉,霍斯勞一世(531年至579年在位)大大加強了帝國的中央行政權力,建立了一支由稅收財政供養的帝國常備軍。與同時代的拜占庭帝國一樣,薩珊帝國也不再依靠盟友拉赫姆王朝協助防守邊境。波斯皇帝的直屬軍隊擔起了守衛國家的重任。
從許多方面來看,這些發展可以說是中央權力集中和政府機構成熟的標誌,然而矛盾的是,這卻讓這兩個強大的帝國變得出奇脆弱。假如帝國政府陷入混亂,或者假如帝國軍隊在某場大戰中遭受重創,那麼地方上就難以抽出可用之兵組織防禦。因爲國家既沒有市民組成的城鎮軍隊,也沒有可以徵集的農村民兵。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軍所遭遇的持續最久的抵抗來自河中、亞美尼亞、厄爾布爾士山區以及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亞山區等地,這些地區始終位於帝國和平原王國的直接統治範圍之外。只有在這裏,本地居民纔會積極保衛家園,抗擊侵略者。
有記載表明,在穆斯林征服的許多地區,入侵者都因這些古老帝國的內部矛盾而坐得漁翁之利,也就是說,某些時候他們被當地人看作是解放者,或者至少是可以忍受的統治者。其中有的是宗教矛盾:比如埃及和敘利亞北部的一性論派基督徒顯然不可能擁護拜占庭帝國,儘管也罕有證據證明他們曾確實協助過入侵者。伊拉克薩瓦德地區的農民很可能因波斯統治階層的崩潰而感到如釋重負;信德地區的商人和手工業者據說曾自願協助穆斯林打擊信仰婆羅門教的軍事貴族。在北非,柏柏爾人時而抗擊侵略,時而與穆斯林聯合,時而臣服於他們,唯獨將拜占庭人甩在一邊,任其自生自滅。
在第一次征服後,被征服的羣體並沒有在文化上自覺反抗外來侵略。他們對於實行苛政,執法不公的總督頗有怨言,但就我們所見,並沒有傳道士或作者呼籲人們挺身而出積極反抗新的統治者。基督教文獻中的反穆斯林宣傳都是以末日文學的形式呈現,預言了未來會有一位偉大的皇帝或英雄人物自外界降臨,解放基督徒。而與此同時,基督徒所要做的只有堅持祈禱和堅定信仰。與其敵視阿拉伯人,基督教不同派別之間彼此的敵意更加強烈,猶太人更是基督徒最爲仇視的對象。在被征服者中,並沒有人呼籲大家推翻新統治者。
拜占庭帝國與薩珊帝國境內存在的以上內部矛盾爲阿拉伯大征服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假設穆罕默德早一代人時間出生,並且與其繼承者在600年出兵進攻這兩大帝國,那麼很難想象他們會取得任何成果。
阿拉伯軍隊之所以能取得勝利,也不僅僅是利用了既有國家的政治制度缺陷。當時的穆斯林軍本身就擁有十分強勁的實力,因此他們比此前和之後出現的任何一支貝都因武裝都更加強大有力。
關於侵略軍的宗教熱情和殉道與天園的觀念對於戰鬥的激勵作用,我們在前文中已經談到很多。這些觀念與前伊斯蘭時代傳統的部族忠誠感,以及個人英雄主義激情相互聯繫,彼此結合。遊牧社會的文化價值觀與新興宗教觀念相互混合,爆發出了強勁的威力。
我們必須指出,參與早期伊斯蘭征服的是一支真正的軍隊,而並不是大批遊牧部族組成的移民潮。他們將家中女眷、牲畜、孩童和老人留在了後方的帳篷或房屋中。士兵則編製成隊,指揮官則由上級任命,指揮官的選任往往經過了哈里發或總督們的會議討論。只有在戰鬥勝利之後,軍人家屬才能與士兵團聚。
如我們所見,阿拉伯軍並非擁有他們的敵人所沒有的先進技術,也並非以數量優勢取勝,但他們的確擁有一些無可置疑的軍事優勢,其中最爲重要的是機動力。大征服期間穆斯林軍奔襲跨越的路程之遠令人震驚。他們的行軍距離自西方的摩洛哥邊緣到伊斯蘭世界東端的中亞地區,綿延遠達七千公里以上。與之相比,羅馬帝國的疆域從哈德良長城延伸至幼發拉底河,距離尚不到五千公里。機動靈活的穆斯林軍在如此廣大的地域中來去如風,佔領了大片地區。他們所穿越的許多地區都是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這些土地只有堅毅可靠的人才能從中暢行。他們的部隊行進時並無輜重車隊。戰士們似乎自備糧草,當補給耗盡時,他們便會就地購買、掠奪或徵取給養。士兵與牲畜都已對貝都因人粗糙貧瘠的飲食習以爲常,並且慣於在惡劣的環境中安然入睡。在寒涼的夜晚依靠閃亮的星星作爲導向行軍是沙漠生活的必備技能,許多有關大征服的史書都曾記載阿拉伯軍在戰鬥中展現了高超的夜戰能力。強大的機動性使他們能夠快速撤往沙漠進行避難、戰敗後重新整編,或者出其不意地突襲敵軍。
穆斯林軍的統帥能力無疑十分高強。軍中的高層指揮官大多出身於希賈茲地區城市居民中的少數精英階層,尤其是古萊氏部族及其分支部族最多,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極其可靠的將才。敘利亞的哈立德·本·瓦立德、埃及的阿慕爾·本·阿斯與伊拉克的薩阿德·本·瓦加斯都是名望遠揚的軍事將領。此後則有北非的烏格巴·本·納菲、西班牙的塔裏格·本·齊亞德和穆薩·本·努賽爾、河中地區的屈底波·本·穆斯林以及信德的穆罕默德·本·卡西姆·薩伽非等優秀將領。阿拉伯文史料還大量記述了戰前軍議和指揮官在實行軍事行動前聽取建議的行爲。儘管這些記述部分是虛構的,目的是爲了生動概括可能確有其事的軍事行動,並凸顯早期穆斯林社會的“民主”特徵,但它們可能也反映了事實,也許當時阿拉伯軍的決策的確需要經過協商和討論纔可施行。
某種程度上說,強大的領導力是阿拉伯社會政治傳統的產物。阿拉伯社會的領導權往往在特定的家族中代代傳承,但在這些羣體中,志向遠大的領袖需要向族人證明自己富有勇氣、智謀過人且善於交際。假如領袖沒能證明自己的能力,那麼族人就會轉而支持其他人。領袖還要考慮他所領導的族人有何觀點與看法。僅靠父輩的廕庇是遠遠不足以成爲合格的領導者的。中亞的伊朗人王太后曾因屈底波的兒子沒有繼承父親的權力而大爲震驚,這一事例便體現了伊朗文化與阿拉伯文化中的不同觀念。無能或獨斷專行的將領都不可能長期爲人信服。阿富汗的烏拜杜拉·本·艾比·拜克拉和河中地區的祝奈德·本·阿卜杜·拉赫曼就屬於這種失敗者。他們很快便倒臺了,並且遭到了同時代詩人與時事評論者的強烈貶損。
在穆斯林的統治結構中還有一些特點促成了他們的成功。史料總是在強調哈里發與總督,尤其是歐麥爾哈里發(634年至644年在位)在組織與領導征服行動中起到的作用。據說許多涉及軍事行動細節的書信都出自歐麥爾的手筆,但實際上這些書信不可能全都是由他所寫,儘管如此,這些敘述材料還是體現了當時的麥地那和後來的大馬士革擁有強大的組織與控制能力。極少有將領敢於違抗命令,遠方戰場或偏遠省份的將領也極少有反叛中央的情況發生。這是十分不同尋常的,因爲相比於同時期的拜占庭帝國,後者的軍力常常因覬覦皇位的地方將領叛亂而大大受挫。令人驚訝的是,像哈立德·本·瓦立德、阿慕爾·本·阿斯、穆薩·本·努賽爾和穆罕默德·本·卡西姆這樣的優秀將領在被撤職召回時,都會乖乖地交出職位回到首都,接受處罰,承受羞辱。
大征服之所以能夠成功,還有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穆斯林軍對待被征服者的方式往往相對較爲寬鬆。只要承諾上交貢賦並保證不協助穆斯林的敵人,阿拉伯將領便會樂意締結條款,爲被征服者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提供保護,宗教場所的權利也會得到保證。在武力攻城中被擊敗的城市守軍時常會被處決,但大規模屠殺平民的事例也極少發生。像在霍姆斯城那樣徵用房屋供穆斯林居住,或強徵其他財產的情況十分少見。蓄意破壞或摧毀已有城市村莊的行爲也同樣罕見。與十三世紀的蒙古軍臭名昭著的屠殺與毀滅行爲相比,可謂判若雲泥。儘管我們無法確定,但可能至少在征服初期,阿拉伯軍對平民徵取的物資和勞役要比拜占庭帝國和薩珊帝國寬鬆許多,他們徵收的稅賦也更輕一些。直到七世紀末,我們才發現有抱怨強徵苛稅的記載出現。很可能對於大多數被征服者來說,阿拉伯軍的入侵僅僅是曇花一現的奇蹟,或者一場僅持續一年的大規模襲掠,此後便會銷聲匿跡—因此,乖乖繳納稅款,簽訂必要的文件,總比眼睜睜看着城池陷落、男人被殺、女人和小孩被賣作奴隸要來得划算。
征服結束後,阿拉伯穆斯林軍隊很快便在新徵服的土地定居下來。他們定居時幾乎總是會與本地居民分區而治。在伊拉克,他們聚居在庫法、巴士拉和摩蘇爾這三座穆斯林新城中。埃及最早的阿拉伯人聚居點是福斯塔特,這座聚落大部分位於開闊的平地上。在北非,主要的早期穆斯林聚落是新建的城鎮凱魯萬,而在呼羅珊,最大的阿拉伯人聚落則是梅爾夫,他們在這座薩珊古城的城牆外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居民區。在敘利亞,阿拉伯人往往定居在已有城市的郊區地帶,而不是佔據城市中心地帶,比如在哈爾基斯和阿勒頗便是如此。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征服軍與當地人之間由於共用庭院與狹窄的街道而發生難以避免的衝突。
阿拉伯大征服在不同地區也有所不同。阿拉伯軍入侵時沿大道行進,一路進攻或招降沿途的主要城鎮。但在大道之外的山區或偏遠村落,一定有許多社區此前從未與阿拉伯人有過交往,可能直到幾周、幾月甚至幾年之後他們纔會聽聞自己已不再受拜占庭皇帝或波斯皇帝的統轄。在阿塞拜疆山區、裏海南岸山脈、庫爾德的丘陵地區、摩洛哥的大阿特拉斯山區和西班牙的格雷多山脈,都鮮見穆斯林的蹤跡。直到早期征服結束後的兩到三個世紀間,纔有穆斯林傳教者、商人和探險家進入這些地區傳播新的宗教,併爲當地人帶來有關新興統治者的消息。這些地區的居民沒有動機抵抗入侵者,因爲入侵者繞過了這些地區。
我們在上文中曾多次提到,穆斯林征服者極少有逼迫被征服者皈依伊斯蘭教的行爲。任何強迫改宗的行爲都可能會引發大規模反抗或公開敵視。因此,穆斯林統治者與教會領袖和其他臣服於他們的宗教機構建立了一套合作關係。人們部分是因爲財政壓力而改宗,爲了逃避臭名昭著的人頭稅而皈依伊斯蘭教,但不僅如此,改宗還能使人獲得機遇逃離現有社會階層約束,成爲新興統治階層的一員。對於想要謀得軍職的人來說,皈依伊斯蘭教是必須之舉。到十世紀,在某些地區還要更早,沒有穆斯林身份就很難在文官系統中官運亨通。因此,這個新興信仰的魅力主要在於吸引力,而非強制力。
在建立以來的頭一個世紀,穆斯林帝國的社會環境十分開放。穆斯林是新興帝國的精英階層,他們宣稱伊斯蘭教是面向全人類的宗教。任何想要皈依伊斯蘭教的人都可成爲這個精英羣體的一分子。相比之下,羅馬帝國的公民或波斯帝國的貴族則是難以企及的特權階層,受既得利益者捍衛。皈依新興的伊斯蘭教之後,被征服者也能夠成爲征服者,加入統治階層,並且至少在理論上與其他穆斯林共同享有平等地位。誠然,不久之後穆斯林元老和新皈依的阿拉伯及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間便爆發了長期的暴力鬥爭,但這不能否定伊斯蘭教是對所有人開放的。
早期穆斯林還抱有強大的文化自信心。真主通過先知穆罕默德用阿拉伯語向他們傳達訓誡,他們遵從真主的信仰,傳播真主的語言。我們可以將他們與五世紀入侵西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相比。日耳曼人佔領羅馬帝國的領土之後,他們便拋棄了舊有的諸神,皈依了基督教,也即他們所征服帝國的宗教,至少就我們所知,沒有人宣稱神的語言是日耳曼語。強大的文化自信心確保阿拉伯語成爲行政語言與新興高等文化的語言載體。任何人想要完全融入政府或知識活動,就必須能夠讀寫阿拉伯語纔行,最好還有穆斯林身份。這與西歐的日耳曼國家也差異明顯。至少到十二世紀爲止,西歐的日耳曼人仍舊將拉丁語作爲行政語言和高等文化語言,新興統治階層仍舊使用諸如“公爵”(dux)和“伯爵”(comes)之類的拉丁語頭銜,而日耳曼語則只有方言俗語留存下來。但穆斯林的頭銜如“哈里發”(khalīfa)、“埃米爾”(amīr)和“瓦力”(wālī,即地方官,總督)都源自阿拉伯語。
儘管如此,征服僅僅爲改宗拉開了序幕。穆斯林建立了一套政治與社會架構,因此伊斯蘭教才能在其中緩慢發展擴張。到1000年,穆斯林可能在所有於750年前被征服的地區都成了多數人口。大征服並沒有引發改宗,但它的確爲其奠定了先決條件:沒有大征服,伊斯蘭教也就不會在這些地區成爲主流信仰。
穆斯林征服的成功還要歸功於當時獨特的歷史條件和新興一神論信仰的傳播。伊斯蘭教擁有許多便於基督徒和猶太教徒理解接受的特點。它擁有一位先知、一部聖書、完善的祈禱文、飲食準則和家庭法。亞伯拉罕和耶穌在穆斯林傳統觀念中同樣也是偉大的先知。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作爲一個獨立的宗教發展起來,但它卻宣稱是過去一神論宗教的完善者,而非摧毀者。伊斯蘭教並不像其他某些宗教(比如佛教)那樣陌生,因此它與既有宗教的相似性和共同的宗教傳統很可能也鼓勵並促進了人們改變信仰。
在很大程度上,穆斯林針對敵人的政策也使他們的統治被廣爲接受:畢竟絕大多數情況下,向入侵者投降,訂立和約並上交貢賦總比頑抗到底更划算。假如政治層面的征服沒有完成,伊斯蘭化與阿拉伯化進程也就不會在征服結束的兩到三個世紀之後出現,但這種轉化並不是征服所直接導致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越來越多人自覺自願地認同和參與當時的主導文化,漸漸以幾乎完全和平的方式造成了伊斯蘭化的普及。
歸根結底,穆斯林征服的成功是整個後羅馬世界的動盪衰敗、貝都因武士的堅忍頑強以及新興伊斯蘭教的激勵與開放特質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