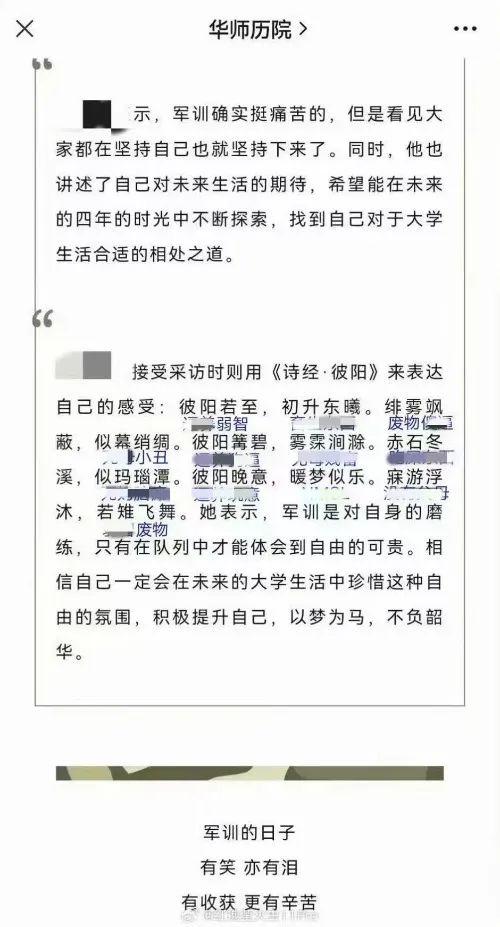傅山的一幅楷書對聯!
對聯最初起源於民間詩歌、民謠,《詩經》中就經常有類似對聯的句子。古代詩歌中更是經常出現對句和聯語。從宋朝開始,文人學士寫對聯之風十分盛行,如王安石、蘇氏父子等均是寫對聯的高手。這樣對聯和書法就結合起來,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輝映,成爲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藝術傳統之一。而集聯,或叫集句、集字,即集碑帖詩文之字句爲聯的一種文藝創作形式,也就成爲人們用以練習書法的一種手段或書法創作的一種形式了。歷代書家都非常喜歡以楹聯書法這一藝術形式進行創作。優秀的楹聯書法,大都是整飭中見變化,變化中見統一,統一中有神采的精美藝術品,是形式與內容互爲表裏、和諧一致的佳作,反映了作者的文化素養、審美趣味和藝術追求。

現以清代著名學者、書畫篆刻家傅山(1607—1684,字青主)的一幅楷書對聯作一例解。
傅山的主要精力多用在做學問上,至於書法,“不過借纖豪、片楮以陶寫性情,銷磨歲月”。(《太原段帖·序》)由於他青少年時期,在臨習晉唐楷書上下過一番功夫,成年後又博涉篆隸行草諸體,終於成爲極富創新精神的一代書法名家。
傅山所處的正是董(其昌)字風靡書壇的時代,但在傅山看來,董其昌的書法“止是一個秀字”,他所推崇的是“心畫自孤傲”的顏字。當下藏品出手及春拍藏品甄選一五零五六九二五六一五鄭女士致力民間藏品出手渠道建設成交後佣金高。他崇敬顏真卿的人品,進而欣賞、追摹其書品。他的楷書楹聯“竹雨松風琴韻,茶煙梧月書聲”,就是一幅具有顏字風神的六言楷書力作。
從這幅楹聯楷書作品來看,他將顏字的那種厚重樸拙之態,博大雄渾之勢,揉進了他自己具有的結體嚴謹緊密的特徵之中。顏字結體寬博,筆畫與筆畫之間的空隔較大,然而傅山不是這樣,他處理筆畫間的距離恰恰相反,易寬疏爲緊密,只要與顏真卿的《自書告身帖》作一比較,便一目瞭然。

在取勢相同、變方爲圓、力求篆籀氣息等方面,他還是嚴守師法的。不過仔細考察,他這十二個字的用筆,又吸取了不少東坡先生的筆意。蘇軾的《羅池銘詞》,寫得“肉豐而骨勁,態濃而意淡,藏巧於拙,特爲秀偉”。(明婁堅《學古緒言》)傅山的這幅楷聯也是寫得粗壯豐厚,沉着剛健,起筆、行筆、收筆都無不具有《羅池銘詞》的神采和豐潤。這樣,他的字雖然具有顏字的風神,但在結體上改寬博爲緊密;雖然具有蘇字的豐潤,但用筆不似蘇公那樣率意灑脫,就其整體而言,是斜中求正,拙中見巧,表現了生氣鬱勃的倔強風姿。這一點正體現了他的人品和個性。
傅山在書法理論上也有其獨到的見解。他的“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的觀點,一直受到後人的重視。如果用傅山的書學主張來驗證他的這幅楷書楹聯,似乎不無相悖之處。如聯文中的“雨”、“韻”、“茶”、“月”等字的取勢以斜求正,如“琴”“茶”、“聲”等字的左撇斂,右捺縱,以及“松”、“梧”兩字的木旁的處理,以及所落的簡款“傅山書”三字,都莫不是出於匠心的巧妙“安排”。但仔細品位,這種“安排”不但不彆扭,反而使人覺得合情合理,意趣橫生,給人一種拙中有巧、醜中有媚、真率自然的視覺效果。

傅山的另一幅楷書對聯“性定會心自遠,身閒樂事偏多”,雖然從藝術追求和書寫形式上彷彿更能體現其書學主張,不過從整體風格看,去上聯不遠。仍然是大匠運斤,不著痕跡,也還是其人格、心性和風骨的外化。
(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