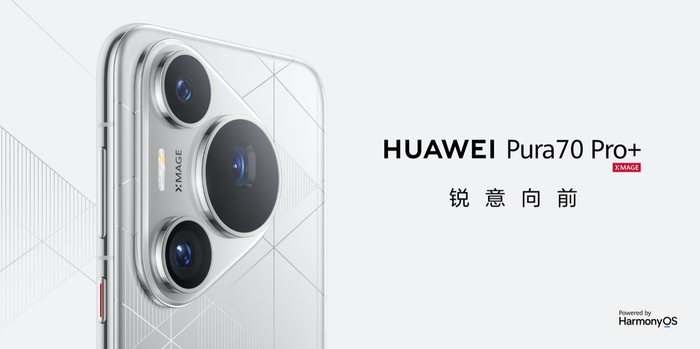“原著粉”爲什麼不喜歡影視改編?
摘要:如今的文字內容更多地作爲影視化的改編材料而存在,依靠抽象文字獲得個人想象只能成爲一種小衆愛好,或是作爲未被圖像覆蓋到的遺珠。看到這裏也許你會說,雖然影視化改編對文字內容進行了限制性的再加工,但它同時也提供給了我們更確實、更長久、更可供調取的記憶,這有什麼不好嗎。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看理想(ID:ikanlixiang) ,作者:蕎木,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們快要被不斷包抄而來的影視改編給寵壞了。
比如很多書,一旦看過了影視改編,就當做自己看過這本書了;比如金庸劇裏的原創劇情已經嚴重影響了你對於原著的記憶。
比如先看完劇或者電影,再掉頭回去看文字的時候,角色是帶臉的,對話是有聲的,情節是腦內不斷播放畫面的;比如和朋友聊起某部作品,對此不瞭解的人一定第一個想起演員的臉:“就是XXX演過的那個嗎?”
儘管現在衆多的IP改編劇都被扣上了“不夠還原”的帽子,“原著粉”對改編時“魔改”的控訴也從未停歇,但你不得不承認,一旦某部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獲得成功,那麼一切就都回不去了。
隨着IP開發鏈條的不斷成熟,我們的記憶也在不斷地發生着迭代,從書本賦予角色的一個輕飄飄的名字和幾行描述,到被圖像覆蓋,被動畫覆蓋,被活生生的演員面孔覆蓋,最後腦海中的形象永久停留在這裏,幾乎已經成爲了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生在一個影視化的年代,必然是幸運的,因爲我們有機會看到古代文明的重現、矮人與精靈的戰鬥、賽博世界的光影。
但同時,我們的想象力又是如此脆弱,以至於基於文字的個人幻想可以輕易被洗牌,最後,真的很難留下什麼屬於自己的東西。
集體回憶也許是美好的,但是被影像統一馴化後的“集體想象”與“集體理解”則成爲了美好背後潛藏着的危機。
1. 被限制的想象
基於文字的想象可以說是想象力的起點,幾乎每個人都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構建起過屬於自己的幻想世界,而我們的想象力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偷懶的?也許是從接受的內容越來越具象開始。
說起小美人魚,你是不是會下意識地想起那個紅頭髮綠尾巴的迪士尼動畫形象?但是原著裏其實除了“她的眼睛是蔚藍色的”之外就沒有再多的外貌描寫了,所以爲什麼你想到的不是一個金黃色頭髮藍色尾巴的小美人魚呢?
此外,如果想象“小美人魚跟海里的魚嬉戲”,是不是腦海中可以馬上出現畫面?如果要想象的是“小美人魚化作了大海的泡沫”呢?由於這一幕並沒有出現在動畫裏,是不是想象起原創畫面來,明顯就要更困難一些了?
說起超人,你想到的是什麼?大概率是現任超人演員亨利·卡維爾的臉——也許你並沒有看過他主演的任何一部超人影片,但他的劇照海報就是優先於超人漫畫形象以及那個經典的S標誌出現在了你的腦海裏,爲什麼?
再比如,郝思嘉應該長什麼樣?毫無疑問,應該長費雯麗那樣。郝思嘉可以長成其他樣子嗎?你不知道,因爲費雯麗的劇照甚至被印在了《飄》這本書的封皮上。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裏面寫到,印刷文字是維繫一個民族“想象的共同體”的重要媒介,“這些被印刷品所聯結的’讀者同胞們’,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見之不可見’當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體的胚胎”。
但自從電影、動畫和電視劇誕生以來,毫無疑問,如今它們已經在建構“想象的共同體”上起到了更加肉眼可見的作用: 它們直接抹平了人們的想象,把幻想中的一切整合成了一個真實的、固定的形象 。

相比於文字中所提供的形象與情節還需要讀者發動想象力去對其進行激活,影像內容給觀衆帶來的則是直接的視覺衝擊——甚至可以說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如果說動畫還需要觀衆自己完成二三次元的思維轉換,那麼電影和電視劇裏的畫面則無需什麼消化時間,就能直接與記憶接軌。
人是會偷懶的,我們的腦子也是。
當我們逐漸形成在影視畫面中直接獲取形象的習慣之後,也正在逐步丟失從文字中獲取抽象形象、在自己腦內重組的能力。最後,在想象力的懶怠中,確實的影像獲得了統治霸權,具象的畫面覆蓋了抽象的描述,動態的視覺體驗取代了腦內平板的空中樓閣——
在這裏,從文字到影像的改變就不再只是傳播媒介的進步了,而是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發生了變化。
2. 不可逆的加速
也許你有聽說過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其實這個觀點並沒有看起來的那麼難懂,麥克盧漢認爲: 媒介變化本身就是一種重大的社會變革。
在印刷媒介時代,文字作爲一種高於生活的概括,把生活中散亂的感官體驗提煉成爲單一維度的敘述,給我們帶來了線性的、連續的、富有邏輯的思維方式。
閱讀文字的過程,更多是在抽象的指引下進行擴展想象的過程。也因此,面對相同的文字,由於不同的人填充了不同的生活經驗,所以得到了完全不一樣的收穫,這讓閱讀成爲了獨一無二的私人體驗。

而到了影視媒介時代,它重組了被印刷媒介打亂的感官平衡,真正提供給了觀衆“所見即所得”的感受。
影視畫面的思維方式是複雜且講究直覺性的:撲面而來的光影效果佔據了觀衆的眼睛與耳朵,讓人忍不住去追逐後續的情節,獲得直接的感情反饋,甚至思考都變得滯後,更不用說額外的想象。
儘管觀影體驗依然是私人的,但是每個人看到的影像內容確實是公共且恆定的, 這些影像被儲存進了我們的腦海裏,成爲了覆蓋文字的、更接近現實的的共同記憶。
當然,這裏並不是要批判影像扼殺了我們的想象力,並呼籲大家迴歸書本,而是不得不點明一個事實:大衆媒介的更迭擴大並加速了人們的感知功能, 我們的思維和行爲習慣都已經被影視化的到來所永久改變了 ,隨着網絡的進一步發展,這個加速只能越來越快,不可能減速或者倒回從前。
所以,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接受或不接受,一切都註定回不去了。
如今的文字內容更多地作爲影視化的改編材料而存在,依靠抽象文字獲得個人想象只能成爲一種小衆愛好,或是作爲未被圖像覆蓋到的遺珠。
在影視化的圍追堵截下,我們還剩下什麼各不相同的個人想象?也許是《背影》裏“父親”翻火車站臺時那個笨拙的身影吧,畢竟我們腦海中的閏土都是同一個樣子的——就是課文旁邊的插畫裏那樣。
3. 被替換的記憶
看到這裏也許你會說,雖然影視化改編對文字內容進行了限制性的再加工,但它同時也提供給了我們更確實、更長久、更可供調取的記憶,這有什麼不好嗎?
畫面的確把關於文字的記憶變得更真實了,但同時,因爲我們腦海裏有畫面的部分被定向加強了,所以沒有畫面只有文字的部分就被消減了,最終,在記憶的競爭裏走向遺忘。
也就是說, 改編正在無比深刻地影響着我們關於原著的記憶 。
再回憶起《哈利·波特》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想到九又四分之三站臺,魁地奇比賽,霍格沃茨保衛戰,斯內普之死……但是說到由女主角赫敏發起的家養小精靈解放運動,也許很多讀過原著的人都已經沒有什麼記憶了,因爲這部分在作者書中花了大量筆墨去寫的支線,在電影版裏被完整地刪掉了。
初讀這條支線,會感覺家養小精靈解放運動彷彿一個可笑的學生鬧劇:比如赫敏對於家養小精靈略顯幼稚的同情心理、過於理想化的解放策略、身邊人的諸多嘲諷、家養小精靈羣體自己的不認同……
但是,也有很多讀者通過赫敏的行爲感受到了家養小精靈不只是一些長相奇異的寵物,而是和很多人類一樣的、正在受到壓迫的少數羣體,甚至這個羣體中的大部分成員還沒有認識到自己可以拒絕被奴役的命運。
也許這條黑白並不分明的支線最有意義的部分就在於,作者沒有把明晃晃的道德教化擺在桌面上,而是把自由聯想的餘白交還給了讀者,讓讀者有機會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中看到故事情節的復現——這可能就是我們對很多小說情節念念不忘了很多年的根本原因。
後來,連羅琳自己都在採訪中說到,哈利·波特電影裏讓她比較後悔的部分就是“家養小精靈權益促進會”的內容沒能出現在影片中。
或許是不夠有戲劇張力,或許是看起來並沒有那麼“重要”,總之,這條支線就被永遠埋沒在了很多人的記憶之外。


當然,無論是更嚴肅的文學名著、還是更大衆的網絡小說,在改編的時候被排除在外、以至於被大部分人遺忘的原著經典情節實在是有太多太多。
比如豆瓣用戶@Enjolras 就說過:“事實上,’還原原著’從來都只能是加分項,但不是必要項。否則,沒有一個金庸迷能接受任何一個版本的《倚天屠龍記》,因爲書中的張翠山的成名兵器是判官筆和虎頭鉤,而不是電視劇中的用劍;也不會有一個古龍迷能接受焦恩俊版的《小李飛刀》,因爲孫小紅在書裏是李尋歡的愛人,和阿飛沒關係,且壓根沒有’驚鴻仙子’楊豔這號人物。”
雖然我們都明白在這個時代,文字作品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改編在大衆語境中獲得更長久的生命力,但是在改編這件事上,“原著粉”對劇方的聲討也從未停歇過。
如果是大刀闊斧的“魔改”,那必定是罵聲滔天;就算在外人看來是“良心還原”、“忠於原著”的改編,“原著粉”也總能挑出多多少少的錯處來。
有人說,既然作者都靠着改編名利雙收了,這些不滿意的書粉當做影視改編不存在不就行了? 但其實,在畫面能輕易壓垮想象、壓縮記憶的情況下,原著根本不可能做到獨善其身。
之前有很多大IP的書粉在面對改編內容時都號召過“書劇分離”,即原著與改編井水不犯河水,要求改編內容的名字改爲劇版XXX、電影XXX,並且表示演員並不代表原著角色、劇版原創劇情不代表原著,甚至各自啓用單獨的分區……
而最後,不成功的改編會被時代淘汰,成功的改編只會更加成功地覆蓋原著。
所謂“書劇分離”終究只是願景,而現實是大衆語境下面的碾壓與重寫。幾年過去,太多看過原著的人都只能記得改編的劇情,甚至在百度詞條裏面,原著都逃不過被摺疊的命運。
我們記住了太多,以至於根本不記得自己忘記了一些什麼。
4. 被現實填充的人
這幾年,隨着IP開發產業鏈條的不斷成熟,但凡是一本新鮮火熱的書進入了改編流程,必定環節緊湊、上下游分明:從出版,到動漫,有聲劇,劇集\電影,周邊產品,主題公園……

無法否認的是,這些內容的確提供給了我們一個更加豐富、真實、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世界。
杜拉斯在《情人》裏面描寫的炎熱而又單調的生活環境,在《情人》電影鏡頭所展現的集市裏變得真實可感;《冰雪奇緣》的同款裙子給了太多女孩擁有魔法的機會;公園裏的大型遊樂設施讓《加勒比海盜》裏的航海冒險夢想成真。
但同時,這個開發的固定順序,其實也是產品內容一步步填充並擠佔你所有感官的順序。
這種信息填塞,讓我們越來越像某種意義上的機器——或者說,變成了習慣於被動輸入而不會主動創造的信息人:不停接收被設定好的內容,喜好和口味越來越趨同,最終被商業體系打造成標準消費者的樣子。

不知道你有沒有質疑過,爲什麼改編的上下游不可逆?就是因爲當你已經全盤接受了某個形象被設定好的面孔、動態、聲音、甚至觸感之後,再折回去看單維的文字、圖片、有聲劇,都會在腦子裏自發地補足其餘部分——而且在這裏,一千個人會不約而同地補足出同一個哈姆萊特。
“給他們填滿不易燃的信息,拿’事實’餵飽他們,讓他們覺得胃脹,但絕對是信息專家。這麼一來,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在思考,明明停滯着卻有一種動感,他們就會快樂,因爲這類事實不會變化。”這是雷·布拉德伯裏在《華氏451》裏寫下的話。
現實世界裏,也許不會有人強制性地燒書,但是跟燒書同等可怕的事情一直在悄無聲息地發生着。
這裏大致是不需要搬出尼爾·波茲曼的理論來重申一下娛樂至死的道理,商業的大手不可撼動地在推着所有人往前走,因爲我們永遠空虛,永遠好奇,永遠渴望更真實的真實。
也因此,留白始終可貴,但難以保存;想象永遠浪漫,但易被折損;記憶一直真誠,但常被重寫。
如果你還記得,《小王子》故事的開頭是“我”小時候畫了一條正在吞喫大象的蛇,而在大人們的眼裏,那只是一頂平平無奇的帽子。


於是十分挫敗的“我”感嘆道:大人們靠自己永遠搞不懂任何事,總是需要別人替他們說明。
也祝願我們能永遠記住那個不是帽子的可能。
參考資料: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馬歇爾·麥克盧漢 | 譯林出版社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上海人民出版社
Pottermore.com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看理想(ID:ikanlixiang) ,作者:蕎木,監製:貓爺,配圖來自《雨果》《成爲簡·奧斯汀》《機器人總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