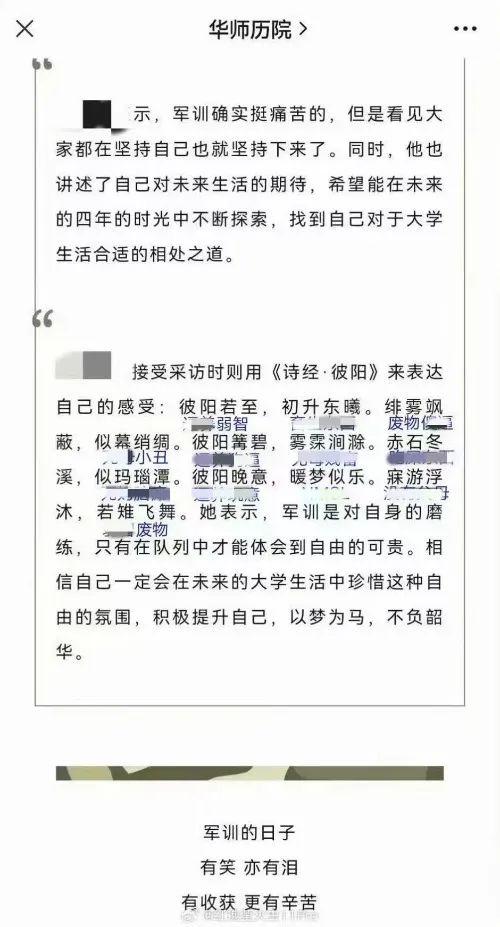自然書 | 虞彩虹:芍藥
自然書
女子邀請男子同去觀景。男子雖已看過,依舊答應同去。不爲觀景,只爲可以相與戲謔。臨別男子以芍藥相贈,以示愛慕。
芍藥
牡丹彷彿是芍藥甩不開的影子。比如,唐代劉禹錫有詩曰:“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讚美牡丹出衆,自是無可厚非,可因此不惜說芍藥妖無格、芙蕖少情韻,叫人心內頗有不平。
誰曾想,作爲藥用植物,芍藥和牡丹共同出現於我國最早的本草著作《神農本草經》,芍藥位列中品,而牡丹位列下品。牡丹那個“木芍藥”的別名,足以說明,從前牡丹並沒有芍藥那麼知名。芍藥早早入了《詩經》,亦爲佐證之一。《詩經·鄭風·溱洧》雲:“溱(zhēn)與洧(wěi),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於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春風送暖,河流解凍,三月三日的上巳節,溱洧兩水附近的人們,手執蘭草去水邊沐浴,以祓除不祥。女子邀請男子同去觀景。男子雖已看過,依舊答應同去。不爲觀景,只爲可以相與戲謔。臨別男子以芍藥相贈,以示愛慕。
芍藥跟牡丹,易被混淆,這倒也是事實。多年前,我曾與同事認真請教度娘,當時似乎是頗爲清楚了的,可事後卻忘得一乾二淨。後來,清明祭祖,在芍藥地裏,又曾就芍藥和丹皮怎麼區分請教於公公,亦得詳細解答,後又全然忘卻。這就好比跟一些人,有過一面或幾面之緣,長久不見,終又陌生起來,回到原點。說到底,是用心不夠,亦或緣分未到。
事實上,在我很小的時候,芍藥是作爲藥材得以普遍栽植的。在父親有限的務農生涯中,所種藥材似乎只有芍藥、丹皮與桔梗。加工時,隱約記得芍藥根要用刀切,丹皮要抽去那根白色而光滑的芯,桔梗則需去皮。只是,我怎麼也沒想到,丹皮竟是牡丹皮。度娘雲“花多爲白色。以根皮入藥,稱牡丹皮,又名丹皮、粉丹皮、刮丹皮等,系常用涼血祛瘀中藥。”
其實,關於芍藥與牡丹如何分辨,早有人總結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來,綜合一番,約摸如下:牡丹,木本,枝幹硬朗結實,芍藥,草本,花枝相對柔軟;牡丹葉寬,葉形三裂,葉面綠中泛點黃,芍藥葉片狹窄,是單葉,正反面均爲黑綠色,亦更有光澤;牡丹花期一般在4月下旬,芍藥花期則在5月上旬,故有俗語“穀雨三朝看牡丹,立夏三朝看芍藥”;牡丹花色亦比芍藥豐富許多。
一個木本,一個草本,表面看,是劉禹錫說芍藥“妖無格”的原因,其實,裏面隱含了牡丹的逆襲過程。在唐以前,與牡丹有關的記載幾乎都與藥用價值有關。一個普通人的喜好未必能改變一種花的命運,但一個掌權者的喜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由於受到武則天的鐘愛,牡丹被大量培育,不但品種花色增多,且出現了雙頭牡丹、千葉牡丹等觀賞性極高的新品。唐玄宗開元末年,裴士淹從汾州(今山西隰縣)衆香寺得白牡丹一棵,植於長安私第,到天寶中成爲都下奇賞。唐李濬《松窗雜錄》記載,唐玄宗命人將紅、紫、淺紅、通白四種牡丹種於沉香亭前,一日邀請楊貴妃月下賞花,命李龜年奏樂,李太白寫詩。李太白以牡丹花之美喻楊貴妃之貌,作《清平調》三首。第三首雲:“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紅樓夢》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寶玉感嘆草木有情,所引“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的典故,就是出自於此。牡丹終被譽爲國色天香,它和芍藥的地位也因了貴族的喜好而逐漸發生逆轉。在五代人所編的花卉排行榜《花經》中,牡丹位於“一品九命”,而芍藥僅排第三,列“三品七命”。從此,牡丹爲花中之王,芍藥爲花之丞相的說法日漸深入人心。
雖如此,也不能阻擋人們對芍藥的喜愛。它有別名曰將離草,故古代男女在表達結情之約或依依惜別時都會互贈芍藥,《詩經》裏那個男子贈芍藥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古代西方也有關於芍藥花的傳說。西方人一直認爲芍藥具有某種魔力,凡有芍藥生長的地方,惡魔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可對抗至毒之花——曼陀羅。在我看來,牡丹和芍藥各有其美,誰也無法替代誰。
提及芍藥花的古詩詞頗多,唐有白居易的《感芍藥花寄正一上人》《草詞畢遇芍藥初開》、韓愈的《芍藥歌》、張泌的《芍藥》、元稹的《紅芍藥》,宋有洪炎的《次韻許子大李丞相宅牡丹芍藥詩》、秦觀的《春日五詩》、姜夔的《揚州慢·淮左名都》,元有劉敏中的《清平樂·張秀實芍藥詞》、王哲的《紅芍藥》等。只是,除卻韓愈,多是借花抒情,少有真正用心寫芍藥花的,讀來不免有些遺憾。倒是在藝術繪畫史中,有關芍藥的藝術精品豐富多彩。比如,光緒皇帝曾御筆《芍藥圖》,著名油畫大師張秋海曾作《張秋海芍藥圖》。
不過,再好的詩詞與畫作,在《紅樓夢》的“憨湘雲醉眠芍藥裀”面前,都不免遜色幾分。“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蜂蝶鬧嚷嚷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那些詩畫,又怎敵得過憨態可掬、醉臥花下的史湘雲?人與花相得益彰,是《紅樓夢》的經典,亦是芍藥花的幸運。
閒人看花,農人重果。芍藥所謂的果,其實就是地底下的根,外表淺黃或灰紫,內裏白色,富有營養,具有鎮痙、鎮痛作用,該是芍藥的精華了。芍藥一般種植三年後採挖,稱毛芍藥。將毛芍藥的塊根剪斷,去除其他根鬚,剩其尾根,每兩根一株,種下,四年後採挖,稱結芍藥。這是父親告訴我的。結,應有控制其生長根數的意思,頗爲形象。想起白朮、玄蔘、貝母等,都是借摘花來保證根莖營養的。若爲藥材之需,將芍藥花於含苞時就摘除,別說芍藥花會心碎,我也會心碎的。父親還說,從前買賣芍藥未必稱斤論兩,還有“判芍藥”,即按芍藥所開花朵大小來定價,花朵碩大者自然價高。憑花判果(即根),一個“判”字,生動地道出了別樣的買賣方式。此外,還有拿芍藥根敲擊酒壺,辨其聲而給價的。“好芍藥,一根可以換一壺酒。”幾乎滴酒不沾的父親,說起來竟頗嗜酒一般。這是一個種過芍藥的人,纔會有的說話語氣。
芍藥集觀賞、食用、藥用於一身。且不說長成後抑或開花的芍藥,單是芍藥的芽,亦是一道至美風景。初春,草地遠未泛綠,但紅紫的芍藥芽卻已早早從泥地拱出,油亮、茁壯,如筍狀,似筆尖,那真是大地上極富生機的一幕。
以花爲食材,是美食,更是美事。以芍藥花爲食材的美食,不可勝數。煮粥、製茶、做餅……清代德齡女士有《御香縹緲錄》,曾敘述慈禧太后爲養顏益壽,特將芍藥花瓣與雞蛋、麪粉混和後用油炸成薄餅食用。此外,還有芍藥花羹,芍藥花酒、芍藥花煎等,這些名字,聽着就已非常美好,亦叫人頗想一試。
芍藥也曾是調味品。西漢辭賦家枚乘《七發》雲:“熊蹯(即熊掌)之臑,芍藥之醬。”可見芍藥在東漢時是一種調味用的香料。再如司馬相如《子虛賦》雲:“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東漢經學家服虔認爲“芍藥之和”的意思就是以芍藥給食物調味。不過隨着大蒜、胡荽等香料引入並廣泛運用,芍藥這種香料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怪不得宋代陳元靚《事林廣記》、清人顧仲《養小錄》等所載的香料中,均不見芍藥之身影。
“牡丹之愛,宜乎衆矣”,不足爲奇;洛陽有牡丹花節,亦不足爲奇。如今,各地花節雨後春筍般冒出,其中亦含了芍藥花節。人們趨之若鶩,紛紛要在有限的花地裏拍出無限的花海來。其實,每年的四五月,農人自然種植的土地當中,還能欣賞到零星的芍藥花與丹皮花,或紅或粉,美得自然。和那些所謂的花海比起來,這些芍藥與丹皮,從哪來,將到哪去,明白、單純,亦叫人心裏更爲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