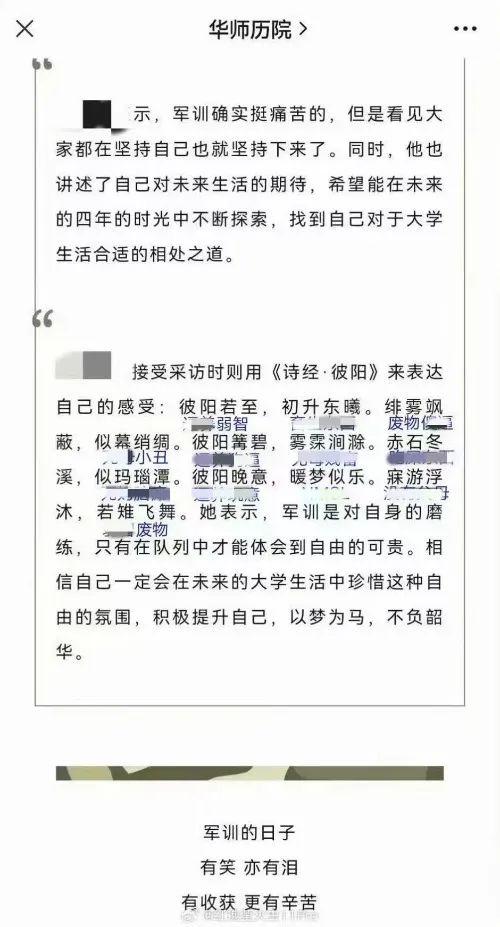《詩經》公案:一曲《卷耳》誰在唱?爭論兩千年,連錢鍾書也捲入

《卷耳》是《詩經》名篇,歷來傳唱、吟誦不衰。但它牽涉到一樁“著作權”案,以至於2000年來糾纏不清。
這樁公案的焦點是,《卷耳》裏的“我”是誰?
看起來多簡單,值得爭論嗎?——先別忙着下結論,看看捲進這事裏的當事人您再說:
毛亨(戰國),焦貢(西漢),鄭玄(東漢),孔穎達(唐),朱熹(宋),方玉潤(清),程俊英、周振甫、高亨、餘冠英、錢鍾書(現代)……幾乎歷朝歷代都是,皆全是學問大家。

遲遲春日
01公案背景
這個案子和現代社會的著作權案大有不同:
第一點,作者不是主張權益者。
《詩經》時代,在遲遲春日或雝雝鳴雁的秋天,常見一個人搖着木鐸,出沒于田間地頭、周行陋巷,他可不是貨郎,而是周王的采詩官,被稱作“酋人”或“行人”。
丁當的鐸聲中,耕田的、伐木的男人,採桑的、採野菜的女子都聚攏過來,開始秀自己的才藝,於是“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都從縱橫阡陌中流出,匯入了《詩經》的大江大海。
——他們是我們民族最初的詩人。
這些詩人有個特點,他們唱他們的勞動和飢餓,唱他們的痛苦與快樂,然後別無所求;沒有人伸出手來說:來,給我稿費!也不爭什麼署名權,哪怕後人把詩作安在哪位國君、哪個后妃名下,他們也全然不在乎。
——這,可以作爲“《卷耳》案”“爭訟”的引線。假如在作品後署上“某丁”“某好”,起碼也給後人留下點線索!
第二點,作品不受“著作權保護期限”和“訴訟時效”限制。
沒有作者來爭訟,並不代表沒有人爲他們(包括詩中的主人公“我”)來主張權益——上面提及的各路“大佬”就是“《卷耳》案”的“代理律師”。
他們也有個特點:沒人委託他們,給他們“訴訟費”,打贏了也不會升職升薪,他們完全是在打一場“公益”官司。爲什麼要打?——爲了他們心中的文化傳承。

卷耳
02原始卷宗
“《卷耳》案”最原始的卷宗就是一首詩,4章,70個字,最初是酋人們抄在竹木簡上,然後在帛上、紙上,以手抄本或印刷本的形式流傳下來: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籲矣!
對《卷耳》的註釋構成了第二個層面上的卷宗,但是從這個層面上起,就充滿了爭議甚至牴牾,一直深入到每個字每個詞的解釋。簡單舉例:
(1)采采,一說茂盛,一說採了又採。(2)卷耳,共識爲蒼耳,亦有人認爲是地耳。(3)周行,共識爲大路,孔穎達等認爲是周朝的位列。(4)玄黃,一說馬本來毛色,一說馬因病所致毛色。(5)兕觥,一說野牛角制的酒杯,一說是青銅做的牛形酒器。(6)砠:有土的石山,或謂山中險阻之地。
涉及到難解的詞語其實還不是關鍵問題,因爲大可以模糊處理,下面是程俊英先生的白話譯文,在裏面我們可能瞧不出根本問題來的:
採呀採呀採卷耳,不滿小小一淺筐。
心中想念我丈夫,淺筐丟在大道旁。
登上高高土石山,我馬跑得腿發軟。
且把金盃斟滿酒,好澆心中長思戀。
登上高高山脊樑,我馬病得眼玄黃。
且把大杯斟滿酒,不讓心裏老悲傷。
登上那個亂石岡,馬兒病倒躺一旁。
僕人累得走不動,怎麼解脫這憂傷!
沒問題吧?可是越過語言層面,看看裏面的“我”之後問題就來了!
問①:採卷耳的人和登山的人是同一人嗎?按程先生譯文,採卷耳的是女子,她是採了卷耳又去登山懷人嗎?也有人認爲採卷耳的是男子,那麼是他徵發在外,帶僕人採卷耳又登高懷人?
問②:如果採卷耳和登山的不是同一人,那麼怎麼會出現兩個“我”?——一個是真實的我,一個是想象中的對方?那麼,採卷耳的是真實的我,還是登山的是真實的我?
問③:會不會是兩個人在不同的空間同時出現?一個採卷耳,一個登山?可能嗎?
……

03精彩的筆墨官司
下面我們就模擬一下這場打了2000年的筆墨官司,代理律師是歷代學者,而《卷耳》的當事人——缺席。
- 第一場:
律師:孔穎達(唐代經學家,孔子31代孫,著《毛詩正義》疏),律師團榮譽成員毛亨(戰國經學家,著《毛詩正義》傳)、鄭玄(東漢經學家,著《毛詩正義》箋)
結論:《卷耳》的“我”共3人,甲是周后妃某,乙是周使臣某,丙是周王某。丙和甲是夫妻關係,丙和乙是君臣關係。整首詩的作者是后妃“我”。
事實與證據:
第一章“我”是后妃。從採卷耳,連淺筐也裝不滿寫起,表現后妃憂心忡忡,想着君王能任用賢臣。“嗟我懷人,寘彼周列”就是后妃心裏想着賢臣們怎麼才能進入周朝廷的位列之中!
(此後妃之憂爲何事,言后妃嗟呼而嘆,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爲朝廷臣也。)
第二三章的“我”有兩個,騎馬登山的是使臣,喝酒傷心的君王。后妃希望賢臣到周,賢臣果然就到了,他不辭勞苦、跋山涉水去出使。國君感念臣子辛苦,內心憂傷,想着臣子回來後舉金罍、兕觥感謝他。怎麼推斷喝酒的是君主?因爲“人君黃金罍”。
(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
第三章是后妃。這一章承第一章,是后妃的感慨,使臣爲君主辛苦效命,僕馬皆病,因而感動、憐憫。
(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悅華按:鄭玄、孔穎達等做的是“經人解經”的工作。他們不會把《詩經》看作文學作品,而是看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因此滿眼是君王后妃,聖主賢臣,所以後世多不認同。
但帶有啓發性是,孔師雖認爲《卷耳》中的“我”多達三人,但敘述者卻是一人,那就是后妃“我”。換句話說就是:全篇都是后妃在吟唱給君王聽的,她先爲不得賢臣而憂傷,又設想賢臣到來後非常辛苦,建議君主好好對待。所以其中的“我馬虺隤/玄黃”的“我”是“我臣”的簡稱;“我姑酌彼金罍/兕觥”中的“我”是“我君”的簡稱。
(孔: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

方玉潤的《詩經原始》
- 第二場:
律師:方玉潤(清代學者,《詩經》研究大家,著有《詩經原始》)。律師團榮譽團員焦貢(西漢哲學家,著有《焦氏易林》),程俊英、餘冠英(現代學者,分別著有《詩經選注》《詩經選》)等。
結論:“我”指兩人,一是採卷耳、飲酒的思婦“我”,一是行役登山的丈夫“我”。而詩的敘述者是思婦“我”。
事實與依據:
《卷耳》爲“婦人念夫行役而憐其勞苦之作”,而非前人所說的“后妃之志”。
證據①:從訓詁角度看,孔穎達們所說“周列”意非“周朝廷行列”,而是指“大道”。
證據②:從邏輯角度看,遵道採卷耳,“豈后妃事也”?
由此可見,第一章乃思婦因採卷耳動懷人之念,採不盈筐棄之路旁,有“一往情深之慨”;而後三章從對面著筆,想像丈夫勞苦之狀,“強自寬而愈不能寬”。
悅華按:方玉潤的貢獻在於,他首先否定了“經人解經”的做法,認爲“后妃之志”是“腐儒”斷章取義、膠柱鼓瑟之解,將“后妃”置換成“思婦”。
然後他以文學的眼光看《卷耳》,認爲後三章在寫思婦想像中的丈夫,是一種從對面着筆的文學方法。
這樣,他成功地將《卷耳》拉下“神壇”,並“抹掉”了孔穎達解說中的一個使臣“我”。
需要說明的是,餘冠英、程俊英等現代學者對方潤玉的學說有繼承,也有揚棄。以餘冠英爲例,他認爲:
這是女子懷念征夫的詩。她在採卷耳的時候想起了遠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過岡了,馬病了,人疲了,又幻想他在飲酒自寬。第一章寫思婦,二至四章寫征夫。(餘冠英《詩經選》)
程俊英也有類似的說法。比較餘、程和方潤玉的說法,區別僅在於前者認爲二三四章全是思婦的想象,後者認爲二三章中登山的是征夫“我”,而借酒澆愁的則是思婦“我”。

錢鍾書《管錐編》
- 第三場:
律師:錢鍾書(現代學者,著有《管錐編》等),律師團榮譽成員李山(當代學者,北師大教授)。
結論:作詩之人不必即詩中所詠之人,婦與夫皆詩中人,詩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
事實與依據:
首先,孔穎達們的“后妃說”迂闊可哂——哪有“求賢”而幾於不避嫌的后妃?
其次,思婦稱自己爲“我”正常,設想丈夫時再稱“我”以模擬丈夫的口吻則“葛藤莫辨,扦格難通”——既混亂又矛盾。這表明方玉潤們第二~四章言思婦設想丈夫行役之狀屬判斷錯誤。
第三,與其說二~四章是思婦爲夫代言,還不如說詩的作者在同時爲思婦、征夫代言!換句話說,詩的作者既不是思婦也不是征夫:
首章託爲思婦之詞,“嗟我”之“我”,思婦自稱也;……二、三、四章託爲勞人之詞,“我馬”、“我僕”、“我酌”之“我”,勞人自稱也。
最後,爲表明論證的正確性,大量引用中西方詩文以作類比,不僅指明這種“兩頭分話、雙管齊下”的結構方式大量存在,更指明《卷耳》爲最古老的一個。
悅華按:錢鍾書先生觀點的創新性在於他引入了“代言”的概念,一反以往後妃“我”、思婦“我”即是詩歌作者的看法。這樣,詩中的“我”無論思婦還是征夫,都只是用第一人稱指稱的對象而已。
這樣一來,解決了《卷耳》裏關於“我”的紛亂頭緒。
值得一提的是,北師大李山教授在錢鍾書先生的基礎上又提新見。
他以新發現的材料孔子評詩“《卷耳》不知人”入手,認爲《卷耳》採用的是一種歌唱方式,第一章爲女子所唱之詞,第二、三、四章,則是男子的唱詞。(悅華認爲第四章理解爲合唱之詞亦可)這樣,對錢鍾書先生觀點做了很好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