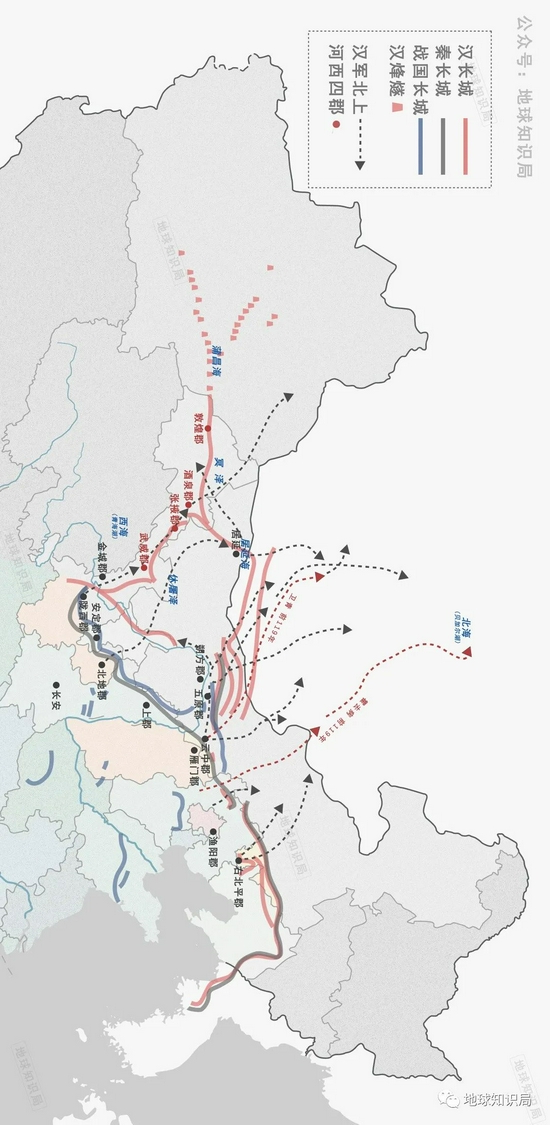辛德勇:歷史大潮中的廢皇帝還有他讀過的那些書
摘要:這樣的認識,我在考古學家把相關訊息披露不久,就於2016年9月將其寫入了《怎樣認識海昏侯墓所出疑似〈齊論·知道〉簡的學術價值》一文當中(後收入敝人文集《書外話》),後來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室裏爲什麼會有〈齊論·知道〉以及這一〈齊論〉寫本的文獻學價值》那篇文章中又基於同樣的立場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認識(文章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論》)。其實若是改換一下思維的路徑,我們還可以翻轉視角,倒過來看待這一問題:即劉賀墓室中既然另有《論語》、《禮記》等先於太史公的文獻,那麼這篇“孔子衣鏡”鏡背的銘文,就也完全有可能先於《史記》、也先於司馬遷問世,劉賀家中的衣鏡,只是照樣鈔錄一篇世間通行的成文而已。
大家好,我們的遊行俠雲遊天地又來了,今天起我們一起來分享歷史知識,也許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哦。
本文系2019年10月19日辛德勇教授在福州鹿森書店萬象裏店講座的文字稿。
我們在認識歷史問題、研究歷史問題的時候,個人依託的那個時代背景往往會比某一個具體人物個人的作爲更重要。今天我想給各位朋友講述的西漢廢皇帝、也就是海昏侯劉賀的命運就是如此。我們不管是看劉賀這個人,還是看他身後留在墓穴裏的那些遺物,都要具備一種開闊的眼光和視野,先放眼時代大背景,再聚焦於具體的人、具體的事兒以及像劉賀讀過的書這樣具體的物。
漢武帝晚年的政治作爲與劉賀的命運
談到劉賀這位廢皇帝跌宕起伏的命運,追根溯源,不能不溯及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作爲。
一些讀到《海昏侯劉賀》的讀者,往往會嫌書中直接述及劉賀的筆墨過少,同時又對這本小書一直向前追溯至漢武帝晚年感到大惑不解。其實只要靜下心來,逐次閱讀這本書的內容,我想,那些原來不理解的讀者,至少其中會有一部分人,是能夠理解其間的原委的。這就是劉賀其人的一生,是隨着他身後的那個歷史大潮飄蕩的,其浮其沉,關鍵的因素,都不在他自己,而是漢武帝晚年政治態勢向前推衍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必須從漢武帝晚年的宮廷政治鬥爭寫起。
不過天下萬事都是一件事連着一件事,歷史的敘事,也不能無限向前追溯,寫海昏侯劉賀,只能溯及與他的升降沉浮具有密切而又直接關聯的往事前因。我在《海昏侯劉賀》這本書中切入的這個開始的時點,可以簡單地用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變”來概括。
衛太子施用巫蠱之術詛咒他老爹漢武劉徹快快死去,是我在閱讀《漢書》過程中注意到的一項重要史事。當然我知道中國學術界的通行看法與此不同;或者說中國“自古以來”絕大多數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就與此不同。這些學者都覺得衛太子沒做這種混賬事兒,這是江充那個奸人對他的誣衊陷害。
如果簡單粗率地閱讀《漢書》等基本史籍的記載,確實很自然地會得出這樣的看法。然而專業的歷史學者從事嚴謹的學術研究,就不能這麼讀史籍,不能這樣解讀史書的記載。對比參閱《史記》、《漢書》諸處相關的記載,不難看出,面對隨時可能被廢黜儲位的危險,萬般無奈之中,衛太子確實是想要通過施行蠱術來促使漢武帝早一天離開人間,這樣也就離開了他的帝位,從而徹底解除對自己的威脅。
其實只要聯繫前後相關史事便可以看到,這樣的做法,在當時是很平常、也很通行的,衛太子做出這種事兒,一點兒也不足爲怪。可是當我把這一情況寫入前些年在三聯書店出版的《製造漢武帝》一書之後,很多讀者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甚至引發了比較普遍的不滿和抗拒。一些讀者以爲我只是順口胡說,並沒有做過什麼相應的功課。
在我看來,衛太子給他爹劉徹搞巫蠱這件事兒並不複雜,這本來是一清二楚的,而且漢武帝太壞了,可謂罪大惡極,咒他速死,也算得上是替天行道,是很正義的,也是我很讚賞的行爲。碰上劉徹這樣徹底集權獨裁的混蛋皇帝,誰也奈何他不得,而他又想得道成仙,長生不老,這樣,除了咒他快些死去,還能做些什麼?
申明這一事實,竟遭遇上述反響,是我完全沒有預想到的情況。爲此,不得不另外專門寫了一篇論文,題作《漢武帝太子據施行巫蠱事述說》,詳細闡釋了我對這一事件前因後果的分析。這篇文章刊出後,當然還有一些業內業外的人士不願意接受我的說法,但理解和接受的人顯然增加了很多。這篇文章,現在就附在《製造漢武帝》的增訂精裝本後面。
沒有讀過的朋友,認真閱讀這篇文稿,就能很好地理解我考察劉賀政治命運的出發點及其緣由了,就能更好地理解我爲什麼由此出發來觀察影響劉賀其人一生命運最主要的政治背景了。我寫《海昏侯劉賀》,就是把下筆的地方,定在了這裏;劉賀一生的命運,就是由這一節點展開的,也是隨着相關政事的終結而結束的。
簡單地說,在經歷了巫蠱事變之後,漢武帝劉徹的猜忌心愈加嚴重,對哪一位成年的皇子都不再能夠放心,同時他自己也更想長生久視,永居帝位,所以就沒有再立太子,定皇儲。直至死到臨頭,纔不得不指定少子劉弗陵繼位接班。這位劉弗陵,也就是後來的漢昭帝。
昭帝登上大位時,年僅八歲。如此幼齡,即使是真龍之種,連家也治不了,更不用說像皇漢那麼龐大的一個帝國了。於是,只能安排輔佐的大臣來代行其政。儘管漢武帝對此做了精心的算計和設置,讓霍光、田千秋(車千秋)、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磾五位輔政大臣各司一職,相互牽制,以防任何一人專擅權柄。然而,秦始皇開創就是一個專制國體。漢承秦制,兩千多年以來,後繼者無不依樣畫葫蘆,向下傳承的也一直是這樣的專制。專制就是專制,豈容彼等五臣共和運作?很快,霍光這位大司馬大將軍就把其餘四人清除場外,使劉家的天下任由霍氏來統管。

明萬曆刻本《三才圖繪》中的傀儡圖(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霍光先是成功地培養並操弄了昭帝劉弗陵。孰知上天不遂人願,漢昭帝這位乖乖的兒皇帝,年輕輕的,竟然在二十二歲就離世他行,迫使霍光不得不再找一個傀儡來繼續操弄。結果,就找來了劉賀,在皇朝大政的舞臺上,讓他充當和昭帝一樣的“劉氏真身假皇帝”的角色。
霍大將軍選擇劉賀來接班當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智力不太高,或者說他是個不大不小的傻瓜。一般來說,傻瓜會比人精更好擺佈一些。可後來問題就出在劉賀只是有點兒傻這一點上:傻透腔兒了纔會成木偶,隨你怎麼提,怎麼扯,而若是腦子明白的,又會按照牌理出牌,一切都可預測預防。出乎霍光意外的是,劉賀這個二傻子,竟然頭腦發熱誤以爲自己是真龍天子了,甚至串通手下,想要收拾霍光。沒辦法,霍光只好廢掉這個傻瓜再另擇他人。於是,劉賀還沒辦完當皇帝的手續(霍光刻意留一手兒,只讓他登基,而沒告訴他若是名正言順地當個皇帝,還要有一個“告廟”的程序),就被退回昌邑國王的故宮,軟禁起來。
於是,朝廷裏就又有了替代劉賀的宣帝。不過這回霍光遇到了真正的對手——是宣帝在霍光離世之後成功地清除了霍家的勢力,爲撫慰劉氏皇室成員以及天下萬民對霍光侮弄劉賀的不滿,同時又要防止劉賀東山再起,影響自己的帝位,就把他遠封到彭蠡澤畔的海昏,做了個列侯。
這就是完整的劉賀故事的梗概,他的升降沉浮,大起大落,實質上不過是隨波飄蕩,可謂成也霍光,敗也霍光。而要想追究霍光擅權的開始和結束,就不能不論及漢武帝晚年和漢宣帝中期的政局。所以,我的《海昏侯劉賀》只能從漢武帝晚期寫到漢宣帝中期,事使之然也。我覺得,只有這樣寫,才能寫出劉賀歷史的全貌和真相。
附帶說一句,讀者朋友們要是有興趣再讀讀我的《製造漢武帝》,或許對劉賀一生的命運能夠有更深刻的理解。
《史記》流佈的歷史與劉賀墓中出土的與之相關的文字
西漢這位幾乎被通行歷史教科書遺忘掉的廢皇帝,之所以驟然間引發萬民矚目,誘因是劉賀墓室的發掘,特別是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
這些文物現身於世之後,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很多專家學者在內,迅即面向公衆,對這些文物做出解析分析。這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考古新發現,激發社會公衆對歷史文化的強烈興趣,專家學者們適應社會需要及時做出回應,這樣才能讓專業的歷史學研究(在我看來,考古學和古器物的研究只是歷史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迴歸於社會,迴歸於公衆。
然而,在認識、解析這些出土文物時,學者們的做法,往往不盡相同。學術觀點的分歧是必然存在的,我講的並不是具體觀點的差異,而是認識問題的方法和途徑。具體地說,我認爲,對大多數古代文物的認識,都不應該是孤立地看待某一器物本身,而是應當儘可能地將其置於一個更大的同類事項或是相關事項的整體環境之下來看待眼前的每一件東西。事實上,清代乾嘉時期以錢大昕爲代表的那些最優秀的第一流史學家,研究每一個歷史問題時,秉持的都是這樣的態度。也正因爲如此,他們才取得了那麼輝煌的學術業績。
如果只是泛泛地說說,這樣的想法,恐怕很多人都會予以贊同。可是,這話說起來容易,動手動腳地實行起來,卻不是那麼簡單。有的人,一接觸實際,就只顧眼前,忘掉了剛纔講的那個大背景;要是爭着搶着先發表見解,就更顧不了那麼多了。另一些人,也許念茲在茲,未嘗或忘,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想做,可怎麼也做不到。因爲學者眼睛裏能夠看到多大的大背景,這是受到其自身知識面和知識量的制約的。知識面和知識量若是不足,是怎麼努着勁兒做也做不到的。
我自己的知識素養當然很差,但隨着年齡的增長,讀書畢竟比年輕時多了一些,所以近年來總是提醒自己,要努力追步錢大昕一輩學者,儘量放寬視野看問題,在大視野下去深入細緻地探究每一項具體的史事。知識儲備不足怎麼辦?哪怕現用現學,也要努力爲之。做不好也要盡力做。
下面,就讓我們本着這種基於大背景審度具體事項的路徑,來看一下劉賀墓中出土的他讀過的那些書。
在這位廢皇帝的墓室裏,出土了一大批帶有文字的竹木簡牘,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包括器物銘文在內的文字。但這些文字大多都還沒有整理出來以正式公佈,因而也無法從事進一步的研究。
在這裏,我想先簡單談一下劉賀墓中那面穿衣鏡鏡背的文字同司馬遷《史記》的關係問題,這也就是劉賀到底讀過沒讀過《史記》的問題。

所謂“孔子衣鏡”鏡背的圖像與文字
或許是與社會公衆好奇的心理有關,實際上更與學術界多年以來過分崇信新材料的學風相關,對劉賀墓中出土的各類文字,人們最感興趣的,就是那些可以與傳世文獻相互比對、同時又與傳世文獻不同的內容。
頗有那麼一批學者,動輒想要賴此新材料去“顛覆”傳世文獻的記載;同時,歷史學研究既然如此簡單,不管是誰,只要能挖出寶來,就能超越一代代嘔心瀝血的學者,獲得全新的結論,這使得社會上那些看熱鬧的,更是躍躍欲試,想要顯示一下身手。
按照這些人的想法,中國這塊土地上居住的這一人羣,世世代代,腦子都不夠清楚,總是把最好的著述棄而不留,同時又偏偏留下一篇篇胡說八道的文本。所以,在他們的眼裏,中國傳世文獻載錄的內容,真是滿紙荒唐言,一筆胡塗賬。要是世間不生盜墓賊,靠他們從地底下挖出點兒什麼,歷史就一團模糊,甚至一團漆黑,根本看不清個模樣。
或許是太期待、也太興奮了,劉賀墓發掘不久,主持發掘的楊軍先生,在一次講演中提到了墓中出土的簡牘,記者報道,便把他講的《禮記》誤寫成了《史記》。一時間人們歡呼雀躍,猶如太史公再世了似的。《禮記》這類經書,早就有過簡書帛書的早期寫本出土,像《儀禮》,武威漢簡裏還一下子就出土了長長的很多篇章。與此相比,像模像樣樣的紀事性史書,在所謂《竹書紀年》於西晉時期出土之後,卻一向較爲罕見。現在,竟然看到了紀傳體史書之祖《史記》最早的文本,喜何如之?
可我一看到這種說法就表示極大的懷疑。爲什麼呢?因爲《史記》的傳佈過程,在傳世文獻中有比較清楚的記載,而按照這樣的記載,劉賀其人是不大可能擁有這部《太史公書》的。讀過司馬遷《報任安書》的人都知道,他是要把這部書稿“藏之名山”以待能行其書之人以傳於“通邑大都”的。所謂“藏之名山”,只是個形象的說法,實際上他不過是把書稿留存給家中後人而已。這意味着在司馬遷生前,並沒有把自己這部著述公之於衆,故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裏說“遷既死後,其書稍出”,也就是說在司馬遷去世之後,世人才對他寫的這部《史記》有所瞭解,然而還是無法獲讀此書。直至宣帝時期,他的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漢書·司馬遷傳》),即這下才由楊惲把《史記》的書稿公之於世。在一定條件下,有意者始可鈔錄傳播。
按照班固的記載,這應該就是《史記》流通於世的時間起點,而如上所述,這是在宣帝時期才發生的事情。這時,被霍光趕下帝位的劉賀,已經離開了長安,或是囚徒般地被軟禁在昌邑國故宮,或居住在江南豫章的新封之地,但仍受到朝廷嚴密的監視,防止他與世人、特別是與中原來人的直接接觸。在這種情況下,他能夠獲讀《史記》,實在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們若是瞭解到《史記》在西漢時期的具體流佈狀況,就更加能夠理解劉賀接觸《史記》的機緣更是微乎其微。
在漢宣帝時期楊惲將《史記》“宣佈”於世之後,這部書在社會一定範圍內雖然有所流傳,但傳佈的範圍仍相當有限。漢成帝時,宣帝的兒子東平王劉宇,在進京來朝時,“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在《漢書》劉宇的傳記裏,記下了朝廷議處此事的經過,文曰:
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眀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逺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知曉朝廷對東平王劉宇閱讀《史記》的防範竟是如此嚴厲,就很容易明白,劉賀要想找一部《史記》讀讀,以他的身份和處境,這在當時應是一件頗犯忌諱的事情;同時我們再來看楊惲後來遭除爵罷官,被禍的緣由,即因其“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漢書·楊惲傳》),而這與他好讀太史公書顯然具有密切關係,從而可知好讀《史記》往往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朝廷對劉賀自然也要加以限制。再說劉宇身爲王爺,想討一部《史記》都不獲朝廷恩准,劉賀這位被監視居住的列侯,本身就對當朝皇帝構成一定威脅,怎麼能夠想讀《太史公書》就會輕易讀到?
雖然後來澄清事實,那次楊軍先生在講演中講的,是出土了《禮記》斷簡,並沒有提及司馬遷的《史記》,但若沒有一個合理的認識路徑,類似的問題就還會出現。果然,接下來就有很多人極力主張把劉賀墓出土衣鏡背面書寫的文字,特別是衣鏡銘文的最後一段,定爲錄自《史記·孔子世家》的內容。
今案這個衣鏡又被報道和研究者稱作“孔子衣鏡”,其背面書寫的某些辭句,同《史記·孔子世家》的文字,確有近似之處;尤其是篇末結語,同《史記·孔子世家》之司馬遷讚語高度雷同,被有些人視作鏡銘出自《史記·孔子世家》的堅實證據。但即使是按照現在研究者通行的思路那樣,一定要因爲司馬遷生年早於劉賀,就認定這篇出自劉賀墓室的鏡銘是問世於司馬遷之後,那麼,它也既有可能是取自與《史記》同源的成文,還另有可能是《史記》之外流佈於世的司馬遷的言詞。
儘管在東漢以後“純正”的儒家看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思想似乎都不夠“正宗”,但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他們就是儒生,司馬遷學《書》於孔安國且據以撰著《史記》相關的篇章(《漢書·儒林傳》),就是很具體的事證。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撰著《史記》以外,還通過其他途徑書寫或是談論到一些與《史記·孔子世家》一書相同的內容並流佈於世間,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漢武帝稱司馬遷“辯知閎達,溢於文辭”(《漢書·東方朔傳》)。班固講述漢武帝時得人之盛,也舉述說“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篇末讚語)。當時《史記》正在撰著過程之中,司馬遷的“文辭”或“文章”自然別有體現(當然也絕非觸罪之後纔寫下的《報任安書》而已),這些“文辭”或“文章”也自然會在世上有所傳播,當然世人也就會對其有所稱引,這些詞句何必非出自《史記》 書中不可!
其實若是改換一下思維的路徑,我們還可以翻轉視角,倒過來看待這一問題:即劉賀墓室中既然另有《論語》、《禮記》等先於太史公的文獻,那麼這篇“孔子衣鏡”鏡背的銘文,就也完全有可能先於《史記》、也先於司馬遷問世,劉賀家中的衣鏡,只是照樣鈔錄一篇世間通行的成文而已。如果我們考慮到衣鏡廳室陳設的性質和日常應用的功能,這樣的可能性應會更大。
實際上我們只要看一看“孔子衣鏡”鏡背的銘文,同《史記·孔子世家》還另有嚴重歧異的地方。如謂“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時,周室滅,王道壞,禮樂廢,聖德衰,上毋天子,下毋方伯,……強者爲右,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縷耳。孔子退監於史記,說上世之成敗,古今之,始於隱公,終於哀公,紀十二公事,是非二百卌年之中,……”云云(王意樂等《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刊《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這好大大一段很特別的話,就完全不見於《史記·孔子世家》,而且也不見於現在能夠看到的任何一種傳世文獻,而被人指認爲出自《史記·孔子世家》篇末讚語的那些辭句,就接在這段話的下邊。依我看這篇鏡背銘文是一篇統一的文字,前後貫穿,一氣呵成。這一情況,就已經清楚顯示出它不大可能是從《史記·孔子世家》的太史公讚語中活剌剌地剪切而來,應是另有整體的來源。假如一定要對這兩處文字做對比分析的話,我倒更覺得應是《史記·孔子世家》因襲了這篇鏡銘的舊文,而不是鏡銘割截《太史公書》。不過這是個需要具體論證的問題,且容我日後一一解說。
讀書需要識大體,首先要前後通觀,把這篇銘文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這樣的視角,其本身也可以認爲是在大背景下看具體的細節。清人錢大昕在研治史事時,就特別強調“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錢氏《潛研堂文集》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所謂“孔子衣鏡”背後這篇銘文,很短,也很簡潔,個人獨立撰述,並不困難。相比之下,司馬遷撰寫《史記》,乃是一項龐大無比的工程,因襲和裁剪、編纂舊文,自是其普遍的撰著形式,此即《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以及“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者是也。在我們考察究竟誰襲用誰舊文的可能性更大這一問題時,這應該是一個基本的立腳點。
如上所述,劉賀究竟讀過還是沒有讀過《史記》,並不僅僅是這個傻瓜到底是不是喜歡讀書和他究竟都喜歡讀哪些書這樣的“個人隱私”問題,這關係到《太史公書》早期的流佈過程,關係到《史記》文本的傳承和變遷,是一個《史記》研究中很重要、也很基本的問題。我想,只有審慎對待劉賀墓中與其相關的文字,而不是簡單地把它拿將過來,用以“顛覆”傳世文獻記載的情況,纔能保證我們更好地利用《史記》,更加深入地展開我們的學術研究。
上面講述的這些內容,前邊很大一部分,我曾經寫入《令人狐疑的〈史記〉》一文(收入拙作《翻書說故事》),想進一步瞭解敝人看法的朋友,可以參看。
《論語》文本的流傳經過與《齊論·知道》的價值
在劉賀墓出土的衆多簡牘之中,《論語·知道》這一佚篇殘簡的發現,最爲引人矚目。也正因爲這是一個十分吸引人的“熱點”,考古工作者特地很早就向社會公佈了這一消息。消息披露之後,一時間歡聲四起,一片沸騰,甚至將其譽之爲整個中國學術界乃至世界學術範圍內非常重大的發現。
其學術價值究竟重大在哪裏,歡騰的人們無暇具體說明;或者說在這些人看來,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根本毋須解說。爲什麼呢?因爲如上所述,人們認爲這是一個佚篇,是當今所見傳世文本中早已佚失的一篇。孔老夫子《論語》當中的一篇,失而復得,其價值之大,你儘管往大了想,怎麼想都不爲過,那還用專門申說嗎?
如果我們僅僅把它看作是和銅鼎磁盤一樣的古物,或者更清楚地說,把它看作是與銅鼎磁盤一樣的收藏家的寶物,那通常似乎不用再說什麼廢話:古的就是好的,有名的古物就是寶物。但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篇中國古代儒家創始人孔夫子留下的經典,這是一篇文字著述,而評價古代文字著述的價值,往往要比對古器物的評價要複雜得多,也困難得多。沉埋在地下的那些久已失傳了的古代文獻,有些東西,今天看起來好像很重要,實際上在當時卻是因其缺乏足夠的價值或是不合時宜而必然地被歷史淘汰掉的;也就是說,當時的人們是把它看作廢物的。
具體就劉賀墓室出土《論語》文本的價值、特別是《齊論·知道》篇的價值而言,我們也要和上面談過的《史記》一樣,首先要把它放到西漢時期《論語》文本流傳狀況的大背景中去審度。
西漢中期以後,社會上通行的《論語》文本,其淵源分別屬於所謂《魯論》、《齊論》和《古論》三大系統。顧名思義,隨意聯想,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魯論》是春秋戰國魯國故地傳習下來的《論語》,《齊論》則是齊國舊地傳習下來的《論語》。核諸史實,可以說這樣的想法也是對的。可是,這《魯論》和《齊論》是直接從戰國時期傳留下來的文本麼?這可不大好說。
孔門弟子傳述孔夫子的言語,並沒有實時編錄成書,或是凝結形成單一固定的篇章書名,而我們若是看看先秦典籍的一般狀況就會明白,其中很大一部分著述都是西漢以後才寫成一個凝固的文本,即所謂“着於竹帛”。這就意味着孔門弟子所傳先師的“語錄”即使早有傳本,估計也會與今傳《論語》的文本有較大的差別,況且《論衡·正說》篇還清楚記載這樣的傳本統統至“漢興失亡”。
事實上直到漢武帝時期以前,諸如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和《韓詩外傳》等書,在引述孔子的言論時,往往都只稱“孔子曰”或“傳曰”,卻不提《論語》之名,而且其中有很多內容是不見於今本《論語》的。這顯示出當時好像還沒有“論語”這個書名,世間似乎也沒有與今本《論語》類同的文本流傳。
不過也就在武帝之前的漢文帝時,“漢興失亡”的孔子“語錄”,復又重現於世,即如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所述,當時“天下衆書多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由此可知,上面提到的陸賈、賈誼等人稱述的孔子言論,即屬此等“諸子傳說”的一部分。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古論》忽地現身於世——在景帝、武帝之間,這部被祕藏在孔府宅第夾壁牆裏的用戰國文字寫成的古寫本《古論》被人發現了。這也就是所謂《古論》,亦稱《古文論語》。
這次得到的孔子“語錄”共二十一篇,基本上就是今本《論語》二十篇的內容。祗是當時的文本,是把今本第二十篇《堯曰》的後半部分另分爲一篇,或題作《子張問》(因前面另有《子張》一篇,所以人們又稱其中含有兩篇《子張》)。當時,西漢社會上似乎並沒有與這種《古論》內容基本相當的孔子“語錄”文本流傳。因爲按照《論衡·正說》的說法,昭帝時“始讀”此二十一篇古本,但直到漢宣帝時,所謂“太常博士”尚且宣稱其書“難曉”。這種情況表明,在此之前,並沒有篇幅、內容與之相當的漢隸文本,不然的話,以“今本”與“古本”相互參照,所謂《古論》是應該很容易被釋讀出來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謂宋景佑本《漢書》之《藝文志》
根據西漢末年人劉向的說法,所謂《魯論》和《齊論》是在西漢武帝以後、特別昭、宣二帝時期以後,纔在社會上被人傳習(見何晏《論語集解》之敘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論語”這一書名,也是隨着這種孔宅古本的流行而確定的。這就提示我們,武帝以後才清楚傳習情況的《魯論》和《齊論》,是不是有可能出自所謂《古論》呢?
對比《古論》、《魯論》和《齊論》的篇章構成,三者實際大體相同,其出入差別多屬所謂“章句繁省”以及篇第次序有所不同。這顯示出《魯論》和《齊論》確實很有可能是從《古論》脫胎而出。日本學者武內義雄就認爲,《魯論》和《齊論》應是兩種不同的基於《古論》的“今文”傳本。
當然《齊論》同《古論》、《魯論》相比,還有一項比較顯著的差別,這就是《齊論》共由二十二篇組成,這多出來的兩篇,一篇就是這次在劉賀墓裏發現的《知道》,另一篇題作《問王》。
從表面上看,《齊論》似乎另有淵源,可對此也能做出另外的解釋:即根據上述源流關係,我們可以把《知道》和《問王》這兩篇看作是《古論》傳入齊地以後當地學者根據其他材料和途徑新增入的篇章。
通觀今本《論語》傳佈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印證這一點的。傳世文本《論語》、亦即今本《論語》最主要的骨幹,出自《魯論》,而成帝時人張禹,是今本《論語》形成過程中最關鍵的人物。據《漢書》本傳和何晏《論語集解》的敘文等處記載,張禹本來是師從夏侯建學習的《魯論》,但後來又轉而師從王陽、庸生學習了《齊論》,因而能以《魯論》爲主而折中二本,編成定本。由於張禹曾獲侯位,世人或稱此本爲《張侯魯論》或《張侯論》。至東漢末,一代大儒鄭玄又參考《齊論》和《古論》,給這種《張侯論》做了註釋。
在這過程中,張禹和鄭玄等人,對《齊論》中的《知道》、《問王》二篇,都宛如視而不見;《隋書·經籍志》更明確稱,張禹在編定新本的過程中,乃是“刪其繁惑”,這纔“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這說明在張禹和鄭玄的眼中,這兩篇的來源或者價值一定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
這樣的歷史背景,就是我在考察劉賀墓中發現的《齊論·知道》殘簡時所要明確的一般前提和需要堅守的基本立足點。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認爲,不宜對劉賀墓室出土的《齊論·知道》抱有過高的期望並給予它超越歷史實際的評價。
其實若是能夠開拓視野,在歷史大背景下審視這位廢皇帝究竟讀到的是怎樣一種《論語》的文本,我們似乎應該更加關注劉賀墓室出土《論語》的整體情況,而不是僅僅關注《知道》這個佚篇。
劉賀在昌邑國時的王國中尉王吉,字子陽,也可以略稱爲王陽,乃特別“以《詩》、《論語》教授”(《漢書·王吉傳》)。瞭解到這一點,自然會明白,在他的主子劉賀的墓室中發現《論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更爲重要的是,《漢書·藝文志》記載這位王吉本以傳授《齊論》知名於當世,史稱“傳《齊論》者,……唯王陽名家”,也就是獨一無二的《齊論》權威,所以當年他向昌邑王劉賀“教授”的《論語》,自然就是《齊論》;在劉賀墓中發現《齊論》也就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予以充分關注的,不僅是久已失傳的《知道》這一篇章重現於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劉賀墓中若是還有《齊論》其他部分的殘簡,將會對清晰、準確地認識《齊論》的面目,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聯繫前面講述的《論語》傳世文本的衍化過程,進一步推究,還可以看到,其意義之重大,還不僅在文本來源的權威性上,而是可以藉此深入瞭解《論語》文本衍變過程中對《齊論》取捨的一些具體情況。
漢成帝時最初編定今本《論語》的張禹,本來是師從夏侯建學習的《魯論》,後來又轉而師從王吉、庸生學習了《齊論》,所以才能以《魯論》爲主且折中二本,擇善而從。明此可知,張禹所學的《齊論》既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惟一以此學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劉賀受學於王吉而寫下的這部《論語》,應與張禹從王吉那裏學到的《齊論》極爲接近。這也就意味着劉賀墓室出土的《齊論》寫本,應與張禹編定《論語》時所依據的《齊論》近乎一致——其文獻學價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瞭。
這樣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在今後的清理過程中,若是在《知道》和《問王》這兩個《齊論》獨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還可以發現其他一些《齊論》內容的話,實際上對我們認識《齊論》,認識《齊論》和《魯論》的傳承淵源以及這兩個系統的文本與《古論》的關係,認識張禹、鄭玄以後流傳至今的《論語》文本,或許會有更爲深刻、同時也更富有學術內涵的意義。相比之下,單單《知道》這一篇殘簡的發現,主要是可供我們瞭解《齊論》這一部分來源和內容的獨特性,以及張禹、鄭玄等人爲什麼對其棄而不用。總的來說,其史料價值相當有限,意義也頗爲淺顯。
這樣的認識,我在考古學家把相關訊息披露不久,就於2016年9月將其寫入了《怎樣認識海昏侯墓所出疑似〈齊論·知道〉簡的學術價值》一文當中(後收入敝人文集《書外話》),後來在《海昏侯劉賀的墓室裏爲什麼會有〈齊論·知道〉以及這一〈齊論〉寫本的文獻學價值》那篇文章中又基於同樣的立場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認識(文章收入拙著《海昏侯新論》)。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通過這兩篇文稿更爲全面地瞭解我的看法。
喜歡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說說自己的意見,我們一起來討論,分享自己的觀點,說的不對的也要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