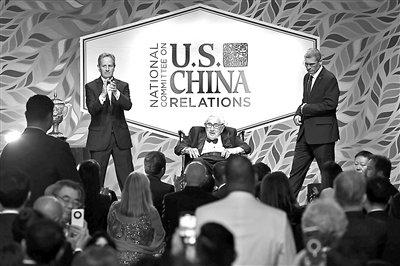基辛格對美國孤立主義的批判:歷史沒有必然性 我命由我不由天
和平不是孤立和不作爲
對於什麼是和平以及怎樣實現和平,基辛格對此有頗多的思考,當他還是一個學者時,他在自己的處女作《重建的世界》中講述了均勢平衡對和平的重要作用,按他的話來說就是“沒有平衡,就沒有和平;沒有節制,就沒有公正”。

不過在以後的回憶錄中,基辛格承認自己的理念是有些幼稚的。平衡並不是那麼容易保持的,人們往往認爲執政時間越久經驗越多的政治家能夠巧妙地控制局勢,但實際上政治家每天都被各種問題搞得焦頭爛額,光是平衡緊急問題和重要問題的次序就已經傾盡全力,所以每當遇到影響國際局勢的突發事件時,他們往往是極爲被動的。於是久而久之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學界,一種衝突宿命論油然而生,並且對整個國家的意志形成了重大影響。

當人認識到自己的侷限性時,那種無力感會很容易導致失望和怨恨。基辛格認爲這種情緒綁架了60年代末的美國,當時美國深陷於越戰泥潭中,美國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失去了幫助南越反擊侵略的道義性,不僅造成越南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也使得美國付出了3.1萬陣亡的慘重代價。美國內部因此政局動盪,暗殺、城市暴亂、精神錯亂式的抗議示威和頹廢的青年文化橫行。國際上歐洲和日本開始對美國產生嚴重的懷疑,他們認爲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國對蘇聯的綏靖和浪費精力在東南亞是一種美蘇合作的信號,一個新的“超級雅爾塔”協定將會決定兩超滅多強的恐怖局面,因此整個西方陣營惶惶不可終日。

對於年輕人對政府的激烈批評以及他們要求美國不插手國際事務的孤立主義,基辛格心中是十分惱火的,因爲在他看來這羣小屁孩什麼都不懂。他們不瞭解過去的歷史,也不知道一個帝國的衰敗是個多麼可怕的災難,如果美國當時真的就如同人們所要求的奉行完全的孤立主義,那麼美國就真的會被國際所孤立。東方有一個暗流湧動的德國,西方有一個滿心怨恨的日本,再加上被美國頻頻打斷殖民帝國復興計劃的英法,就算沒有蘇聯在對面美國也會死得很慘,這是毫無疑問的。

基辛格認爲歷史是永不停歇的,也從來沒有過什麼真正的和平時期,但從他的觀察與分析來看,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仍然是有迴轉餘地的。任何人以歷史的必然性來做擋箭牌,就是一種精神上的不負責任,人們不應該忽視力量、希望和靈感等改變歷史的重要因素,政治家不應該困於現狀聽天由命,而必須要進行鬥爭和創造,只有這樣才能帶領人民徹底改變命運。

所以基辛格認爲想要和平,美國絕不能沉迷於孤立主義並且必須要有所作爲,人們畏懼於核武器的威力而不敢去改變現狀,這是極其愚蠢的。如此下去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必將重演,災難性的戰爭終究會降臨,美國在這之前必須要學會在這種能夠互相毀滅的局面中尋找突破口,壓制對手取得平衡以實現和平。
基辛格版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爲
鄧小平曾針對國際局勢提出中國的國際戰略,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爲”。這一套理論放在70年代的美國身上是正合適的,基辛格通過冷靜的觀察與分析明確了國際局勢的動向,從而確立了明確的目標和制定了大膽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得美國在與蘇聯的對抗中反敗爲勝。

基辛格分析了之前美國所犯下的戰略錯誤,並且制定了相應的改革方案:
1、過分注重軍事力量而忽略外交手段。美國總是在過高估計蘇聯的軍事力量,爲了避免進一步衝突而選擇避讓。但這給了蘇聯發展的寶貴時間,蘇聯很快在軍事力量上追上了美國,而這個時候美國卻反而要使用自己並不佔優勢的軍事力量企圖壓倒對手。如果美國想要這麼做,就應該在二戰結束後立即利用核優勢逼迫二戰傷亡兩千萬人的蘇聯就範,從一開始就避免冷戰的出現。
現在覈均勢已經誕生,那麼美國就應該採用外交手段來調整策略,而不是濫用武力空耗自己的國力。美國建國之初的政治家們非常善於使用歐洲那樣的均勢外交手段,保護弱小的美國不被牽扯進歐洲強權的鬥爭中獲得了近長達一個世紀的平穩發展期,美國必須重拾這種能力來韜光養晦實力,並給對手製造麻煩爭取時間。

2、美國忽視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很重要的力量。當時廣大的亞非拉國家擺脫殖民統治者紛紛獨立,一個廣大的第三世界成爲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然而美國在第三世界當中遠不如蘇聯受歡迎,即使是不結盟運動國家也傾向於共產主義,因爲共產主義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思想旗幟鮮明深受第三國家的支持。儘管美國也提倡反殖民主義,但是其參與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以及與西方殖民國家站在一起的做法遭到了廣泛的懷疑和批評。

此時的美國已經深刻地認識到意識形態對於國際關係的重要性,於是爲了擺脫自己的孤立局勢,美國必須將他的那一套“民主自由價值”推行到第三世界當中去。這一點美國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這幾個東歐國家身上看到了希望,蘇聯允許這幾個國家舉行自由選舉,結果共產黨都遭到了慘痛的失敗,因此基辛格認定這種現象是可以利用的,而後來所發生的種種“顏色革命”也印證了基辛格和其他美國戰略家的想法。

3、美國濫用武力而放棄了自己的經濟優勢。美國一直在經濟上保持着對蘇聯的絕對優勢,這是美國最有用的武器,而美國卻缺乏戰略思想沒有將其武器化。基辛格認爲通過經濟全球化,讓美國經濟主導世界進而遏制蘇聯是最爲行之有效的辦法,於是他開始了著名的“穿梭外交”,通過經濟利益遊說各國合縱連橫。
這其中最爲關鍵的經濟“戰役”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機,當時美國與蘇聯爭奪中東的主導權,誰能拿下中東便能問鼎世界的霸權。原因無他,就是因爲世界各國都需要通過工業化來實現國家崛起,而石油是工業的血液,沒有中東的石油想要實現復興無異於癡人說夢,這就是中東地區如此炙手可熱的主要原因。

廣大的中東和北非地區人民是傾向於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反帝反封建的世俗化似乎不可阻擋,這讓長期與英國殖民者同流合污的阿拉伯封建統治者寢食難安。1969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剛剛掌權不久就出訪了科威特,當時基辛格滿以爲科威特酋長會因爲巴以問題而向尼克松表示抗議,然而令基辛格驚訝的是科威特只關心英國撤出中東後美國對中東局勢的態度如何,如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會不會出手。
此時基辛格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中東這羣阿拉伯國家的封建統治者們只關心自己的統治利益,他們十分擔心像伊拉克和埃及這種蘇維埃共和國將來剝奪了他們的權力,與之相比什麼宗教、什麼民族大義統統都是浮雲。

於是美國勾結以色列、沙特和伊朗策劃了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傻乎乎地跟着沙特一起減產石油造成了世界石油危機,結果自己在世界石油市場的份額被削減了。沙特和伊朗王室配合西方石油七姐妹大賺了一筆,他們還獲得了進入美國華爾街金融圈的權力,這樣石油美元體系就建立了起來,實質上就是美國與沙特、以色列的三角同盟。

石油美元體系的建立讓歐洲和日本遭到沉重打擊,他們剛想趁着美國越戰虛弱擺脫控制,結果脖子上又被栓上了鏈子,能源和金融這兩道鎖再也無法扯斷。阿拉伯地區最親近蘇聯的伊拉克、敘利亞、埃及和巴勒斯坦遭到以色列的痛擊基本上喪失了再次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加上埃及隨後的叛變行爲,蘇聯在中東的戰略基礎已經被動搖。

整個第三世界因爲短期內的石油暴漲而導致外匯賬戶破產,他們不得不接受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援助”,當美元和“民主自由”源源不斷地進入這些第三世界國家時,他們就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再無法保持自己的獨立意志,逐漸淪爲西方的新殖民地。

而可笑的是蘇聯完全被石油危機的假象所矇騙了,蘇聯以爲這下美國的西方陣營要崩盤了,自己還能借助石油價格上漲狠賺一筆。結果錢是沒賺到,整個世界的局勢已經開始轉向不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了,在中東被遏制住之後,蘇聯只能選擇親自下場從阿富汗向南實現出海口的突破,結果就是陷入基辛格精心編制的大網之中直至慘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