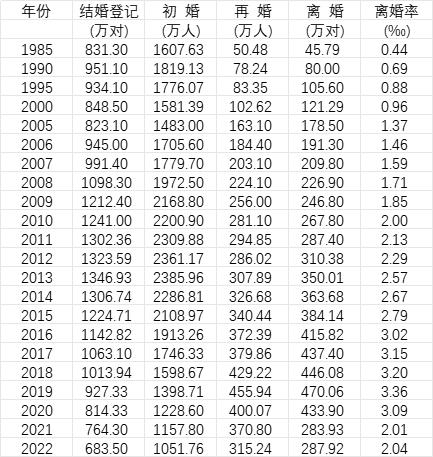宋小女曾每天工作20小時:晚上咬着嘴哭 過得狗一樣
(原標題:宋小女的傷)
8月5日,南昌,張玉環接受媒體記者電話採訪。紅星新聞 王勤/攝 人民視覺供圖
27年終於過去了。時間在宋小女身上留下的印跡清晰可見。黝黑的皮膚是被海邊太陽曬出的,右手虎口處的老繭則是殺魚廠的剪刀留下的。1993年,前夫張玉環因被指殺害同村兩孩童而入獄,從那以後,宋小女就沒過多少安穩日子。
她現任丈夫以打魚爲生,和她租住在離海邊不過一兩百米的房子裏。她曾在殺魚廠工作,每天拿着剪刀從凌晨4點工作到夜裏12點。她邊打工邊爲前夫申冤,小兒子7歲前對她沒有印象。
宋小女患有高血壓,得過宮頸癌,手術後,人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現在藥物的副作用又讓她有些虛胖。
自從張玉環被關押起,她便很難整晚安眠。8月4日凌晨4點多,50歲的宋小女從淺睡中醒來。這一天,被羈押9778天的張玉環無罪釋放。
她想要前夫的一個擁抱,“非要他抱着我轉”。兒媳婦問她,面對那麼多媒體咋有勇氣那麼說。“我那時眼裏完全看不到媒體。”她說,“如果張玉環在我身邊,他看到我(喫的苦),他肯定會抱我一下。所以這個抱對我來說好有意義,我不騙你。”
張玉環出事後,她發現和張玉環的合影只有結婚時拍的一張。從此她對拍照近乎成了執念,每次打工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帶着兒子去照相館照相。而今,她要把8個人——兒子、兒媳、孫子、孫女完完整整地“還”給張玉環。“這8個人過得都很辛苦,一步一個腳印,誰也想象不出來,這麼多年究竟是怎樣過來的。我希望他可以好好珍惜。”
1997年,宋小女和兩個孩子的合影。
但是,那個擁抱,宋小女還是沒等到。爲了給見面那一刻做好準備,宋小女喫了兩倍劑量的降壓藥,張玉環下車走向人羣那一剎那,她還是暈了過去。她躺在外間的一把舊椅子上,紅着臉喘着粗氣見證這場重逢。
很多天後,她的鼻子下面還留着指甲掐痕,咽喉處有一大塊紫色的痧痕。那是當天的搶救,在她身上又留下的一處傷痕。
1
並不是所有傷痕都足以示人。比如,宋小女幾乎不向外人提及左手腕上表盤大的疤——在深圳打工時,她自己用菸頭燙的,她想念兒子和丈夫,“白天打工,晚上咬着嘴巴哭,過得跟狗一樣”。
“小女”是“幺女”的意思。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兒。張玉環被捕那年她23歲,此前的人生,她從沒爲生計憂慮過。因爲身體不好,她一年級讀了4年,偶爾幫家裏放牛。嫁到張家後,張玉環包攬了春種秋收的幾乎全部農活,農閒時,他去上海、福建兩地做木工活,到縣城裏拉板材,打零工。家裏的柴米油鹽、人情往來也都是張玉環負責操持,宋小女覺得自己“被寵得像女兒”。
這樣的生活持續到1993年秋天。那年10月27日,26歲的張玉環作爲嫌疑人被警方帶走。那時,家中兩個兒子一個3歲,一個4歲。
一家四口從那時起分在四處:張玉環在看守所,大兒子由奶奶照料,小兒子在交給外公,宋小女外出打工。此後的26年,這個“家”再沒完整過。
受害者家屬把怒火發泄到張玉環母親張炳蓮和妻兒身上。“來我家搶走糧食,往房子裏扔石塊,一塊就砸中了我的頭。”宋小女回憶,爲了躲避報復,她聽了婆婆的話,帶着兩個兒子回到孃家。年邁的父親已經由哥哥們輪流贍養,她和兒子便隨着父親在各家“流浪”。
“殺人犯家屬”在村裏像過街老鼠。宋小女昔日最要好的姐妹見到她都會扭頭繞行。實在難過時,她會獨自跑到山上哭一哭。
在南昌打工的兩年,歇工時宋小女就往省公安廳、政法委、法院跑,不認識路只能打車,她心疼“花了很多冤枉錢”。
爲了省錢,坐在出租車裏,她老遠就開始張望單位名字,看到後立刻要求司機停車,她自己走過去。
一次,工作人員被她問煩,說“一個女人家,這裏跑那裏跑,難道家裏沒有男人了嗎?”
“我家的男人一個8歲,一個7歲,可以嗎?”宋小女說。
張寶剛記得兄弟倆和母親去申冤的經歷。母子三人走累了坐在馬路邊上,邊歇腳邊喫東西,有人路過,把錢放在他們面前。
有時在家裏她會忍不住邊哭邊發火,“放張玉環出來,讓我進去,我們換一下!”
2
張玉環被逮捕的第一年,宋小女帶着孩子隨父親在哥哥家喫住。她變得敏感,總覺得哥嫂吵架與他們母子三人有關,“家裏都有孩子要養,誰家能多添3張嘴。”
他們搬到張玉環的大哥張民強家住過一段時間,嫂子幫她置辦一個小菜攤,但因爲宋小女心裏裝着事,賣菜時總倒找人家錢,這個營生也很快結束。
等到第二年,宋小女隨返鄉招工的親戚南下打工。她第一次經歷與孩子的骨肉分離,忍受“錐心的疼痛”。從1994年到2002年,母子三人團聚的時刻屈指可數。
打七八歲起,兄弟倆經常要凌晨三四點起牀跟着張炳蓮下地幹活,按時節種水稻、芝麻、花生、玉米,“田裏的水沒到大腿”。張炳蓮捨不得用除草劑和肥料,自家地裏的玉米稈比旁人的細了好幾圈,祖孫三人每天都要去地裏拔草。
除了幹不完的農活,張寶剛和哥哥經常受到欺負,在張家村“沒有一個朋友”。張寶剛見過有幾個小孩把哥哥按在地上打,向他嘴裏塞牛糞讓他嚥下去。
宋小女的弟弟宋小小告訴她,村裏有人說,兩個孩子這樣都不死,“是老天都嫌棄,不肯收他們。”
兄弟倆淘氣或偷懶的時候,沒少挨張炳蓮的竹竿。張家門口有一棵“祖傳的樹”,張玉環的弟弟小時候捱揍後爬上樹睡,後來輪到張玉環的兒子。再後來,豬圈、菜地他們都睡過,“像兩個野人”。
兄弟倆幾乎沒穿過新衣服,褲子是撿來的,掛着補丁。餓肚子時靠紅薯黃瓜和野果子充飢。學校組織打疫苗,需要要交錢的那些,他們一針都沒打過。
他們不會和母親提起這些事,“因爲提了也沒用。”張寶剛回憶,“她很久纔回來一趟,也只待一兩天。”
“哪個母親聽了不心疼?他們兄弟倆喫了多少苦。”二兒子12歲時便跟宋小女去西安打工,15歲時獨自去廣東闖蕩。宋小女愧疚當年沒有能力讓兩個孩子多讀一點書,但是她沒辦法。“不打工,3個人餓死,出去打工,我們還有條活路。”
宋小女與張玉環母親、兩個兒子的合影。
她給孩子寄自己織的毛衣,雖許久見不到孩子,但大小總是合身;她把工資分成三份匯回家,兩個孩子的生活費和學費,還有一筆要攢下爲張玉環上訴。
她在深圳打工3年沒回一趟家,1997年,張寶剛在外公的葬禮上才第一次見到媽媽。這是宋小女離家3年後第一次回來。她在生日時特地打了耳洞,和工友一起淘一些香港那邊來的二手衣服,喇叭褲、泡泡袖和大波點襯衫,“不能讓村裏人看不起”。
3
張玉環入獄的第六年,宋小女的身體垮了。她得了子宮肌瘤,醫生建議她做手術。這個女人不懂這個病,但“瘤”這個字讓她感到恐懼。“我兒子已經沒有父愛了,如果我再從手術檯上下不來,他們太可憐了。”
她因此才決定改嫁給現在的丈夫於國慶(化名)。那是在1999年,她向對方提出結婚的三個要求,一是要對兩個孩子好;二是她隨時能去見張玉環,不能阻攔;三是要能去看張玉環的母親。
改嫁後,宋小女隨於國慶到福建打魚。於國慶也帶有一子,五口人組成了新的家庭。
丈夫是弟弟宋小小介紹的。決定嫁給他之前,宋小女從弟弟口中得知了於國慶對亡妻的態度——前妻得了白血病,他賣了農村人視爲命根子的牛,到處借錢給妻子治病;醫生說沒救了,他仍堅持身上只留下幾毛錢的路費,剩下的錢都花在妻子身上;彌留之際,妻子囑咐他,治病花了太多錢,自己死後就不要棺材了,用草蓆裹就成。
“我們就是兩個苦命的人抱團取暖吧。”宋小女向於國慶說,“我忘不了張玉環的。”
20年過去後,她與於國慶再也拉扯不開。颱風天,宋小女只能通過衛星電話得到丈夫要回來的消息,不知道他能不能在臺風到來前到家。她每天都會站在窗口焦急地等。於國慶出海回來,會跑去殺魚廠幫宋小女請假,遞煙陪笑讓領導准假,然後帶她出去玩,順便喫點好的。
一次,於國慶在船上幹活時斷了一隻手指,送到醫院時人還處於昏迷狀態。宋小女心疼得一直掉眼淚,醫生告訴她,可能需要手術植皮。她當即伸出胳膊,扯着嗓子哭道“從我這裏割,割我的肉”。
但她還是惦記張玉環。她曾對着於國慶喊“張玉環”。兩人爲此生過氣。看到丈夫難過,宋小女也難過,但惦記前夫成了一種生活習慣,她高興時會想,難過時也會想,生活切換到任一場景,她會想,要是張玉環在會怎樣。
丈夫和兒子出海後,她在家門口的殺魚廠打工。丈夫擔心她辛苦,勸她回家帶孫子算了。她不肯,她想辛苦兩年一鼓作氣把在江西老家的房子蓋起來。房子蓋在丈夫的村子,宋小女告訴自己的兩個兒子和兒媳,這個房子“沒他們的份”。
2012年,宋小女做了宮頸癌手術。手術前,她最後一次去探望張玉環。她哭着問,“我已經是要死的人了,你最後再告訴我一次你到底做了沒有?我等也等了,該做的也做了,我被折磨得太難過了,我不想活了。”
“張玉環說真的沒有,他是冤枉的,他讓我一定活下去。”宋小女回憶。
手術前後都有波折,於國慶先開導動了自殺念頭的她,又忙前跑後地照顧。
“這件事之後,我覺得我該給他(於國慶)一個名分。”那一年,宋小女與張玉環簽了離婚協議。
張玉環無罪釋放後,她在現場被救護車拉走的畫面被丈夫看到。丈夫坐了火車連夜趕到南昌。
她渴望一個抱的視頻也在網上傳開,她不擔心自己的形象,但是怕於國慶難堪。在後續的採訪中,她會反覆表達對現任老公的愛和感謝。
她最近幾天都在圍着張玉環忙活。有記者把電話打到她手機上,想採訪張玉環。她把手機遞過去,掐着時間,觀察張玉環的表情。張玉環露出疲態她立即搶過電話中止採訪。“還是忍不住想保護他。”
“張玉環對我那麼好,所以我就義無反顧的。爲他喫的苦,我心甘情願。”但宋小女表示,自己不會回到張玉環身邊,她要去加倍疼愛現在的丈夫,“因爲他爲我們母子三人付出了太多”。
4
張玉環入獄後,宋小女添了兩個“毛病”:失眠的時候喜歡用被子矇住頭,這樣“有安全感”;喜歡拍照,而且把最喜歡的照片都放到微信收藏夾——手機相冊裏的照片和小視頻太多了,找起來困難。
每次打工回來後,宋小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着孩子去照相,以至於後來看相片時她會懊惱,爲什麼不給孩子買套衣服再去拍?一張在冬天拍攝的照片裏,兒子上身穿着她給織的毛衣,下面是一條打着幾個補丁的單褲。
張玉環兩個兒子的合影。
她後悔自己和張玉環的合影只有一張,而四口人連張全家福也沒有。張玉環入獄後,她時常摩挲那張照片,照片的左上角已經褪色發白,她趕緊去照相館翻印幾張。
拍的照片她通常會洗三份,一份自己帶在身邊,一份放在張家,還有一份隨她探視的時候帶給張玉環。
1998年拍的一張照片,張寶仁閉了眼。他在照片背後用圓珠筆寫了兩行字,“爸爸你好:爸爸我這次照相,沒照好,請原諒。等你回家來我們再一起照相。”落款處有他的名字,日期是4月19日。
張寶仁在照片背面給父親留言。
27年裏,張玉環一共收到過17張照片,這是他能捕捉到家人變化的全部痕跡。
在獄中,他沒有停止申訴。據《南方人物週刊》報道,張玉環剛到南昌監獄服刑,被分去做衣服,因不服判決,他用剪刀把做的衣服全部剪掉,被管教罰禁閉。哥哥張民強知道後,一邊安撫他,一年繼續和他一起申訴,“我們就寫給最高院、最高檢、全國人大、中央政法委,一個禮拜寫一封,四個地方都寫一遍,一個月就過去了。”張玉環在監獄裏面一週寄一封,張民強在外面也同樣,一直到2017年。
2016年,江西樂平姦殺案再審。原告被改判無罪。這讓一直申訴的張民強看到了希望。
同樣關注此案的還有曾在附近北嶺林場工作的醫生張幼玲。他聯繫江西的一位記者,又找到報道樂平案時結識的律師王飛和尚滿慶。
宋小女是在福建得知有記者關注張玉環的案子,她立即定了回江西的票。接受完採訪,她覺得“張玉環有救了”。回到福建,在飯桌上她突然想到此事,先是大哭,然後笑到停不下來。“瘋了,我老公說。”那天,她最終被家人帶去醫院打了鎮定劑。
2018年6月,江西省高院對“張玉環案”立案複查,2019年3月份決定再審,2020年7月9日進行公開審理。8月4日,江西省高院宣判張玉環無罪。
8月7日,大兒子租了一輛車,將妻子和弟媳以及所有的孩子接到南昌團聚。
宋小女起初的想法是,把兒子兒媳和孫子孫女八口人留給張玉環,讓他享受天倫之樂。但他們發現租一套“裝下這麼多人的房子”太貴了,而且8月15日要開海了,兩個兒子的收入是兩家的全部經濟來源。
“我突然覺得不能這麼做,我不能讓我的孫子像我兒子小時候一樣漂泊。”宋小女決定聽從大兒子的決定:老大家先返回福建掙錢,老二家留下來陪父親。
那個擁抱沒有實現。有記者提議爲他們補拍一張擁抱的照片,因爲那是宋小女“幾千遍幾萬遍想的”。但是這次,宋小女拒絕了。
“沒有了。”她笑着說,自己等了27年,因爲(見面時)“沒有抱”,所以張玉環永遠欠我一個擁抱。
張玉環隨兒子搬進了縣城老城區內的出租屋。房子在六樓,30多年前就矗立在這,張玉環對這一片相對熟悉。
他在努力適應新事物——空調遙控器、手機怎麼擺弄,物價怎麼這麼高。依然有記者每天登門,這讓他有些疲憊——與人交流時,他總要思考一下才能回應,有的問題需要記者掰開揉碎解釋。
8月11日,宋小女和丈夫於國慶啓程回福建,她要去醫院查下卵巢裏新長出來的瘤子。
她在社交平臺上感謝了律師、記者和網友。“我走了,帶着酸甜苦辣,我回家了,願自己餘生安好。”寫完,她在結尾加了3個感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