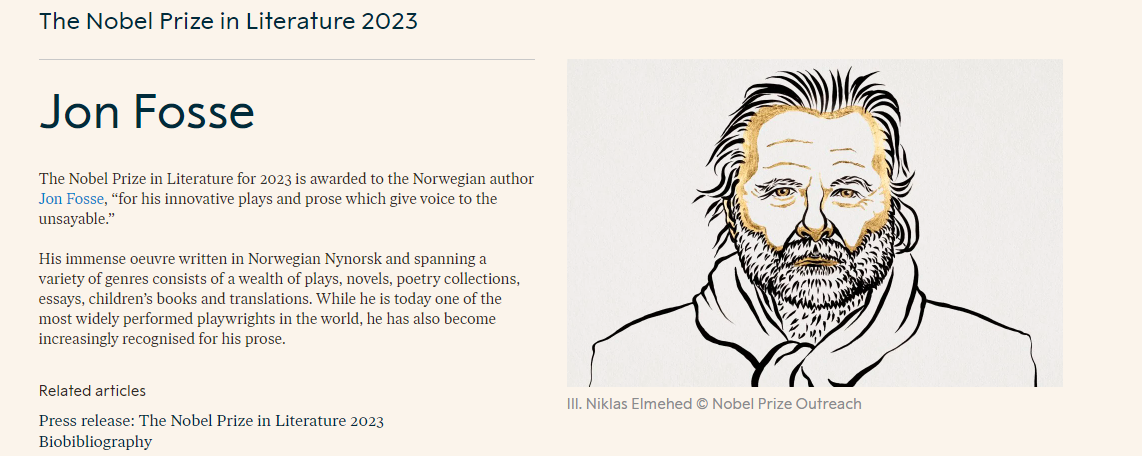女詩人獲諾貝爾文學獎後:我不會有任何朋友了
(原標題:女詩人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反應太真實了)
摘要: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不會有任何朋友了”,因爲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是作家。
“這消息太新了……我真的不知道它意味着什麼。”
在被告知自己獲得了202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後,露易絲·格麗克(Louise Glück)接受了諾貝爾獎團隊的電話採訪。
露易絲·格麗克獲得了202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不會有任何朋友了’,因爲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是作家。”格麗克說,“但最重要的是,我關心的是保護我愛的人的日常生活。”毫無心理準備的她,在諾貝爾獎團隊的再三請求下,答應在兩三分鐘裏簡短回答幾個問題。
她建議新讀者從她的任何作品開始閱讀,“因爲它們都非常不同”。她提出,從她近期的作品《Averno》開始讀是個不錯的選擇,或者是她的上一部作品《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但她不推薦新讀者從她的第一本書開始讀,“除非他們想要感受到蔑視!”
格麗克對於現在的處境感到不適。10月8日,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經公佈,記者們紛紛趕來,站在她位於馬薩諸塞州的家外面的街道上。她的手機從早上7點開始就一直響個不停,她形容這種猛攻是“噩夢般的”。
“在我的一生中,要處理這種特殊事件似乎是極不可能的……我不喜歡採訪,但這並不意味着我是一個隱居者。”露易絲·格麗克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這樣說道。
到目前爲止,格麗克應該已經習慣了讚揚。在長達5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她出版了十幾本詩集,獲得了幾乎所有著名的文學獎項:美國國家圖書獎、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評論家獎和國家人文獎章等等。
在白宮,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擁抱格麗克,並授予她2015年美國國家人文獎章。
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Anders Olsson)表示,她的寫作特點是力求清晰,關注童年和家庭關係的主題。
他強調,儘管她的自傳背景很重要,但她並不是一個自白的詩人,並將她與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相提並論。奧爾森指出,格麗克的作品尋求普遍性,她從神話和古典主題中獲得靈感。
格麗克因其簡潔、直接的詩歌而受到文學評論家和同齡人的尊敬。
“她的作品就像是一場內心的對話。也許她在自言自語,也許她在跟我們說話,這有點諷刺。”她的老朋友兼編輯喬納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說,他是Farrar, Straus & Giroux出版社的董事長,“在她的作品中,有一樣東西是永恆不變的,那就是內心的聲音。她總是用自己的經歷和某種無法匹配的理想進行對比。”
過去的幾個月對格麗克來說是一種考驗。格麗克已經離婚,獨自生活。在疫情爆發前,她已經習慣了每週有6個晚上和朋友出去喫飯。在春天的幾個月裏,她努力寫作。在今年夏末,她又開始寫詩,並完成了一本名爲《冬季集體食譜》(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的新詩集,計劃明年出版。
“我們希望,如果你能挺過這段時間,就會獲得藝術。”她說。
延伸閱讀
女詩人未死,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她意味深長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作家的根本體驗是無助——我有意使用了‘作家’這個詞,‘詩人’這個詞必須謹慎使用;它命名的是一種渴望,而不是一種職業。換句話說:不是一個可以寫在護照上的名詞。”——路易斯·格麗克
20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桂冠被美國女詩人路易斯·格麗克摘獲,當地時間10月8日13點,瑞典文學院公佈獲獎者時,宣稱其獲獎的理由是:路易斯“無可挑剔的詩意之聲,以樸素的美感使個體的生存變得普遍化”。
這是個對大部分中國讀者都陌生的名字,在世界範圍內也相對小衆。就在諾獎揭曉前一分鐘,“路易斯·格麗克”都還落在英國博彩公司的預測賠率榜單相當靠後的梯隊,一天前甚至久久維持在第21位,在她前面的候選者包括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常年陪跑的村上春樹,及我國的閻連科、殘雪、餘華等人。
2020年的諾貝爾獎項註定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文學獎尤甚,不僅因爲文學本質上是關於人的藝術,更因爲在災難年代,藝術更應擔起一定的祛魅和吶喊功能。吶喊也許是無聲的,就像一部電影短暫留白的三秒鐘,僅僅是那三秒鐘,滲透了人心裏,狠狠地揪起了人們的思維和靈魂。
而這次獲獎的是一位詩人——不同於相較依靠敘事支撐的小說和戲劇,詩,這一文學形式的魅力,在於予人一瞬間的觸動,那觸動甚至可以是不可說的,它就那麼精準地、分毫不差地刺入人心,讓語言、詞句全部被碾碎、再得到一次全新的重構。
這是個極其具有魅惑力和危險性的工作,那些聲揚着“詩人已死”的“文藝實幹家”們,保不準這會兒或許正在原地跺腳,爲諾獎的“荒謬”而咬牙切齒呢。而路易斯的悄然闖入,難道只是爲了給這個不平靜的2020,讀一首詩嗎?
01
女詩人未死
現年77歲的路易絲·格麗克出生於紐約一個匈牙利裔猶太人家庭,自2003年起,她在馬薩諸塞州的威廉姆斯學院講授一年級英語、詩歌寫作和當代詩歌等課程,迄今爲止已出版了9本詩集,其中1992年的《野盞尾花》曾獲得1993年的普利策獎。
(路易斯·格麗克)
在西方文學界,路易斯被冠以“自傳體詩人”的稱號,且被譽爲美國的“必讀詩人”。其詩作擅長刻寫對心理幽微之處的把控,以細膩的感情、個人的生命經驗,從神話、人類歷史中汲取靈感,架構一種與現代社會脈絡的獨特銜接,晚期作品更通過透視人與神的奇妙聯結,抵達愛、死亡、毀滅與重生等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
初讀路易斯的詩,的確會明顯捕捉到大量所謂女性主義基調,雖然這是她意圖避免的,大部分直白的書寫來自她自身的成長、情感經歷,關乎女性獨特生命體驗的抒情。
“我的身體不是得救了嗎,它不是安全了嗎
那傷痕不是形成了嗎,無形的恐懼和寒冷
它們不是剛剛結束嗎……”
“我越是躲着不看她們的痛苦
它越是像我們家族的命運:
每一家都向大地獻出一個女孩。”
諸多私人化的敘述和抒寫,都將個人的生命體驗轉化爲詩歌,其中罕見幸福和愛情,而是幾乎字字都飽脹着沉重與沉痛。譬如:不少人聽過《格林童話》,路易斯卻對裏面一則《漢塞爾與格萊特》的故事做了新解——結局雖然與任何一個童話一樣皆大歡喜,但人物面臨的種種威脅、恐懼鮮活地存在着。
路易斯自童年起是個“孤獨的孩子”(2006年訪談言),童年時經歷過二戰餘創,青春期時患上厭食症,兩次入學、兩次輟學,後來又經歷兩次失敗的婚姻。她在出版於1968年的第一本詩集《頭生子》裏,用一種飽含少女之思與少婦之痛的情調描摹悲楚:
“總是在夜裏,我感覺到大海/刺痛我的生命”(《雞蛋》III )。
熟悉現代詩的人或許感受得到,這兩句頗有193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葉芝的味道:
“我就要動身走了,因爲我聽到那水聲日日夜夜輕拍着湖濱”
(愛爾蘭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
也讓人想起我國詩人海子:
“豐收後荒涼的大地,黑夜從你內部升起。”
據《哥倫比亞美國詩歌史》文獻的記述,從1980年的組詩《下降的形象》開始,路易斯將自傳性材料揉入她淒涼的口語抒情詩裏,大多取材自親歷的家庭生活,如姐妹關係、父母關係、喪親之痛等等。
其作大多關於生死、愛和性,這些文藝創作者們屢用不爽的元素,越是老生常談,就越能考驗一個詩人的文學造詣。
從路易斯的第一部詩集開始,“死亡”就以或顯或隱的形式反反覆覆出現:
“聽我說完:那被你稱爲死亡的
我還記得。
頭頂上,喧鬧,松樹的枝杈晃動不定。
然後空無。微弱的陽光
在乾燥的地面上搖曳。”
路易斯娓娓而來的全是日常生活與經驗世界,可感可觸,卻有一種難得的質量——從個人體驗出發,於細微之處將個人的觀察、體驗露骨地伸展開來,正如她在中國的主要譯者柳向陽評價其詩像“錐子扎人”,然後逐漸蔓延至深耕大地,擁攬自然、宇宙入懷,不可謂不廣大、深髓。
1992年獲普利策詩歌獎的《野鳶尾花》成爲路易斯最廣受世界讀者傳閱和喜愛的詩集。相較於早年的私人化、情感化寫作,她從這裏開始有意識地轉向死亡和生存的抽象性問題,探討伴隨死亡的恐懼、威脅、人類內心的茫然和猶疑。她大面積借用《聖經》裏的素材,在西方文化背景和典故里關注挫折、幻滅、希望、責任。
《晚禱》:
我認爲我不應該被鼓勵
去種植西紅柿。或者,如果我被鼓勵,你就應該
停止暴雨、寒夜……
不少當代文學評論家都分析認爲,路易斯的創作圖式、肌理始終處於某種重複和變動的張力之中,以寓言的形式對世界實施判斷,將表象的現實秩序化,向人類生存狀態進行文化思考、自然野性方面的觀照:
“記不起從另一個世界來路的你,
……從忘卻中返回,都回來,
發現了一種聲音:
從我生命的中心湧出
巨大的泉流,湛藍的
在海面上投影。”
不同於風格各異、形式無窮的小說家們,受歡迎的詩人倒有着某些共性,比如採用儘量簡潔扼要的詞,忌諱辭藻雕飾,現代詩往往轉向口語化等等。路易斯則曾在演講中強調,讓她着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種可能性”:
“我所回應的是一首詩如何藉助一個詞的安排,通過時間設定和節奏的微妙變化,解放這個詞的豐富而令人驚訝的意義分佈區。對我來說,似乎簡單的語言最適合這種創新事業;這種語言,作爲一個類別,其個體詞語的內部往往包含最大、最戲劇化的意義變化。我喜歡刻度,但我喜歡它變得無形。……我爲之吸引的那種句子,是反映了這些心靈趣味和本來習慣的句子,是悖論,它具有的增強的優勢能恰到好處地將固執的本性從一個正變得過於道德化的修辭體系中挽救出來。”
這或許也是值得借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牽引出的另一個思考:文字,詞語,它們永遠是我們敘述這個世界的方式,甚至可以說,某種意義上,敘述扮演着對這個世界的一種支配和掌控的權力。
時至今日,語言在人類社會扮演的角色被重構。虛擬與真實、表意與譬喻,種種對人類語言文字的玩味、變質,都在不斷折騰着由歷史承襲而來的語言魅力,而折騰,未必象徵着進步。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加·託卡爾丘克)
去年,201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託卡爾丘克就在獲獎演說中警示人們,“世界快死了,而我們沒有注意到”。
今天世界缺少講述故事的新方法,缺乏具體的語言、視角、隱喻、神話和新的寓言。語言的靈性正在消失,或變得膚淺和儀式化。與此同時,文學市場的商業化、市場與互聯網的控制,使得創作脫離了本質,混亂、真假難辨的信息讓讀者失去了對虛構的信任,小說和文學變得邊緣化。
“世界的低語被城市的喧鬧、電腦的嗡鳴、飛機飛過天空的震聲與信息汪洋令人疲竭的噪音取而代之。我們被包圍在單個小氣泡中,創造出許多彼此不兼容甚至公開敵對,互相對立的故事。”
從這個層面來看,路易斯·格麗克的“被看到”,更像是一股必然的清流,是對文學之根——語言本源發出的警鐘與戀歌。
02
諾獎是文學的禮物,而不是標準
在二戰之前,諾獎某種程度上一直代表着西方人看待世界的一種視角,大部分桂冠都是頒給歐洲人的,而近幾年來,諾獎文學獎得主分別蔓延到奧地利、北歐、俄羅斯及東亞文化地區,從高行健、莫言等人的獲獎,也可看出瑞典文學院正在有意識地讓頒獎在地域上平衡,石黑一雄、鮑勃·迪倫等人的獲獎,也昭示出諾獎評委正逐漸青睞具有開創性的文學議題和形式,同時也開始更多注意到女性作家崛起的聲勢。
(2018年,瑞典文學院院士卡塔琳娜·佛洛斯登松的丈夫讓·克勞德·阿爾諾被指控性侵犯和泄漏諾獎評選結果,這一風波導致2018年的頒獎被推遲到2019年)
在201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公佈之前,評審團主席安德斯·奧爾松就曾公開表示:2019年的獎項將會“開拓我們的視野”,扭轉這個獎項長久以來的“歐洲中心主義”與“男性主導”的頒獎傾向。
到2020年,這一趨勢只會愈加明顯。尤其是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團遭遇2018年的性醜聞風波後,世界有理由認爲,瑞典文學院這些年的授獎,極可能頒發給一些相對“保險”、具有相當聲望的作者,以維持諾獎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同時有意識地增加女性作家、亞非作家在整體獲獎者比例上的分佈。
路易斯的獲獎,一方面當然是名至實歸,另一方面,也貫徹了一個世界級文學獎項的意義:讓那些在某一領域有着長時間深度積累和傑出貢獻、但相對小衆的人,被全世界更多人看到。就像去年的彼得·漢德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其作品迅速在世界範圍內被轉譯、印刷,獎項撬開了一個傳播優秀作品的機制,但這套機制的排他性,並非是對文學作品本身優劣的純粹批判。
就我國而言,不少中國人一直有着較強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市場上層出不窮的“諾獎作品全集”、八年前莫言獲獎掀起的熱潮,種種現象都說明了,諾獎在國人心目中的某種殿堂級地位。
(莫言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但事實上,世界上絕大多數優秀作家,都是無緣諾獎的。從托爾斯泰、卡夫卡、博爾赫斯等,到我國的殿堂級現代文學先驅魯迅,都沒能被諾獎“攬入懷中”。
於是,一個“諾獎”定式應運而生:每一項對人類擁有巨大意義的重磅級世界獎項頒佈之時,都會同時掀起歡呼和嘆息,或者說更像一種必然的偏頗性——越是世界性的,就越不能涵蓋全世界,越是擁有絕對重量、受到至高關注的,就越難免在某些方面顯得輕飄飄。
一個獎項往往是各種因素平衡所致的產物,如文學與藝術的平衡、歐亞地域平衡、政治與經濟、時代藝術審美的平衡種種。如此備受全球矚目的重量級文學獎背後,定然存在着一根看不見的槓桿,在風雲變遷的世界文學框架裏,企圖維持一種不溫不火的巧妙平衡。
與其站在籠統的所謂“文學價值”角度,去拷問一則獎項及它的擁攬者,對這個世界做出的貢獻,不如帶着荒漠中被拯救出來的一抹甘霖,去試圖體悟和反思文學獎的真正意味。
正如前文所說,路易斯的獲獎,一方面符合了諾獎這些年開始重視女性作家和個體心靈關懷,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爲一種對人類語言文字提起警示與重視的信號。
詩人,卻不僅僅是詩人,它應該、必須被“謹慎使用”,因爲他們揹負的使命,絲毫不亞於任何傑出的文學載體。正如俄國思想家別林斯基所言:“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爲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於社會和歷史的土壤裏,他從而成爲社會、時代以及人類的代表和聲音。”
在經歷了政治動盪、經濟危機和籠罩全人類的自然威脅後,2020年繼往的文學藝術創作與批判,註定揹負着更厚重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