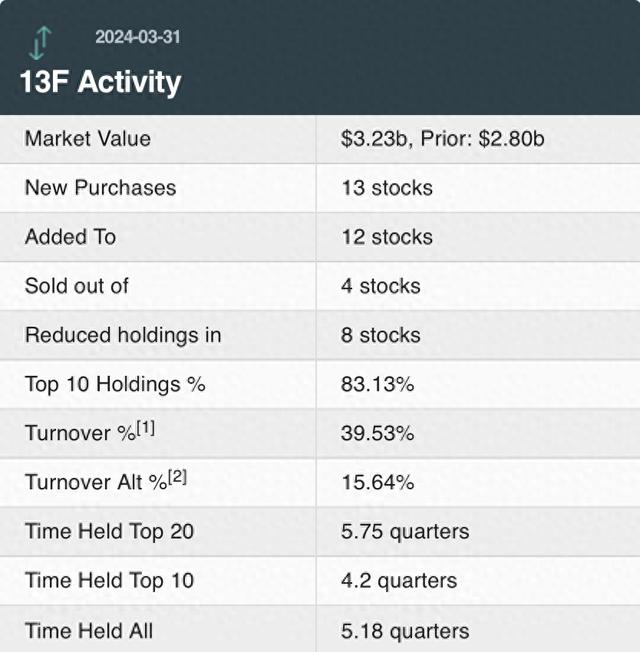不要神化臺積電
臺積電三大關鍵戰役:兄弟鬩牆、機構臃腫、巨人砸門。
文:Lina
芯片,國之命脈。
這一枚小小的方塊,竟卡住了我國無數尖端行業的咽喉,成了科技巨頭們的阿喀琉斯之踵。
2021年,36氪重磅推出《芯征程》系列產業觀察。本系列將對半導體產業上下游進行一次全方位的深度研究,包括不斷突破摩爾定律極限的製造巨頭、設備供應商、材料供應商、以及芯片設計企業。希望我們的內容能夠爲飽受“缺芯”困擾的中國產業界提供一些借鑑與參考。
臺積電被神化了。
在貿易摩擦與全球缺芯的背景下,這間中國臺灣晶圓代工廠突然成爲了全球焦點,其一舉一動都被解構重讀,成了膾炙人口的語錄式真理。
本文將把臺積電請下神壇,還原臺積電“封神”路上的三大重要戰役,還原它是怎樣一步步攻艱克難,經過幾千個日夜的奮鬥,才能最終走到今天。
兄弟鬩牆,纏鬥二十年
臺積電的第一個敵人,是其一奶同胞的聯華電子。
聯華電子(聯電)與臺積電同樣誕生於臺灣工研院。從1995年成立以來,一直到2010年前後,聯電始終穩坐全球第二大半導體代工企業的寶座,並分別在1997年、1999年、2001年向臺積電發起了三場令人拍案叫絕的閃電戰。

年輕時的張忠謀
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比聯電創始人曹興誠年長16歲。張忠謀自少年時期就在美國哈佛、MIT留學,並在加入德州儀器後一路飛黃騰達,不僅在25年內坐到了德州儀器全球三把手的高位,更與傑克·基比(Jack Kilby)、安德魯·格魯夫(Andrew Grove)這些半導體神級人物們私交甚密,時時把手言歡,談笑風生。

1976年,工研院派員赴美國RCA公司 曹興誠(左一) 圖源:工業技術研究院
相比之下,曹興誠則是個土生土長的臺灣漢子,早年間在臺北讀書時,曹興誠還曾因家境拮据而與三輪車伕們同住鐵皮屋,看遍人間百態。畢業後的曹興誠成爲了一名臺灣經濟部公務員,隨後轉調入成立不久的臺灣工業研究所電子部,並在1976年獲得工研院赴美學習半導體技術的機會。
回到臺灣後,恰逢工研院創辦臺灣第一座半導體工廠聯華電子,曹興誠主動請纓,成爲聯華電子首任副總經理,並因成績出色而在兩年內升任總經理。
成長經歷的差異賦予了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點。張忠謀嚴肅、沉穩,偏愛有留學背景的管理人才,臺媒評價其“喝紅酒、抽雪茄、紳士做派”。而曹興誠行事不拘一格,講義氣,有魄力,極其善於運用財務槓桿進行殺伐吞併,頗有些亂世梟雄的江湖氣派。
二人結緣已久,卻也結怨已久。誰要說臺積電是“史上第一個提出晶圓代工模式”的企業,曹興誠第一個跳出來反對。
1984年時,37歲的曹興誠向身處美國的張忠謀發出了一份《擴大聯華電子》企劃書,其中不僅詳細論述了半導體產業即將到來的整合新時代,更是首次提出了“晶圓代工”的概念。
然而,張忠謀並沒有回覆曹興誠。第二年,張忠謀受“蔣經國接班人”孫運璿邀請,離開美國,來到臺灣工研院擔任院長,成了曹興誠的頂頭上司。
而令曹興誠大跌眼鏡的是,第三年,張忠謀竟然宣佈創辦了“史上第一間晶圓代工廠”臺積電,其中隻字未提曹興誠的企劃書。

臺積電1987年租下的工研院超大型集成電路(VLSI)廠房 圖源:工業技術研究院
曹興誠的憤怒可以想象。然而此時張忠謀不僅是工研院院長、臺積電董事長,更是聯華電子的董事長,曹興誠的直系領導。曹興誠控訴無門。
在1991年,曹興誠終於聯合其他董事上書罷免了張忠謀的董事長之位後,曹興誠纔在公開場合正面抨擊了張忠謀的“抄襲”“盜用”行爲,卻從未得到臺積電或張忠謀的回應。
在一次採訪中,曹興誠甚至賭氣地說:“當初可能是政府比較信任白頭髮的人,就交給頭髮比我白的張先生去執行。”
聯電成立於1980年,是臺灣最早的IDM廠商,芯片設計製造兩手抓。1995年7月,聯電宣佈剝離所有半導體設計業務,專注於晶圓代工。此後業內赫赫有名的聯發科技,正是當年從聯電剝離而來。
能夠早在十幾年就提出晶圓代工模式,曹興誠對產業發展的毒辣判斷可見一斑。此人好讀史、喜風雅,最善下圍棋,其商業手段看似大開大合,實則計算精準,步步爲營。
1995年,美國重奪半導體世界第一寶座,韓國逆勢崛起,日本雖敗尤強,全球半導體產業進入產能緊俏的新週期,正是聯電宣佈全力進軍晶圓代工的最佳時機。
爲了與搶跑8年的臺積電競爭,曹興誠立刻想到了與客戶深度綁定的差異化戰略。7-9月期間,曹興誠聯合了來自美國、加拿大的11家IC設計公司,在高達30億美元的鉅額的資本運作下,聯誠、 聯瑞、聯嘉三大晶圓代工廠拔地而起,一時竟成倚角之勢。
這種大投資、大版圖、利益捆綁的集團式打法,也自此成爲了聯電的拳頭打法。
在此後兩年間,聯電不斷出手,併購、參股、設廠、出海、挖人搶客戶,處處緊逼,追得臺積電幾乎喘不過氣來。
據媒體報道,1997年6月,臺積電宣佈斥資4000億新臺幣擴建產能,聯電隨後立刻宣佈加碼5000億新臺幣進行投資。
8月,聯電旗下的8寸晶圓代工廠聯瑞正式投入運營,次月的產能一下衝到了3萬片,前景一片大好,以至於聯電總經理宣明智在10月初接受臺灣媒體採訪時,曾經自信滿滿地向記者宣佈——“聯電在兩年之內一定幹掉臺積電!”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在一場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大火裏,那間嶄新的聯瑞工廠,連帶着上百億元的機器設備、幾萬片尚在生產線上加工處理的晶圓,全部付之一炬。
據說,這場大火是由於當時聯電的承包商施工不慎所致。當時整個新竹園區上空佈滿了黑色的煙雲,火舌燎燒着嶄新的廠房四壁。
事後統計,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讓聯電直接損失上百億新臺幣,超過20億元訂單無法執行。而更爲嚴重的是,聯電因此錯過了半導體全球大復甦的絕佳行情,損失不可估量。
成功需要實力,需要人脈,更需要一點點的運氣。
天不隨人願,可曹興誠卻偏要逆天改命。
1998年開始,聯電又開啓了新一輪的併購大戰。在此期間,聯電先後收購了合泰半導體15%的股權、與英飛凌共同投資36億美元在新加坡建設新廠。
1999年,曹興誠更是憑藉高超的資本運作能力與驚人的談判能技巧,以4億新臺幣的超低價格,將日本新日鐵半導體公司160億資產收入囊中,震驚了整個半導體產業。
同年,曹興誠再度宣佈,聯電將與旗下的聯電四虎(聯誠、聯瑞、聯嘉以及合泰)合併成爲“聯電集團”,合併後的大聯電不僅一舉佔據了全球晶圓代工超過40%的市場份額,其產值更是直接衝到了全球第三,僅次於英特爾與臺積電。
除了產能、規模雙管齊下外,聯電在技術上也突飛猛進。歷史上,它是第一家導入銅製程產出晶圓、第一家生產12寸晶圓、第一片65nm芯片的生產者,與臺積電的技術差距日漸縮短,直逼全球第一。
1997年與1999年的兩場閃電戰,聯電一輸一贏。時間來到2001年,隨着中國加入WTO,960萬平方千米的市場空間打開,海量的半導體需求湧入市場。嗅覺敏銳的曹興誠立刻意識到,這正是聯電苦等多年的超車機會。
“與臺積電一較高下的戰場,非中國大陸莫屬。”曹興誠興奮地說。
不過,此時臺灣當局以避免先進技術和就業機會外流爲理由,一直嚴格控制着臺灣芯片廠商投資大陸。
爲了搶下這塊送到嘴邊的肥肉,2002年4月,聯電繞過了臺灣政府,迅速與上海貝嶺達成合作,宣佈在上海張江合作投建8寸晶圓廠。11月,聯電又巧妙地通過曲線投資的方式,與無錫上華半導體合資10億美元投建的8寸晶圓廠“和艦科技”。
然而,第二年,臺積電獲得了臺灣政府批覆的在大陸投資建廠的資格,聯電的批准卻遲遲沒有下來,上述合作只能持續以“桌底合作”的形式開展。
如果一切順利,聯電將與臺積電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進行他們最後一場生死決戰。但正如1997年那場猝不及防的工廠大火,命運又一次朝曹興誠開了個小小的玩笑。
2004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果出爐,陳水扁上任。
多年以來,曹興誠一直主張大陸與臺灣兩岸應和平共處,在這場選舉中自然是反對陳水扁的種種措施。
曹興誠性格豪爽,在公共場合從來都是大膽直言,毫不在意外界評價,自然也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誰曾想,2005年2月15日,農曆大年初七的下午,臺灣檢調部門突然出動120多名人馬,對聯電多名高管的住所和辦公地點進行了閃電般的突擊檢查,並稱聯電涉嫌向大陸和艦科技提供非法支持。
自此,曠日持久、轟動大陸兩岸的“和艦案”正式拉開序幕。

“和艦案”爆發後曹興誠接受媒體採訪,圖源:CRNTT
在聯電遭到當局搜查之後,曹興誠數次對員工及媒體發佈公開信,言辭一次比一次犀利,直指這次的搜索是公權力被誤導的行動,更點名指出承辦檢察官陳榮林就讀的臺灣交大科法所,正是由競爭對手臺積電所贊助。
在此後的一年多,聯電被此案一拖再拖,一罰再罰。曹興誠的不服輸只換來了公權機構更大力度的打壓,臺灣當局有心把“和艦案”樹爲限制兩岸經貿合作的典型案例,不斷騷擾着聯電上上下下。
2005年12月,聯電股價大幅跳水,公司上下陰雲密佈、迷霧重重。
2005年12月29日,就在新年的前兩天,曹興誠終於投降了。
爲了保住他爲之傾注了20年心血的聯華電子,曹興誠在公開信中宣佈,自此辭去董事長和董事職務,與聯電斷絕一切關係。
一年以後,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裁定,控訴聯電的檢方並未詳細查明情況,也未經專業單位鑑定等,法院無法採信爲證據,聯電無罪,曹興誠無罪。
但經此一役,聯電徹底失去了與臺積電爭奪全球老大的家底,並在2018年宣佈放棄12nm以下先進工藝投資,專注於成熟市場。
從1995到2005,聯電與臺積電整整纏鬥了20年,三次發動閃電戰,但就在每次聯電快要趕上臺積電時,總會被其他因素絆住了腳步。這是時運不濟,卻也是因爲聯電在標準化、國際化等領域存在着天然短板——與聯電相比,臺積電的管理層要“洋氣”不少,其中不僅大多有着海外高校的博士學歷,更不乏國際芯片巨頭高管。
此後,曹興誠一門心思做起了藝術收藏,再也未曾過問商事。

曹興誠晚年專心藝術收藏、不問商事 圖源:烏鎮文化講堂
2008年汶川地震之時,曹興誠還拍賣了自家珍藏的乾隆筆筒,捐款給四川地震災區。
遲鈍臃腫,“大公司病”萌芽
2005年,老對手曹興誠退休了,比他年長許多的張忠謀也早已萌生了退休的打算。
此時,臺積電的第二個敵人悄然現身。然而,這一敵人卻並非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體量不斷增長的臺積電本身。
隨着聯電深陷官司泥潭,眼見大勢已去,同年5月,已經74歲高齡的張忠謀正式辭去CEO職位,將臺積電交到了他親手培養的“皇太子”蔡力行手中,自己則退休回家,伺花弄茶,悠閒地度過退休生活。

蔡力行,圖源:臺積電
蔡力行他是放心的。這位康乃爾大學材料工程博士後在臺積電僅僅成立兩年之時就加入了公司,領導創建了臺積電歷史上第一座8英寸廠,是臺積電早年開疆拓土的重臣,更是張忠謀的心腹愛將。
雖然比張忠謀小上整整20歲,但蔡力行與張忠謀不僅同樣有着相似的經歷,更有着相似的性格與成長環境。
蔡力行出生於官僚之家,其父親蔡同璵曾任臺灣證交所董事長,而張忠謀的父親曾任寧波市鄞縣財政局長,母親是寧波清代著名藏書家徐時棟的後人。
除了求學與從業經歷之外,二人最爲相似的還是性格與行事作風。張忠謀行事嚴謹、風格強勢、凡事都要求完美;蔡力行則更是以”鐵血強勢“,業內稱他治廠如帶兵,一旦目標設定,風雨無阻,使命必達。
自從打敗了聯電,並在0.13微米銅製程上打贏了一場漂亮的技術仗後,臺積電逐漸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此時張忠謀本以爲可以放心交權給蔡力行,自己退居二線了。
然而,沒過兩年安生日子,戰火再度燒到了自家門前。
隨着臺積電在技術研發的投入越來越大,如何保住利潤率、同時又能持續吸引客戶,成了臺積電最頭疼的事情。豐年情況尚可接受,可一旦到了災年,臺積電的壓力就陡然大了起來。
2007年,次貸危機席捲全球,半導體產業也不能倖免。在全球金融緊縮的背景下,臺積電不得不連年降價,毛利率一路下滑,才能在錢包越捂越緊的客戶手中搶到一筆訂單。
爲了進一步壓縮成本、提高毛利,在CEO蔡力行的主持之下,臺積電不僅暫緩了40nm先進技術設備的採購,更採取了格外激進的裁員措施——績效排名最後5%的員工直接辭退,不留任何餘地。
於此同時,在市場逐漸恢復景氣、晶圓代工產能開始出現短缺時,臺積電應聲漲價,“勸退”了不少老客戶。據臺灣媒體報道,當時一位臺積電的美系大客戶表示,不能接受漲價的決定,並開始啓動培養第二、第三家晶圓代工供應商,以防止未來再次被單一供應商卡住脖子,而不得不接受漲價。
這一切的一切,張忠謀看在眼裏,急在心裏。
如今的臺積電,已經從當年那個不到幾百人的小晶圓廠,發展成爲擁有超過2萬名員工、生意遍佈全球各地的龐然巨獸。人員的流動、項目的管理、技術的繼承,全都成爲了發展路上的難題。
2009年4月,放權已久的張忠謀罕見地出現在了臺積電年度業務大會上,全程厲聲批評,甚至說出“大家皮繃緊一點!這樣下去,臺積電會完蛋”這樣的重話,罵得在座高管們全都默不作聲。
隨着事態持續發酵,當年6月,張忠謀強勢介入,不僅公開宣佈回聘所有被裁員工,更親手撤掉了蔡力行的CEO頭銜,打入“冷宮”,改任新事業組織總經理。

張忠謀現場宣佈撤掉蔡力行CEO職位 圖片來源:商業週刊
78歲的張忠謀重新披掛上陣,再次扛起了臺積電的大旗。
迴歸之後,張忠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佈此前的裁員無效,所有希望迴歸的員工,臺積電的大門都將爲他們打開。而且不光是不裁員,臺積電還要加大人員的研發投入,豪擲10億美元研發經費,條件只有一個,“儘快花出去”——要知道,2009年臺積電的總營收也就僅有90億美元。
技術提升,客戶迴流,人心再度凝聚。尤其是臺積電重金投入研發的Gate-Last技術,更是力壓競爭對手,成爲了公司在28nm工藝稱霸產業的關鍵節點。
張忠謀的這次迴歸,將臺積電的“大公司病”扼死在了萌芽狀態。
蔡力行並非能力不足——幾年之後,他將空降聯席CEO職位,拯救另一間臺灣芯片廠商於生死邊緣,並且大獲成功。只不過,張忠謀這類第一代創業者所具備的“Day 1”“我們離倒閉只有30天”的緊迫感,以及力排衆議、不顧財報表現、堅持己見的“偏執”,是所有職業經理人都難以具備的。
這一仗幾乎算是險勝,要是再晚一點,臺積電即將迎來它生命中最強大的對手,一個富可敵國的龐然巨獸——三星。
巨人三星與“叛將”梁孟松
三星是韓國最大的企業集團,這間由李氏家族創辦並把持大權近90年的大型企業,旗下擁有近百個下屬公司,涉足電子、醫療、人壽、金融、建築、酒店等諸多領域。
尤其在電子產業,三星集團的觸角一路向產業鏈上下延伸,囊括了屏幕、電池、鏡頭、傳感器等多項關鍵器件,憑藉着技術壟斷賺取豐厚利潤。而且,三星集團的行事風格非常“韓國”,我國的手機、電視產業都曾被它擠壓得苦不堪言。
在1985-1987年日美貿易戰期間,日本與美國在半導體領域大打出手,三星漁翁得利,一舉挖空了日本的存儲芯片人才,並在未來幾年迅速壓低市場價格,以雄厚的資本實力碾壓對手,在1993年做到了內存芯片市場第一,在2003年做到了閃存芯片市場第一,自此一路稱霸。
日本戰場的硝煙還未散盡,三星又瞄準了下一個受害者。據臺灣媒體《今週刊》在2013年的報道,在2008全球次貸危機期間,三星最高管理層經過多次密謀,最終決定將炮火瞄準中國臺灣——這顆冉冉升起的IT之星。
爲了奪下臺灣的市場份額,三星制定了一套縝密的“Kill Taiwan(消滅臺灣)”計劃,有針對性地對臺灣電子產業進行挖角與市場傾銷,幾年間陸續壓垮了臺灣的存儲、面板、手機產業,一路凱歌。
而利潤豐厚的晶圓代工,自然也逃不開三星的魔爪。
由於晶圓代工廠前期技術投入高昂,聰明的三星並沒有一上來就和臺積電發生正面衝突,而是巧妙地選擇了高端市場這一細分領域。三星電子半導體事業部總裁暨CEO黃昌圭在接受媒體的採訪時也一再強調,三星代工的主要是面向高端的芯片產品,與臺積電定位並不相同。
而2009年,則是一切的轉折點。
這一年裏,發生了三件大事:
1、78歲高齡的張忠謀迴歸臺積電,撤下“皇太子”蔡力行,重披CEO戰袍。
2、蘋果、三星、Intrinsity公司共同研發的“蜂鳥”手機芯片面世,由三星代工生產。
這款手機芯片是蘋果與三星的得意之作,憑藉着它,蘋果拿出了震驚世界的初代iPad與iPhone4,三星則推出了其智能手機一戰成名的代表作,Galaxy S i9000,一時火遍大江南北。三星的代工業務也藉此一舉突破4億美元大關。
3、臺積電技術骨幹梁孟松負氣出走,被三星成功挖角,來到韓國。
在臺灣媒體此後多年的報道中,梁孟松都被冠上了“臺積電頭號叛徒”的稱呼。在這場戰役中,梁孟松的加入,瞬間踢翻了臺積電與三星的實力天平。
梁孟松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機博士,其導師正是半導體產業舉世聞名的、爲臺積電續命20年的FinFET發明人,胡正明。
在臺積電的16年時間裏,梁孟松帶領團隊打下了不少重點技術攻堅,不僅有着強大的技術研發能力,更具備深厚的產業Know-How。
根據梁孟松同事回憶,他是個技術狂人,能力強、要求高、脾氣急,性格豪爽火爆,喜歡單打獨鬥——這一點在去年沸沸揚揚的梁孟松怒辭中芯國際CEO事件中可見一般。
時至今日,梁孟松身上仍然保留着工程師那棱角分明的技術傲氣,對於先進技術有着強烈的熱愛與執着。臺積電前法務長方淑華曾經感嘆,“(梁孟松)他就是有種執念,覺得要做最先進的技術,纔算重用。”
這也是爲什麼,在2006年臺積電研發副總改任時,梁孟松發現自己不僅沒有被升任研發副總,反而被調離先進技術研發一線,安排去負責“超越摩爾”計劃的成熟工藝產線時,反應異常激烈,甚至怒斥這是“架空”“降職”“冷凍”,最後負氣出走。
此時,翹首以盼的三星正迫不及待地張開懷抱,歡迎梁孟松的到來。
上億臺幣年薪、上下班專機包送都只是基礎操作,更重要的是,三星給予了梁孟松絕對的控制權與廣闊的發展空間,能夠讓他安心專研先進技術。
梁孟松之後,黃國泰、夏勁秋、鄭鈞隆、侯永田、陳建良等臺積電舊部也陸續被三星挖角成功,在三星內部組成了一支強大的“臺灣團隊”。
在短短几年間,三星的晶圓代工技術突飛猛進。晶圓代工廠們眼看着45nm、32nm、28nm這一個個關鍵技術節點被三星逐一攻克,跟臺積電的差距越拉越小。
2009年,三星的晶圓代工業務還只有4億美元;2010年,這一數字激增至12億美元,2013年更是達到了驚人的39.5億美元,其崛起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等到臺積電嗅到危險,開始以競業協議控告梁孟松時,已經有些晚了。
此時,一路凱歌的三星在梁孟松的帶領下,做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決定——跳過20nm,直接向14nm進軍,搶在臺積電前全球首發14nm,正面宣戰。
2015年,臺積電推出16nm工藝,可三星早在半年之前就完成了14nm的量產,並順利搶走了本該屬於臺積電的10億美元蘋果A9訂單,同時搶下高通芯片的鉅額訂單,一時風頭無兩,好不輝煌。

臺灣媒體對梁孟松的報道,圖源:三立財經臺
製程落後、客戶流失,雪上加霜的臺積電股價開始崩盤,瑞士信貸、里昂證券等一向看好臺積電的券商,開始調低臺積電的投資評價等級。
在2015年1月15日的法說會上,在面對分析師的詢問時,張忠謀無奈地承認,“沒錯,我們有點落後。”
這是臺積電自成立以來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在過去幾十年間,它從沒有在先進製程上如此顯著落後。
此時的張忠謀已經84歲了,世人懷疑之聲不絕於耳,這一仗,臺積電還打得贏嗎?
答案是能。
爲了發起技術強攻戰,臺積電效仿富士康,實行了24小時三班倒的研發制度,參與人員底薪上調30%、分紅上調50%,全員殺紅了眼,目標只有一個——打倒三星。
蔡力行之後,臺積電治廠本就以“鐵血”著稱,此番雞血高壓之下,更是迸發出了驚人的戰鬥力,不僅16nm工藝良率直線拉昇,更是在2015年底就開啓了10nm工藝的送樣認證。
與此同時,臺積電還對梁孟松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訴訟打壓。即便梁孟松一再強調自己並未泄露臺積電核心機密,“絕對遵守競業禁止規定”,也並無用處。
臺灣的各大主審法院更是從一開始就明確了自己的站隊立場,二審的主審法官熊誦梅甚至直言,“(臺灣)能有幾個大企業?如果我們不保護他們(臺積電),要保護誰?”
正當梁孟松爲訴訟焦頭爛額之時,三星的14nm工藝也因搶跑先發,良率與功耗控制出現了明顯問題,甚至出現iPhone6s“芯片門”事件,使得蘋果後續A9的追加訂單重新流回臺積電手裏。
此後,梁孟松不堪訴訟困擾,揮別三星,並於2017年受邀加入中芯國際,擔任CEO職位。
這一局,臺積電再次險勝。
不過,時至今日,三星依舊沒有放棄對臺積電的追趕。
2016年,有韓國媒體報道,三星答應高通,在自家Galaxy S8中搭載驍龍830芯片,條件是高通的驍龍830訂單將由三星代工生產。
2019年,三星拼命壓低價格,瘋狂搶單臺積電,並已經成功地拿下英偉達訂單。

李在鎔(左二)參觀荷蘭ASML在埃因霍溫的工廠 圖源:三星
去年10月,三星集團實控人李在鎔更是親自飛往光刻機巨頭ASML的荷蘭總部,得到了ASML CEO與CTO的親自接待,雙方進一步商討5nm、3nm、甚至更先進製程上的合作機會。
硝煙未止,戰爭仍在繼續。
尾聲
回望臺積電這四十年風雨歷程,這三大戰役,正好將臺積電的成長分成了三個階段。
在成長初期,臺積電與聯電的瑜亮之爭,恰恰促進了第一代晶圓代工技術的爆發浪潮。聯電咄咄逼人的“軍備擴張賽”,更是爲臺積電日後的全球稱霸積累了豐富的物質基礎。
在成長中期,隨着企業機構日漸臃腫,“大公司病”悄然滋生,臺積電及時地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不被財務報表所束縛,更加堅定了技術立身之根本,爲臺積電的長遠發展確立了文化根基。
在成長後期,當臺積電真正站上全球舞臺,面對富可敵國的財閥巨頭,它不僅重新肅清了研發攻堅體系,更將國際政治關係運用得如魚得水,帶領檯灣晶圓代工界成功地躲過了三星的“精準爆破”,邁向全球霸主之路。
有時你最應該感謝的,是你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