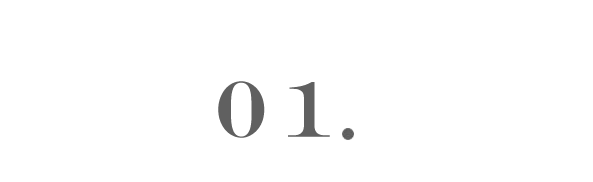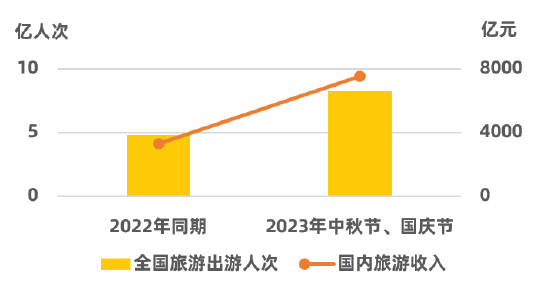他點燃國慶70週年"人民萬歲"煙花:對中國土地有責任
[文/觀察者網 馮雪 編輯/隆洋]
還記得那晚一步步邁向鳥巢的“大腳印”嗎?

見過騰躍着金色火光的“天梯”嗎?

如何打造國慶70週年最絢爛的焰火?

這一切視覺奇觀的創造者,名叫蔡國強。
他1957年生於福建泉州,求學上海,後旅居日本、美國,憑藉獨樹一幟的火藥作品,“爆破”全球。在國人眼中,他最爲人熟知的身份是,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核心創意小組成員及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
國外“遠行”多年後,蔡國強重磅“歸來”。
本次“遠行與歸來”緣起他近年“一個人的西方藝術史之旅”,在世界重要美術館舉辦展覽,與其館藏代表的西方藝術史對話。同時,蔡國強與繪畫初心、中國文化精神和作爲他永恆之鄉的宇宙的對話,追溯漫漫之旅。

蔡國強 趙夢佳攝 蔡工作室提供
這場巡迴展,去年年底落腳點在北京故宮,今年7月來到上海浦東美術館(MAP)。觀察者網通過“上海”、“蘇聯”、“火藥”、“國家”與“宇宙”五個關鍵詞解讀這位藝術大師。
上海
蔡國強與上海有着不解之緣。
2001年上海APEC會議設計焰火表演、2010年上海世博期間展出《農民達芬奇》、2014年上海黃浦江上綻放百日焰火……
上海是他離開家鄉後的第一個港口。1978年,蔡國強第一次出走老家泉州,到上海觀看“法國十九世紀農村風景畫”展覽:第一次親眼目睹西方藝術家原作。80年代初,他從泉州高甲戲劇團來到上海戲劇學院學習舞臺美術設計。
“上海對年輕的我,就是西方文化的一個真實存在……這個展覽,關於我與西方相遇的神奇、與先輩們單相思的折騰,也是我在他們故鄉和作品庭園裏的深深呼吸。”上海,萌生了蔡國強“西方藝術史”的遠行。
蔡國強告訴觀察者網,藝術圈的朋友誇讚浦東美術館可以媲美世界一流,定位和目標非常明確;與世界各大經典美術館進行對話和交流,把好東西介紹到中國,這屬於“海派精神”。同時,他也提醒道,硬件方面,我們做得很快,但軟件方面,比如文化層面,我們還需努力。

MAP展館正立面 浦東美術館提供
“嚴格來說,(這世上)沒有美術史,也沒有美術館,”蔡國強非常看重作爲個體的藝術家。
他說,所有這些,都是爲了讓藝術家開放他們的靈魂、自由精神、天馬行空、對時代的看法等等可能性;只有讓他們玩起來,城市的文化才能動起來;只有他們留下令人難忘、雖有爭議的作品,城市才能留下文化的記憶。
蘇聯
建國之初,上海畫家中,除了老一代留法留日的,之後都是受蘇聯影響。蔡國強在上戲的老師周本義先生,就是蘇聯列賓美術學院畢業的。
蔡國強對觀察者網說,“蘇聯情結就是我的紅色少年情結,深刻影響了我的成長曆史”。他在回憶少年時代的文章中寫道,很難向俄羅斯人講清,俄羅斯文化對一個遠在中國東南邊陲小城的少年有多大影響。

蔡國強《早期作品牆》 顧劍亨攝 蔡工作室提供
單從美術上來講,就不得不提到“老馬”。
1955年,蘇聯畫家馬克西莫夫來到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從全中國挑選出大約24位最優秀的年輕油畫老師到北京參加“馬訓班”。
時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吳作人形容馬克西莫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人生一樂也!” 雖然馬克西莫夫不曾去過福建,但時代的精神無遠弗屆。蔡國強承認,家鄉的油畫長輩,包括他自己、以及後來幾代人,都受他影響。
中蘇關係破裂後,馬克西莫夫於1957年離開中國,但“馬訓班”的學生紛紛成了各美院掌門人,有的還是全國美協主席。
“俄羅斯文化曾經那麼大,大到就是中國人眼中全部的外國文化,就是東方的西方,國畫以外的洋畫;中蘇關係對立後,俄羅斯突然在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消聲,但她的文化還是根基,頑固地存在,作爲藝術少年的營養。”
蘇聯,註定與蔡國強纏繞不清。
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上,蔡國強“復刻”了反映地主與農民階級矛盾的《收租院》:他把部分原作者請來,現場表演製作這套雕塑作品。

蔡國強作品《威尼斯收租院》 Elio Montanari攝 蔡工作室提供
同年底,據他所述,在阿姆斯特丹一家畫廊裏看到一件小油畫頭像,一下子知道是“老馬”,從此開啓了“老馬”作品收藏之旅。
3年後,“蔡國強收藏馬克西莫夫作品展”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展出,久違的“馬訓班”老畫家也現身回憶尊師。蔡國強介紹說,這是兩個不同時代藝術家在命運上的對話,尤其是同樣出身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藝術家。
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藝術家”來說,“十月革命”是記憶中最難忘卻的場面之一。2017年,時值“十月革命”百年,蔡國強應俄羅斯國立普希金美術館邀請舉辦紀念展覽,並構想在紅場實施白天焰火。

蔡國強作品《紅場上空的馬列維奇:黑方格、黑十字、黑圓圈》、《紅場上空的紅星》 蔡工作室提供
蔡國強透露,當時他腦海裏想到了家鄉巨大山岩上的毛主席像。藉助傳統水墨拓碑方法,他和團隊結着保險繩吊在山崖上,用蘸墨水的布團一下下拍在布片上,拓出毛澤東側像。

蔡國強於山崖上製作《拓毛》 33 工作室攝
蔡國強對觀察者網說,雖然他並未如周本義老師那樣,創作蘇聯社會主義寫實作品,但這段歷史都成了他詢問“爲什麼”的一個機會;這些都使他有思考、有好奇,而有不明白就有藝術。
遺憾的是,因種種限制,蔡國強最終未能在紅場上空“發射”紅星。
火藥
離開上海後,蔡國強的下一站是日本。雖然在國內已然開始嘗試火藥畫,但正是到日本後,蔡國強逐漸脫離顏料,純粹使用火藥創作。
在蔡國強的講述中,有個頗具意味的細節。
無法順利搞到火藥之際,蔡國強結識了日本煙火元祖“丸玉屋”十三代傳人、日本煙花協會會長。他對蔡國強說,“日本火藥和焰火都來自中國,我們受中國的恩。你隨便用我們的材料和場地,算是我們的心意。”
無論誰受惠於誰,中國和日本在當代有着共同的複雜心結。在蔡國強看來,亞洲當代藝術既要面對是否被西方承認,又要在西方衝擊下,尚能說出自己的話語。這是有矛盾的。

蔡國強作品《花瞬二》 趙夢佳攝 蔡工作室提供
與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汪暉聊到“以日本爲鏡,如何看待中國”時,蔡國強曾如此剖析:由於東方材料和精神上的傳統特殊性,沒能成爲國際語言,日本人一直爲此痛苦搖擺;我在日本的狀態還好,我堅信書法、茶道、花道這些,包含一套完整的認識世界、表現世界的方法論;既然東方先人有這一套東西,跟西方是不同的。爲什麼在當代,用這一套方法論就不能繁衍出不同的當代藝術呢?
“我沒有在痛苦中搖擺。”
或許,由中國煉丹士偶然發現的火藥,是蔡國強緩解痛苦的抓手之一。他認爲,跟火藥對話,減到“一”;東方文化裏,“一”能表現所有。
他還向觀察者網坦白,自己講話思路清晰、很有邏輯,做一個人是挺好的,但作爲藝術家其實不大好,這意味着善於控制自己的思維、控制自己的行動,也就放不開;他繼承了父親那一輩泉州人的性格,不是很狂,火藥可以讓他更失控,破壞他自己。
“有時候我往寫實走,有時候我往抽象走,有時候我讓火藥更自由一點,有時候我又更被控制一點,等於是我跟火藥一直在較勁。”
國家
歷史學家白傑明說:“蔡國強的國際名望與中國崛起爲大國是並行一致的,也反映了中國的崛起,激發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當代藝術不斷高漲的興趣。”
當代中國多個顯耀的歷史瞬間中,都有蔡國強的深度參與,典型如北京奧運會、國慶70週年。
煙花輕盈劃過夜空,升騰前的一瞬,似乎也有“包袱”。蔡國強加盟奧運時,西方有聲音質疑稱,作爲獨立藝術家,爲何要與“國家行爲”扯上聯繫。
在2016年名爲《天梯》的紀錄片中,蔡國強戳破了這個假“包袱”。他反問道:可是所有的國家、藝術家,都在給他們的國家做奧運會,就像倫敦奧運會,達米恩·赫斯特也做了一個英國國旗的舞臺;問題就出在,你是一箇中國人,在自己出生的國家,做這個事情,有問題。
當觀察者網問及這個問題,蔡國強說,這其實是一個很個人的問題,我對這個土地有情感,也有責任。
“我能夠做一點事情,且做的過程,能夠思考內在的、文化的,包括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中國走向未來面對的問題,也是人類走向未來面對的問題。那麼,在中國參與這些項目,讓我更接地氣。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我接觸的人和事,有時最讓我焦慮掙扎,也最讓我有成就感、有收穫,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成長機會。有情感、有責任,做一個藝術家就會有好作品的可能。”

蔡國強作品《夢遊紫禁城》 顧劍亨攝 蔡工作室提供
宇宙
高30餘米、長寬17米的浦東美術館中央展廳,是建築師爲藝術家埋下的挑戰,這沒有難倒蔡國強。作爲特別委任作品,《與未知的相遇》超越歷史線性敘事,讓不同的宇宙觀橫截面這裏碰撞:
空中充斥着一座座萬花筒般的星系所構成的“宇宙叢林”;下沉空間裏是深藏着的“黑洞”和“蟲洞”;升起的移動平臺成爲中國古人“萬戶飛天”和現代航天飛船的發射臺,其上有 “宇航員環繞地球”、“加加林”以及如梯子般的文字“地球是藍色的”;展牆上掛着“接觸”、“與未知的相遇”;展廳中心爲裝置主體——象徵着連接世間萬物的“宇宙樹”,呈現從 “原始人與外星人” 到 “愛因斯坦”和“霍金”,再到飛碟、外星人和空中的天使……

蔡國強作品《與未知的相遇》 顧劍亨攝 蔡工作室提供
蔡國強告訴觀察者網,整個主題背後,其實反映了他試圖把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作爲自己的文明繼承,不同先輩、祖先,也是他的先輩、祖先。
巧合的是,今年也是中國航天大年,火星探尋、載人飛船等等重磅消息頻出。蔡國強坦誠,自己並未料想到今年中國在航天領域種種大動作。或許,這就是藝術家與時代之間某種微妙的聯繫。冥冥之中,蔡國強完成了與當代中國的對話。
“天梯”衝破大地,刺向宇宙,變作“天塔”。

蔡國強作品《天梯》 視頻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