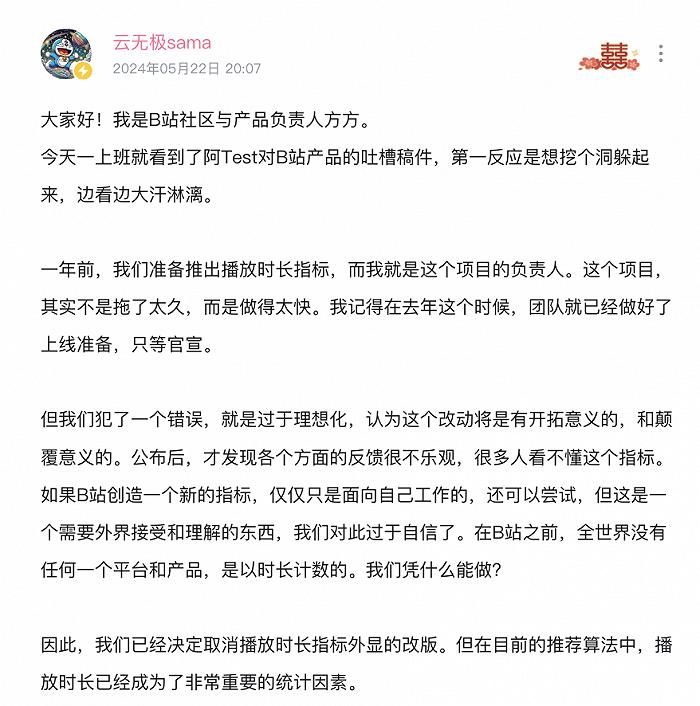這代打工人不想996了

歡迎關注“新浪科技”的微信訂閱號:techsina
文/儲松竹 戴老闆
來源/飯統戴老闆(ID:worldofboss)
B站up主“大猛子”,姓印名猛,字牛馬,號勸學居士,粉絲73萬,是2021年B站出圈級的風雲人物。
大猛子畢業於河北農業大學,在嚴肅文學之鄉保定渡過了四年大學生活,可惜學的是土木工程,剛畢業就去了中鐵九局的一線工地上幹活,因此他的視頻以展示工地日常爲主,一張包工頭形狀的橫肉臉跟22歲的年齡反差極大,在一衆細皮嫩肉的B站後浪裏顯得特立獨行。

大猛子向粉絲展示B站頒發的獎牌
在視頻裏,他常戴着紅色安全帽,操一口東北話,一邊跟粉絲保證永不提桶跑路(土木人對辭職的自嘲),一邊假裝抽兩口華子,做吞雲吐霧的陶醉神情,更是偶爾爆出“有人出生就在羅馬,有人出生就是牛馬”這種當代醒世名言,人送綽號“猛爾仁尼琴”。
大猛子的視頻受到年輕人的追捧,但這些視頻裏唯獨缺的,也是年輕人。
在60多期視頻裏,你可以看到出生於1950~1990之間的各代人:有頭髮花白還在工地裏幹活、中午蹲路邊喫盒飯、不排除晚上還順點兒鋼筋回去的50後老大爺;也有每天開戴着破舊的帽子,在清冷的早晨騎着電動三輪載着工人的60後老大叔。
還有一個月能掙一萬多,但一年只捨得剪三四回頭的70後瓦工,一邊穿着單薄的冬衣在寒風中抹水泥,一邊跟大猛子說自己要把錢留着“給閨女兒子花”;也有掄着鐵鍬鏟水泥、全身上下蒙了一層白灰的80初小包工頭,在猛子管他要煙的時候不太情願地掏出一盒玉溪。
但除了在某期視頻裏出鏡的一個年輕同事,大猛子的鏡頭中就很見到同齡人了。在一期播放量375萬的視頻中,他講到了這個現象:“現在工地上說所有幹活的人,就是各種工種的人,基本上都是在35歲以上,平均都是40多歲,你很少看到有年輕的人去幹工地的那活。”
土木工程以前算是一個熱門專業,尤其是在房地產和基建黃金二十年的背景下,設計、施工、監理、總包等單位容納了大量新增就業。但近些年來,相對一般的福利待遇和風吹雨淋的工作環境,“三總五項”(三年做總工五年做項目經理)的職業路徑越來越無法吸引到年輕人。
大猛子儘管還沒有“提桶跑路”,但他其實也在拒絕這種一眼能看到頭的按部就班。通過做up主,他一期視頻的廣告報價應該不比他一整年的收入少太多,因此儘管他的成功很難複製,但不少年輕人在關掉視頻之後,第一時間做的就是搜索21天視頻剪輯速成和跨專業考研寶典。
擁有一份up主副業的大猛子,以及消失在他視頻裏的年輕人,隱藏了中國勞動力就業幾十年裏最大的變遷軌跡。
變遷:中國勞動力就業簡史
1978年,北京市政府的一份內部調查紀要這樣來形容那個年代的青年[1]:
“部分青年經濟非常困難,難以維持正常的生活。精神負擔和壓力很重,許多人思想苦悶,悲觀失望,家庭爭吵,婚姻困難,個別青年無所事事,遊蕩在社會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敗壞社會風氣。”
很多人以爲市場經濟一放開,就業機會就從天而降,其實不是這樣的。改革開放後大量返城的知青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待業,住房、學習、婚姻等問題層出不窮,1978年、1979年城鎮登記失業率高達5.3%和5.4%。1979年城鎮待業人數高達1500萬,達到建國以後的高峯。
除了城市青年,潛在的農業人口就業需求更爲龐大。由於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大量農民從田間地頭上被解放出來。儘管土地和戶籍制度能夠暫時“綁住”他們,預防農業人口變成城市貧民甚至流民,但如何滿足龐大的非農就業需求,其實跟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總設計師當時非常關心就業問題,他的解決思路就是“廣開門路”。1978年他在一場談話中這樣說:“真正解決下鄉知識青年問題,歸根到底是城市工業發展。重工業發展後,是不是開闢一些就業門路,比如輕工業、服務行業,都可以用一些人。又比如發展旅遊事業,可以用很多人。”
後面就是一場“連續創造容納百萬千萬級就業的產業”的勵志大劇了。
1980年代,經濟體制的變化催生出了無數鄉鎮企業,個體戶也首次在南方的城市出現,它們容納了大量就業人口(包括百萬裁軍的退伍人員)。同時,高等院校的重新招生也讓勞動力有了一個不小的緩衝池。中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從1978年的5.3%,一路下滑到1985年的1.8%。
1990年代,“三來一補”的外貿企業繼續發展,92年之後下海的人羣入過江之鯽,同時外資企業蜂擁入華,製造業崛起。而此時一些新的行業出現了,比如未來能容納千萬級就業人口的房地產行業。但同時在90年代末,對國企的全面改革也讓成千上萬的工人面臨重新就業的難題。
2000年代,加入WTO的中國經濟開始起飛,在內部外部龐大需求的刺激下,中國開啓了重化工業進程,GDP每年兩位數增長,外貿(背後是製造業)、房地產、投資(主要是各類基建)逐漸成了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同時它們也都是容納數千萬級就業人口的超級行業。
2010年代,服務業和商業對就業人口的容納開始趕超三駕馬車。在2014年,批發零售行業首次超越了製造業,成爲中國就業人口第一的行業。而隨着互聯網商業模式的不斷創新,一些前人無法想象的崗位也被創造出來了,比如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新媒體創作者等,這些新職業都能容納百萬級的就業人口。
2013年是一個分界點。在這一年,中國勞動力人口達到了10億人,之後總勞動人口的數量就在不斷下降,尤其是新增20歲的勞動人口水量。在2013年之前,勞動力的需求方議價能力更強;而在之後,勞資博弈的天平開始逐漸向越來越“稀缺”的年輕人身上轉移了。
對於50後60後甚至70後80後來說,找工作的時候往往不是看我們想要什麼,而是看市面上有什麼。
從一個極端案例的對比中就能感受到:今年1月,騰訊一個95後應屆生因爲加班怒懟領導,自己主動離職並表示“希望各方不要卡我的審批,免得妨礙我過年”。一個80後朋友看到新聞後,在羣裏頗爲得意的講道:“你看,還是咱們這些有房貸的35歲+的中年人好使吧!”
他的本意是想吐槽公司喜歡招年輕人的偏執(甚至不惜工資倒掛),只不過這句話讓人聽了五味雜陳。
對於1990年前出生的人來說,貧窮和物質匱乏的記憶是刻在他們腦子裏的,因此有一份餬口且穩定的職業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畢生追求,至於興趣愛好、生活平衡、職業空間、勞動保障等……似乎都遠在天邊,看得見但摸不着,用趙本山的話來說就是:要啥自行車啊?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大猛子這屆年輕人之所以不一樣,一方面是六個錢包的積蓄能夠讓他們有了一些從容的空間,另一方面是因爲年輕人的“供給”在減少,“出路”在增多——而這些所謂的出路,其實也都是上幾輩人努力奮鬥的結果。
基建:昂貴的就業選擇權
很少有人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業的選擇權看似是一項個人權力,但它其實是一種嚴重依賴一個國家的產業基礎設施的昂貴公共品。
所謂產業基礎設施,指的是能夠容納大規模就業的崗位數量(足夠多的勞動力需求)、支付能力(足夠大的現金流收入)、勞動保障(關乎勞動力的可持續)。任何一種能夠容納中國勞動人口0.1%比例的職業,背後都是一個成熟的產業。它需要市場參與各方的齊心協力才能誕生。
0.1%這個比例看似不大,但乘以人口基數後絕對值一點兒都不小。2021年中國勞動力適齡人口8.8億,0.1%就是88萬,四捨五入取100萬的話已經抵得上一個小國的就業人口了。一個容納百萬級就業的職業,背後既需要政府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也需要企業搭建的商業閉環。
在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期,老百姓只能去做農民,祖宗八代裏但凡能蹦出一個讀書致仕的小官小吏,都得寫進家譜裏常年香火供着。即使到了民國時代,95%的青年出路也是農民,其中的30%還只能做沒有自耕地的佃戶,接受黃世仁的盤剝。
原因無外乎就是一條:農業社會只有第一產業。所謂“工農商學兵”,其他四個加起來也沒有“農”的零頭大。
甚至連“兵”這種職業也依賴於產業基礎,其裝備、彈藥、運輸、醫療等無一不需要強大工業的支持。因此在二戰期間,工業國家的動員率遠超農業國,比如美國的動員率爲12%,英國15%,蘇聯17%,德國22%,日本12%,而中國只有4%——農業國養不起更多的軍隊。
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沒有產業,何談就業?
而B站“up主”這門職業,在10年前也根本不存在。它的出現依賴於三個條件:一個是通信基礎設施的完善,保障了視頻能成爲媒體形態的主流之一;二是智能手機的普及,確保有足夠多的信息消費者和生產者,三是能夠提供商業閉環的平臺,確保up主們能掙到錢,不至於用愛發電。
大猛子之所以能夠持續用鏡頭展現深夜的打灰、凌晨的巡查、風雨的環境等,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這是一份能夠帶來收入的“副業”。其實工地的辛苦一直如此,“提桶跑路”最早出自土木工程百度貼吧,10年前就已“一片狼藉”,只不過圖文互聯網時代,行業內的吐槽沒能出圈而已。
那會兒雖然已經有優酷土豆這種UGC(用戶生成內容)視頻平臺,但發佈者很難獲取物質回報,up主很難成一種可持續的職業。直到隨着流量費用的下降,視頻逐漸成爲人們日常信息消費的主流,B站、快手、抖音這種平臺完成了商業閉環的搭建,“主播”和“up主”才逐漸成爲能夠容納百萬級就業的新職業。
再舉一個例子:外賣員這個職業的誕生,背後也是基礎設施和商業閉環共同發力。
人類其實很早就有了“把飯送到我嘴邊”的這種需求:早在清明上河圖裏,就有宋朝汴梁的外賣小哥進行送餐的場景;伊朗國王巴列維曾經調用協和的噴氣式客機,每天從巴黎空運早餐到德黑蘭給自己喫;至於“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不就是生鮮電商嗎?
但在餐飲業幾千年歷史裏,“外賣”從來沒能形成商業閉環,餐館老闆自己建設配送隊伍,是一件怎麼算都划不來的事情。即使到了物質極大豐富的2000年後,想偷懶不出門點個餐也只能依靠外賣“小卡片”(不是會被掃黃扭送派出所的那種),配送時效長,種類選擇少。
直到移動互聯網的誕生(背後是國家建設的200萬個4G/5G基站和5000萬公里的光纜網絡),美團和餓了麼等外賣平臺用新的技術連接了上億的消費者和接近1000萬的商家,然後開始自建配送團隊,把外賣的配送平均時效大大提高,形成了商業閉環。
所以說,經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激烈的商業競爭,“外賣”才成爲了能夠容納百萬級就業的產業,而外賣配送員也成爲青年人的就業選擇之一。
過去十年中,智能手機性能的不斷提升和移動互聯網效率的躍遷,是很多商業模式出現的基礎。除了外賣配送員,數字經濟時代催生了大量此前不存在的就業工種,比如典型的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騎手、主播等,按照官方口徑,這些“工種”的就業規模超過了5000萬。
除此之外,一些小型工種也隨着人均收益的提升和數字經濟的發展湧現出來。根據美團的新型就業報告,近年來,平臺集中湧現了包括套餐設計師、家庭整理師、密室策劃師、漢服造型師、VR指導師、電競顧問、寵物殯葬師等在內的近百個新型工種,且需求持續旺盛。
這些新型工種的出現,本身也是就業從農業和工業,遷移到服務業的表現。總設計師在1978年視察鞍鋼的時候就講過:“世界變化的結果,生產越發展,直接從事生產的人越少,從事服務業的人越多。服務行業很多,如種子公司、修理等,這說明有很多辦法可以安置勞動力。”
因此,沒也有必要指責這些新型服務業挖走了製造業的工人,這本身就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規律。
2019年我國首次實現了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中國老百姓對消費的需求也出現了很多變化,閒暇時間多起來的居民們,也開始關注精神消費。說到底大猛子之所以能在B站做up主,也是因爲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來這種視頻網站找樂子,大猛子也能在工地之外給自己搞份副業。
因此,在幾代人心目中排名前10的土木工程,可能在95後眼裏連前20甚至前30都排不進去。年輕人可能沒有出生在羅馬,但相比那些同樣沒有出生在羅馬的50後~80後們,年輕人明顯多了一些新的選擇。這種選擇的結果,就體現在大猛子視頻沒有年輕人的這個結果上。
總而言之,“選擇權”的擴大是政府基礎設施投入+企業搭建商業閉環的結果。在早些年的輿論環境裏,前者的重要性被忽略;而近些年的輿論環境裏,後者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
進化:這代打工人不想996了
大猛子火了之後,就有好事的媒體將他和同爲B站爆火UP主的何同學聯繫起來做了對比。
腦袋大脖子粗像伙伕一般的大猛子和科技精英範兒的何同學其實同爲95後,這種極其強烈的對比背後,確實可以解讀出很多意味深長的社會學命題,但這無法展開探討,也永遠都講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從對工作的態度上而言,95後是截然不同的一代人。
根據一份《96後畢業生就業現狀調查》顯示,最受95後歡迎的新興職業是主播或網紅,而期望選擇該職業的人數佔比達到了35.32%。大猛子和何同學兩位95後做着所有同齡人都夢想的工作,當網紅。這份職業在中國傳統意義上算不得是正經工作,不在編制內,沒有五險一金,前途不穩定,但95後喜歡。
前兩年85後之間盛行着35歲焦慮,但是這兩年不少互聯網大廠意識到情況不對:新招進來的95後不像想象中那麼願意卷。過去那套價值觀+激勵的胡蘿蔔掛出來,再也吸引不了人了。不但吸引不了人,還動輒還會被實習生用一份郵件或者小作文捅出個全網的新聞。
這個時代的職場關鍵詞是反內卷和躺平,似乎什麼也催動不了年輕人們的鬥志。不要急着批判,歷史上好像還有兩代人也呈現出相近的情緒面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年輕人唱着搖滾開啓了轟轟烈烈的嬉皮士運動。他們穿喇叭褲、抽大麻、搞性解放;他們批評政府、憎惡資本、反對戰爭;他們反對物慾,歌頌愛與和平;他們迷惘又理想,頹唐又亢奮。這是一場包裹在文化裏的政治運動,對抗的是那個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但等級森嚴的美國社會。
嬉皮士的影響是極爲深遠的,留下的藝術、文學、音樂後來滋養了一代代年輕人。更爲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代荒誕和垮掉的人,創造了美國IT產業後來的全盛時代。在一本名爲《鼴鼠私語——60年代反文化如何塑造了個人電腦行業》的書裏這樣寫到:真正賦予個人計算機爆發般創造靈性、塑造硅谷企業靈魂的,卻是一羣深受嬉皮文化影響的狂熱分子。
喬布斯這一代最終爲美國創造了新的秩序。從垮掉的一代人到時代的引領者,嬉皮士們在戰後美國的建制中絕望,又從廢墟中創造了新的未來。與此相似的,是八十年代的日本“新人類”。
有一本叫做《飽食窮民》的書,描寫了日本1980年代白領們那種殫精竭慮工作的場景,有一個情節是爲了完成KPI,員工居然去借高利貸來衝刺業績。比我們今天碼農們的996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這樣內卷環境里長大的新一代日本年輕人,最終選擇走上了一條類似美國嬉皮士的道路。

1986年《朝日新聞》的王牌主持人筑紫哲策劃了一欄與二十歲左右年輕人對話的節目“新人類的旗幟”。天命之年的文化精英與新人類敞開心扉的促膝長談,一經推出就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新人類”一詞在當年的流行語評選中斬獲頭名,成爲長期的社會熱點。
新人類不再試圖通過向公司奉獻自己的人生來實現人生價值,他們更願意自己定義生活的意義,不再被宏大敘事所捆綁,決意要過自己的人生。這跟美國嬉皮士背後的社會學機理是相近的:就是社會在經歷了一輪快速的發展後,人們不再需要爲了基礎的物質需求而奔波。
這樣的環境裏,要求年輕人按照過去那種循規蹈矩的方式去上班,是不切實際的,這其實就是國家提出“靈活就業”的大背景。
今天中國的95後00後們無疑是幸運的,他們對於工作有了更多選擇的餘地,他們那些父輩兄輩們,在人生路徑上並沒有那麼充裕的選擇空間,往往是隨波逐流的就業,用魂縈和房貸把自己套上,然後勤勤懇懇的工作一輩子。某種意義上,這種人生的確不是當代年輕人想要的。
充滿“爹味”的東亞社會,不應該一方面羨慕着谷愛凌的成長軌跡,一方面對年輕人的選擇嗤之以鼻。
尾聲:一代人是一代人的橋
2008年,HBO製作了一部只有7集的美劇,叫做《約翰·亞當斯》。
約翰·亞當斯這個名字對中國人來說可能略顯陌生,但在美國可是家喻戶曉,跟我們熟悉周總理差不多。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是美國第一任副總統(總統是華盛頓)和第二任總統,另外他的長子約翰·昆西·亞當斯是美國第六任總統,可謂四世三公,朴正熙看了羨慕,老布什直呼內行。
這部美劇貫穿了大陸會議和獨立戰爭等重大事件,呈現了美國從1770年-1820年之間波瀾壯闊的歷史,堪稱美國版的《建國大業》。講述偉人事蹟的主旋律影視作品,按道理反響應該一般,結果上映之後火爆全美,IMDB評分8.6,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豆瓣網友打了一個9.1的高分。
電視劇裏有這樣一段場景:獨立戰爭期間,亞當斯作爲特使來到法國爭取援助。那時的法國正值路易十六時期,奢靡成風,接待他的法國貴婦人問他:“亞當斯先生,你對歌劇和舞蹈有什麼樣的研究呢?”亞當斯慚愧的回答:“沒有任何研究,因爲沒有時間。”然後他話鋒一轉,講道:
我還要研究政治和兵法,讓我的兒子能在自由的環境下,學習數學和哲學;我的兒子要鑽研航海、貿易和農業,好讓他們的後代,有權利研習繪畫、詩歌和音樂。

一個落後國家(相對於當時的英法)的慷慨立志,引起了全場爲他鼓掌。但作爲一箇中國觀衆,我從這段話裏強烈感受到的一點就是:每一代人都是下一代人的橋。
消失在大猛子視頻裏的年輕人,可能出現在更多的新行業裏,這些新的崗位新的職業的基礎,就是上幾代人修的路、搭的橋。網店商家、主播、up主、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等新崗位,都是歷史進程的產物,那些提供這些新崗位的B站、快手、美團等公司,也只是順應了歷史潮流而已。
就像黃崢談消費升級那樣:“消費升級不是讓上海人去過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讓安徽安慶的人有廚房紙用。”同樣,就業的升級,也不是讓藍領勞工學會寫Python和算法,而是讓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人能夠多幾條出路——即使有侷限性的選擇,也是選擇。
一代代人的前仆後繼,不就是爲了能讓年輕人有選擇的權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