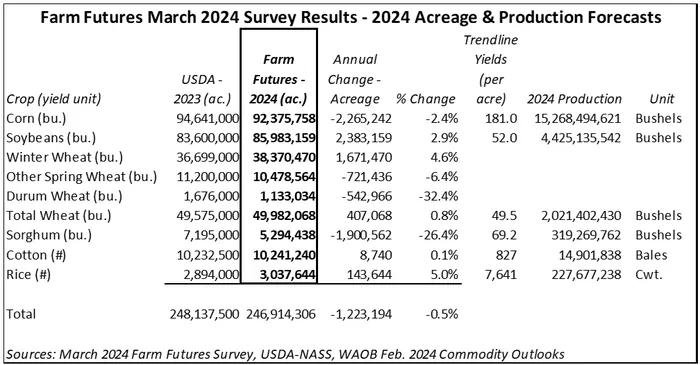韓長賦: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始終尊重農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

全國政協經濟委開年首場集體學習,聚焦土地與農民!
——圍繞國之大者,委員們這樣說
《 人民政協報 》
文/圖 本報記者 崔呂萍
2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發佈。這是21世紀以來第19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
就在中央一號文件發佈5天前,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分黨組2022年第一次集體學習暨“經濟增長的中國經驗”讀書羣線下交流會在全國政協機關小禮堂舉辦,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分黨組成員、副主任韓長賦就中國特色農村土地制度做了專題報告,多位與會委員做了互動交流。圍繞土地與農民那些事,一起來看他們是怎麼說的。
■委員開講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韓長賦: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始終尊重農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
韓長賦表示,中國特色農村土地制度,其基本內容包括土地集體所有、以農戶爲單位平均分享集體土地權益、以市場爲導向優化土地資源配置以及土地制度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中國特色農村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直接影響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直接影響農村財稅制度演進的方向;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直接影響鄉村治理方式。
“中國特色土地制度的優越性,則體現在三個方面,包括適合農業特點,有利於農業生產發展;符合國情,有利於農村和諧發展;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韓長賦表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有過不少重要論述,韓長賦認爲,從中我們可以提煉出“九個堅持”,即堅持以土地制度改革爲主線,推動農村改革;堅持集體所有制不動搖;堅持家庭承包經營不動搖;堅持長期穩定土地承包關係;堅持實行“三權”分置;堅持多種形式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堅持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堅持改革底線。
關於正在探索和推進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韓長賦提出,首先要搞清楚當前關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在他看來,主要目標可以分爲5大類,即產權關係明晰化、農地權能完整化、流轉交易市場化、產權保護平等化以及農地管理法治化。
韓長賦同時強調,要明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這裏包括始終把握與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始終尊重農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始終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始終助力好穩定與放活的關係;始終注重漸進性改革,保持歷史耐心。
在韓長賦看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還有10項具體任務,包括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落實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帶動小農戶發展;推進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探索建立土地承包權退出制度;強化耕地保護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徵收制度;健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穩慎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及改革完善土地出讓收入使用制度。
■互動討論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
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動搖
現行的二元土地制度是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表現形式。在現有體制下,城鄉要素循環基本上還是農村勞動力、土地收益和資金向城市單向流動的循環模式。近年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試點推進,但也遇到了不少問題。
第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新的實現形式問題。比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如何界定?土地權屬變更需要一人一票,但很多農民已進入城市,如何避免土地過度集權化,使權益向少部分人集中?如何正確引導土地股份合作制發展?
第二,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問題。宅基地流轉要不要擴大範圍,如果流轉範圍不擴大,城市資金便很難進入農村。而擴大流轉範圍,很多人又擔心農民會不會居無定所?還有宅基地使用權流轉期限如何規定?
第三,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問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對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有重要意義。現在強調,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條件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同權同價、同等入市,但在實踐中如何實現同權同價?如何擴大農村集體性建設用地入市範圍,並完善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機制?
第四,進城落戶農民承包權退出問題。在沿海地區、大城市周邊地區承包地流轉已形成一定規模,但“進城不棄地”仍大量存在。中央明確提出,要支持引導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願有償轉讓承包地,但實際進展並不明顯,如何增加制度供給,有效激勵進城落戶農民退出承包地,促進農業規模化經營?
上述問題都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找到答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農村經濟的“魂”,不管怎麼改,不能把集體所有制改垮了,這是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須遵循的原則。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創造條件實現農地有序流轉
這麼多年來,農民進城推動了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大家經常認爲土地很緊張。需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城市化進程到底是在節約土地還是在浪費土地?僅從居住角度看,農村居住比較分散,進城後人員集聚性提升,城市化進程應該是節約了土地。當然,實際情況可能並非這麼簡單。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要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能夠流轉。但也有同志擔心,如果農民宅基地出讓了,有些農民會拿着宅基地出讓得到的錢去喝酒,錢花光了,居無定所,會出現社會不穩定。
這種假設確實造成了困擾。曾經遇到一位縣委書記,他說這麼多年在農村工作,深感中國的農民個個都是經濟學家,賬算得很細,拿自己家宅基地換錢喝酒的人應該很少,而且這種人不僅農村有,城裏也有,但城市裏並沒有因爲這種人存在,就不交易房子了。過去我們認爲,土地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承擔着社會保障的功能,特別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很多農民返鄉了,大家說,還得靠土地。這句話當時講是對的,但這些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普遍建立起來了,我們已經有了能夠爲農民提供安全網的更有效率的辦法。應該也完全可能用這種新辦法爲農民提供保障,同時把土地這種稀缺資源解放出來,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還需要說清楚的一個問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不能交易,價值是要打折扣的。我們經常說要保護農民利益,但又不讓土地流轉,農民在土地上的這個利益是多少並不清楚,又談何保護?目前宅基地流轉只限於本村甚至是本居民組範圍內,但更多的需求是來自外部,來自縣城、省城甚至一線大城市。重要的是應該把農村土地流轉、交易的權利還給農民,他們有了這種權利後,不一定非要轉出去,轉還是不轉,由他們自己算賬後做決定。
因此,如果我們真正要保護農民利益,首先要創造條件,使農民擁有自主轉讓權利,土地的市場價值能夠得以顯示。同時,土地使用權轉讓後的收益,首先要用於爲相關農民完善社保體系,包括住房保障條件,並由此帶動城鄉之間在生產生活、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融合發展。
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
解決好爲農民謀利的問題
去年全國兩會後,我到一個村調研,這個村位處淺山丘陵地區,面積12.8平方公里,2000多人,4000畝稻田,2000畝旱地,1萬畝林地,應該說土地資源還算充裕。許多人出去打工了,脫貧之後爲了使生活更好一些,也要從地裏增加些收入,因此就種優質稻,想在村裏建個小型加工廠,但沒有建設用地。
村裏有個養豬好手,之前在水庫邊上養,怕把水庫污染了,想着把這個養豬場搬出來,也找不到建設用地。其實在農村,荒山荒坡不算少,未利用地也有,大家都說要延長農業生產鏈,把加工留在當地一部分,但真做的時候又辦不成。有的地方,農民出去打工了,一些地撂荒了,一些地栽上了樹,很是浪費。我的感覺是,土地制度不是理論問題,最根本是要解決實際問題,既要嚴格管理,又要擔當作爲,研究解決好如何爲農民謀利的問題。
另外,在我國主要的農產品中,國產食用油自給率低,保供安全性差,是需要補齊的短板弱項。油料作物不能只在地裏種,還要積極發展木本油料,在荒山荒坡、田邊地角、房前屋後都可以種。發展木本油料,一個大的瓶頸就是用地不足。這件事,涉及多個部門,建議統籌考慮,做好頂層設計。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農民致富要有自我造血機制
新的文件規定,土地出讓收益用於農業農村比例達到50%以上,真正實現“取之於農、主要用之於農”,推動農業農村發展。城市裏的農民工也是農民,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等問題,逐步實現農民工的同城待遇平等化,也應當納入“三農”的範圍。土地出讓金要如何用在農民身上?如果不從農民工市民化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只是固化思路認爲農民只能待在農村,農民工遲早要回到農村,那麼“三農”問題沒有出路,城鄉二元結構的扭曲無法得到緩解,還會影響到潛在經濟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我國的發展潛力取決於55%的農民市民化的進程以及如何市民化,這個問題深度影響內需和供給能否形成良性循環。
如果農民擁有的土地權能(承包權、經營權、使用權、資格權等)不能交易、不能貨幣化、金融化,則“三權分置”改革的意義大打折扣,難以給農民帶來實際價值,農民增收、農民市民化都會擱淺,農民的美好生活願景——生活得更好,下一代不再當農民等,都將難以實現。因此農村的問題必須與城市的問題關聯起來統籌考慮,逐步形成城鄉全國統一市場。
現在農民日子過得比過去好多了,我回村裏去看,感覺大家幸福感、獲得感滿滿,但對如何增加收入的前景並不樂觀。還需看到,當前農民收入中有一部分來自財政轉移支付,也就是補貼,這種補貼不可能長期存在,打工收入也遇到了天花板,缺少技能,打工機會也在減少。因此,農民致富必須要有自我造血機制,這就需要與城市保持聯動,可以說,農民羣體未來最大的公共利益是市民化,這是當下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民工的願景,也是廣大農民的下一代的願景。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