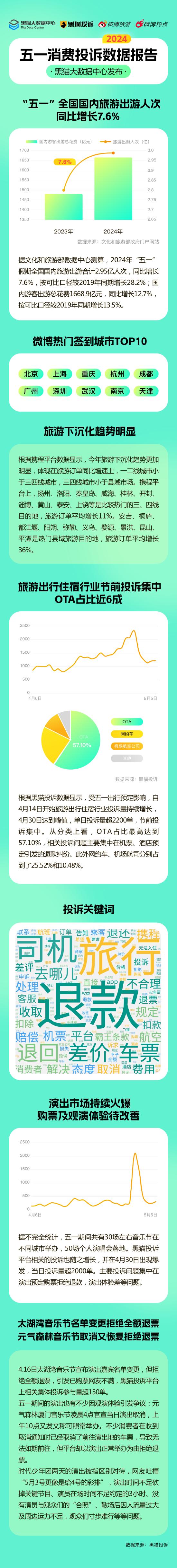手錶成了孩子的“社交神器”?有家長很無奈:一怒之下摔了,被迫又買新的
從盲盒到奧特曼卡牌,
小學生的社交硬通貨
永遠在追逐新鮮的玩意兒,
但鄙視鏈頂端,
還是屬於小天才電話手錶。

年輕人聽了費解,小學生聽了興奮,家長聽了焦慮,這種專門給小孩子用的電話手錶,很少能被人持續用到初中以上,卻憑藉着對手機的替代功能,佔據了小學生社交的半壁江山。
很少有家長能拒絕孩子“買手錶”的需求,它看起來無比的正當——既給忙到不能接孩子放學的家長一個定位的心安,又不至於擔心孩子被網絡的花花世界吸引,一鍵禁用的功能躺在家長的手機裏,擊破着他們的心理防線。
然而,隨着手錶配置和價格的雙重升級,它似乎正在背離初衷,從方便通話,到成爲小學生社交新寵,依賴它的不止有小學生,還有家長。
前腳砸完小天才後腳給兒子買最新款的故事正在杭州上演,或許困擾着家長們的不止是一個電話手錶,還是親子之間那根敏感的邊界線。
“傷痕累累”的錶盤和最新款手錶
一塊傷痕累累的錶盤,是陳詠和兒子鬥爭的印記。
2019年,陳詠的兒子小陳上二年級,沒有“雙減“,小陳的週末只有輔導班。彼時的輔導班上,已經有大半的孩子戴着電話手錶上課,下課間隙,兩個手錶碰一碰,便加上了好友,比微信還要更方便。
被輔導班的家長推薦了一下,陳詠第一次知道了小天才,顯示位置、打電話,陳詠覺得有了它,讓兒子自己上輔導班也沒問題。在他的理解中,小天才是用來學習的,和曾經流行過的步步高異曲同工,總比直接給兒子手機更好。
那年生日,小陳就擁有了第一款電話手錶,型號是Z5,除了最基本的定位等功能,還可以在手錶上玩拼寫答題遊戲,學英語,背古詩,陳詠充了一些錢,希望兒子至少能學到些知識。
家裏的電視被陳詠拿去回收站了,電腦設置了密碼,只有陳詠夫妻倆知道,沒有娛樂設施,小陳只有手錶。陳詠動了惻隱之心,週末和假期時不開啓一鍵禁用,這也就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偶爾陳詠不在家,他在監控裏看到,小陳盯着手錶,一看就是幾個小時,偶爾和同學發語音,用手錶答題闖關。警告幾次,小陳依然很難把目光從那個小錶盤裏挪出來,甚至連喫飯也不願動身,一怒之下,陳詠開始摔起了手錶。

手錶被摔在家裏的地板上,小區旁的花壇裏,屏幕碎了補,補了碎,每一次怒不可遏地摔手錶都不能阻止小陳重新擁有它,因爲陳詠知道,他自己也開始離不開它。
“有時候我們夫妻倆都是晚班,沒人接孩子,只能讓他自己坐公交回家,但我們又擔心他的安全。“陳詠有些喪氣,他習慣了兒子用手錶打電話報平安,潛意識裏,也不希望逼着兒子,他總是希望小陳能自己掌握好學習和休息之間的尺度,卻每一次都大失所望。
一個月前,重新被修好的屏幕再一次因爲小陳的持續沉迷被陳詠摔碎,“那天叫他跟我出去喫午飯,他在玩手錶,和好友語音不停,我又叫了他一遍,他放下手錶開始充電準備跟我去喫飯,我走到樓梯口等他很久,一直沒跟上來,我回家一看,他還在玩手錶,然後我就火了。”
這次,整個手錶都壞了。陳詠向老婆發誓,這次再也不修了,也不買了。在老婆“以後我接不到孩子怎麼辦?他聯繫不到我們怎麼辦?孩子丟了怎麼辦?”三連逼問下,夫妻倆沉默妥協。
摔完手錶一小時後,最新款的小天才電話手錶又被陳詠買回了家,他內心複雜,孩子看到新手錶,眼神一下子發亮,“爸,你不會有什麼陰謀吧!”陳詠不知道自己這個決定是對是錯,因爲當他企圖教小陳如何使用最新款的功能時,小陳搶先說了句:“我知道怎麼用,班上早有同學買了最新款,要2000塊錢呢。”
過於“好玩”的電話手錶
電話手錶的流行之風也從週末的家裏飄到了學校裏,沈括小學的高瑤瓊老師前一段時間發現,班上的孩子總是神神祕祕地聚在一起研究着什麼東西,湊近了一看,原來是一位同學的生日禮物——最新款的小天才手錶。

學校不建議帶電話手錶到教室,但是高老師想給孩子們充分的討論空間,“電話手錶能幫助我們做什麼?我們需要手錶那些功能嗎?”在班會上,高老師拋出問題,一部分孩子提出的手錶種種功能,又被另一部分孩子一一給出替代辦法。最後大家一致得出結論,帶手錶到學校,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老師的引導總是有說服力的,現在高老師的班上,已經幾乎沒有人會帶電話手錶上學了。但在那些老師管不到的週末、親子時間、假期,小天才依然是小學生社交的必備之物。
只有兩個小天才之間碰一碰才能加好友,這樣的功能無疑是在孩子們之間形成了社交屏障。專做博物館活動的張天老師說,每次週末帶着一羣小學生去博物館,他們都會聚在一起碰手錶,這是孩子們的固定項目,不知不覺中,沒有手錶的孩子被排除在外,無論是孩子還是家長,心裏都不是滋味。
從商業角度看,小天才作爲電子產品,走上更新迭代之路不可避免,勢必會增加各項娛樂功能,雖然在宣傳上一直堅守着“不能玩遊戲”的底線,卻在實際功能上,設置了和遊戲機制一樣的闖關,以學習知識爲名,讓孩子逐步沉迷其中。
陳詠發現,小陳經常匆匆跑來向他詢問一些問題,得到答案後又迫切地輸入,答案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積分,闖關。
“這種機制本質上和遊戲沒什麼不同。”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孫繼軍醫生解釋。答對問題,通關,本質上是一種容易獲得的快樂,而人本身就會對容易獲得的快樂陷入沉迷,不僅孩子如此,就連大人也無法避免。
一個屬於孩子的“私密空間”
“我只給孩子買最基本款的小天才,限制他每個月的流量和花費,迴歸最開始買這款手錶的初衷。“張天說。她的孩子今年小學四年級,她也因爲小天才和孩子發了幾次火,原因都是孩子出門不帶手錶,有什麼事情都沒辦法第一時間找到彼此。

雖然張天所在的學校已經嚴格禁止孩子帶小天才到學校,但她還是聽了不少家長的吐槽,孩子沉迷小天才沒有自制力,同學之間攀比小天才款式。張天認爲,技術本身並沒有錯,家長如何把握比較重要,“那些附加的功能真的那麼必要嗎?真的需要把定位精準到某個樓層嗎?我會去思考這些問題,適當替孩子做決定。”她說。
表面看,孩子沉迷於小天才,是因爲其背後引導成癮的機制,實際上,小天才已經成爲小學生們不可多得的一個“私密空間”,有時家長過度的介入,也會適得其反。
孫繼軍醫生分析,具備聊天交友音樂等功能的小天才手錶,已經是孩子獨立意識的重要載體,“平時出去是自己戴,能從手錶裏獲得平時不常有的快樂。”孫繼軍自己的孩子在讀五年級,也會頻繁使用電話手錶,討論手錶的新功能。
“這是一種成長的意識,可能一些孩子的家庭關係不是特別理想,或是有一些情緒問題,他就會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手錶上,在手錶的世界裏,他是可以自主掌控的,也是自由的。”孫繼軍說。
陳詠也能感受到兒子“掌控手錶的自由”,他想起小陳自己坐公交車時,遇到了前方公交車着火事故,便立刻打開小天才的攝像頭向他實時直播近況,有時也會用小天才唱歌,發動態,那些瞬間小陳都會露出難得的笑臉,這或許也是陳詠一次一次摔壞手錶,又一次一次買回來的原因。
“父母總是希望能和孩子成爲朋友的,對他們充分尊重的。”陳詠說,與其說是“小天才”捆綁了他,不如說是他仍然沒有找到和孩子之間更舒適的溝通方式,他曾經刪掉了兒子手錶裏所有的聯繫人,又默許兒子一個一個把他們加回來,他始終在探索如何能引導小陳減少對小天才的依賴,也在和兒子的“鬥智鬥勇”中,不斷自我反思,雙向成長。
來源: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劉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