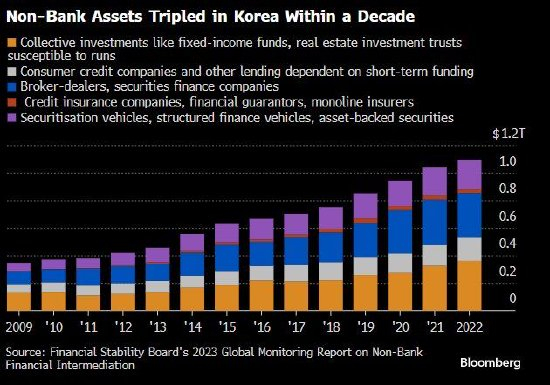大咖七日談︱張軍:最大挑戰在於如何擺脫宏觀失衡困擾
初步覈算,2023年全年的GDP錄得5.2%的同比增幅,確實不易。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這其中有4.3個百分點是消費支出的強勁反彈貢獻的,貢獻率高達82.5%。這意味着消費支出實現了接近兩位數的增長。而總的投資僅增長3%,是因爲,儘管電器、電子和汽車等行業的投資增長較快,但房地產投資下降了接近10%,基建投資也比上一年下降了3.5個百分點。雖說這些信息反映出的變化帶有疫情平穩轉段之後的特殊性,但如果未來中國的GDP增速真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這樣的格局,那我們的經濟在宏觀上就真是實現“再平衡”了。
當然,這只是假設,我們的經濟離開“再平衡”的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2023年家庭消費支出出現V型反彈,跟疫情期間受到的抑制有直接的關係。但我們也要看到,新冠三年,家庭收入的增長軌跡相對原來的趨勢有所偏離,收入預期有所下降,這會影響未來幾年的消費支出,尤其是在消費支出節奏正常化之後。所以,基數效應衰減之後,2024年的消費支出增速大概率會比2023年放慢,除非我們加大對家庭收入的支持力度。
我們看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疫情期間通過財政政策加大了對家庭的收入支持,家庭反而提高了平均收入和支出能力。而中國在疫情期間沒有啓動大規模的家庭收入支持計劃。疫情轉段之後,大多數家庭的收入預期降低了,大多數中小微企業和工商個體戶受疫情衝擊至今面臨較大的生存壓力。考慮到這些變化,2024年及之後幾年,政府若能啓動大規模支持和提升家庭收入的計劃,以取代更多的基建投資支出,財政政策的支出向家庭傾斜,幫助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緩解不斷加強的預防性儲蓄傾向,家庭消費支出增速放緩的趨勢則有望得到糾正。
疫後經濟恢復,宏觀政策要提振國內需求。當下到底主要靠鼓勵更多的投資支出,還是鼓勵更多的消費支出?不可能不要投資,但政策上要鼓勵的主要應該是企業設備投資和一些重要的更新改造投資。總體上,存量大和邊際回報率過低已經制約了啓動大規模基建投資的機會。雖然基建投資在過去爲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今天的邊際投資效率已經很低,對拉動需求的倍數效應也很小,增量資本產出比居高不下。而宏觀經濟在過去這些年來已受到過度投資和宏觀比例失衡的困擾及債務拖累,也是事實。
事實上,這些年央行創造了很多新的釋放流動性的工具,強調了政策精準和差異化,用於支持投資的信貸投放和流動性相對還是充裕的,只是在試圖避免過度刺激投資的重演。我們看到投資增速也因此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一些新興行業的投資增長較快,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相對之前慢了下來。考慮到地方大多數基建投資的邊際效率不高,財務上難以收回成本,控制基建投資節奏總體上是利大於弊的。現在不具備2008年的條件,確實難以再啓動大規模的基建和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難以再像當年那樣過度借貸。中央暫停一些地方基建投資總量的擴張在短期是必要的,這些地方已負債累累,要鼓勵更多的預算支出去幫助家庭彌補收入缺口,幫助恢復當地中小微和個體工商戶重回市場,恢復其經營,恐怕眼下比一味地支持大規模基建投資項目更重要。
由於地方政府的過度舉債在一定程度上已制約了其支出擴張的能力,這就需要國家從整體上考慮未來的解決方案。我認爲,在這方面,中國是有條件也有能力解決的。中國現在主要的債務風險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方面。儘管債務規模不小,不過目前來看,這些債務積壓對經濟造成整體衝擊的可能性非常低,一方面中國不像日本,銀行不參與交叉持股,金融傳導的渠道狹窄,另一方面,這些年國家金融監管的首要任務一直是防止系統風險的形成,債務風險總體上被隔離在不同行業和地區的局面已經形成,局部的風險不大可能釀成全局風險,所以不會像日本那樣形成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現象。中國要減輕債務對總需求的拖累,需要儘快對債務存量明確給出一個重組方案,亮出底線,用底線和透明度來消除市場的恐慌和遲疑。而從長計議,中國需要修改三十年來的政府間財政關係,建立起一個符合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的收入與支出體制。現在可能是醞釀出臺新一輪政府間財政改革方案的時間窗口。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未來的支出向家庭傾斜也是必然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依靠房地產和拍地收入來支撐基建投資。房地產市場的形勢發生了階段性改變,分化嚴重,除了一線城市之外,未來即便政策復原,房地產市場再次進入繁榮長週期的可能性也極小。現在政府要抓緊將探索多年的房地產長效機制制度化,在土地、金融、稅收和收入政策上協同一致,構建形成一個房地產可以穩定發展的格局刻不容緩。
從跨國的數據很容易看出,我們的家庭消費支出在總需求中的佔比,以及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都遠低於全球的平均水平,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更大。這其實是過度投資體制長期形成的結果,因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而產生,成爲我們經濟面對的慢性病。過度投資雖然在短期可幫助平衡總需求與總供給,但中長期會惡化兩者的不平衡。所以,宏觀經濟失衡的根源也在這。過去,中國成功依靠出口和投資主導的模式實現了快速的資本積累和經濟追趕,但作爲大國,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後,中國難以像德國那樣長期保持對出口的依賴和貿易盈餘,從這個意義上說,降低國內儲蓄率和維持國內消費需求的繁榮是通向經濟發展持續性的必由之路。
長遠來看,要促進家庭消費支出的合理增長,中國需要允許名義工資有更快的增速,至少也要保持不低於名義GDP的增長率。工資增長緩慢在宏觀上也牽制了價格水平的靈活性。這些年宏觀經濟的一些指標,包括價格指數,扭曲的情況遲遲沒有得到矯正。由於價格機制受到長期干預,基礎產業的價格,包括受管制的服務領域,比如能源、交通運輸和城市基礎服務的價格等,長期變化幅度很小,若能允許更多的市場化,緩解價格扭曲,市場機制的調節會更有效消除一些宏觀失衡,而且可以與工資形成相互影響的關係。這樣的話,CPI、PPI回到更真實的起點,而不再有較大失真成分。現在中國的CPI構成中,不僅家庭居住支出低估,而且像服務品價格、食品和能源價格等受到國家不同程度的管制較多,缺乏靈活性,導致CPI的變化可能被長期扭曲和被低估。
與大多數人的看法不同,我認爲中國相對於很多國家來說,經濟活動遠比我們認爲的要更分散,地方色彩更濃厚。這有好處,也有弊端。在未來相當時期裏應該是利大於弊。因爲經濟活動更分散,地方上的差異很大,所以面對同一個衝擊,整體上的傷害不太可能很大,也很容易被格式化。競爭一直在,不受管制或管制不到位的局部空間一直有,這解釋了爲什麼這些年的各種衝擊這麼大,中國經濟依然沒有出現劇烈失速,在有些領域,像新能源和電動車行業,還能獲得超常的擴張機會。如能將地方政府面臨的激勵調整到正確方向,更多的決策和裁量權從部委下放到地方,制度上設置更大的容錯空間,完全可以期待地方上有更多的政策創新、更多的市場化改革和對經濟變化更直截了當的回應,我相信中國經濟依然會凝聚來自底層的創業和創新活力,獲得克服短期困難和挑戰的勢能,繼續回到和保持穩健增長的勢頭。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