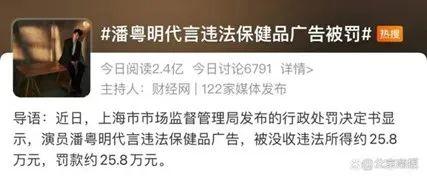商人郭德綱往事
這一次,德雲社的紅,與李菁出走不同,與曹雲金和師傅郭德綱對罵不同,與小嶽嶽賤萌的河南style不同,與張雲雷點燃一個個少女心深情唱着《探清水河》不同……
郭德綱的公關戰
大家都知道了,這兩天老郭的徒弟吳帥(藝名:吳鶴臣)因腦溢血住院,在“水滴籌”上發起100萬元的籌款。劃個重點:吳家在北京有兩套房產、一輛車,以及15萬元存款。
當這幾個“重點”被描紅加粗後,可想而知公衆的憤怒:那麼多家在邊遠山村一貧如洗的家庭,在親人身患重病時都無法得到援助,德雲社一個在北京已安家立業享受醫保的相聲演員,得了腦溢血就要伸手向大家要個100萬,憑什麼?
臺上,你是演員,相聲說得好了,大家自然要給你掌聲;臺下,德雲社的光環不該被當做籌款的籌碼,對不起,大家只能救急不救窮。
徒弟要救,德雲社的牌子更要保。
眼看着口水聲吞沒了多年積攢的掌聲,德雲社發佈了“關於吳帥(藝名:吳鶴臣)病情及若干問題的聲明”,表示公司已開展內部募捐,公司及郭德綱本人將繼續提供一定的經濟援助。吳帥有北京醫保,之前吳帥之妻發起的衆籌系其私人行爲,受捐款項將按平臺規則由平臺方直接劃入醫院賬戶。
很多公司都應該來學習一下,老郭的這波公關回應玩得6:首先,告訴大家德雲社內部已經先捐了,除了公司捐錢,作爲師傅,郭德綱還會另掏腰包;其次,徒弟向大家籌款這件事,德雲社事先根本就不知道,純屬個人行爲。
撇清責任,同時於道義上予以援助,有理有情。
其實,從德雲社的回應還是能看出來:簡單利落,不會被公衆牽着走——回應要有,但儘量少說話,等下一個熱點來了,德雲社的風波自然也就過去了。畢竟瓜太多,大家都是很善於遺忘的。
郭德綱不是不會說,還記得上回他與曹雲金大戰故事嗎?曹雲金小學生水平的流水賬哭訴,被師傅6000字長文,秒得渣都不剩。
郭德綱知道什麼時候該說,什麼時候不該說。在筆者眼裏,德雲社是一家公司,郭德綱就是那個運營者。
德雲社每個人都是IP
師徒制、班社制,這是郭德綱運營德雲社的思路,也是馬克思口中的行會制度,這種制度不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本質上是一種落後的生產方式,阻礙再生產和資本增值。
可德雲社偏偏在這種制度下,生存了24年。經歷了創始人李菁出走、當紅弟子何雲偉離職等連環暴擊後,德雲社依然穩固,經受住了市場的考驗。
“別的不敢說,相聲界,我讓誰紅,誰就能紅!”老郭這話真狂妄,可他沒吹牛。甚至,“我說你幾時紅,你就幾時紅。”
郭德綱敢於這麼說,是因爲他的一套捧人招數已經爐火純青了。這一招,最開始是拿他自己練的。
德雲社,小黑胖子,于謙的爸爸,這是郭德綱走紅後,大家在他身上貼上的標籤,別忘了,這些標籤都是郭德綱本人早年在相聲演出中,一次次輸出給大家的。
他深知自己、于謙、德雲社,都是一個個產品,既要當產品經理,又要當運營專家。
德雲社每一個人都有標籤:
于謙:抽菸喝酒燙頭,郭德綱最親密的異性朋友。
岳雲鵬:五環之歌,保安,河南話。
張雲雷:二爺,高空跳傘無傘運動員,鋼釘,演唱會。
郭麒麟:德雲一哥,少班主。
曹雲金:德雲四少之一。
張鶴倫:無所謂,心態,一乃乃(一聲)。
徐德亮:北大中文系高材生。
標籤貼上了,也就紅了。注意,標籤可不是呼啦一下挨個全都給貼上,要集中精力先貼一個,用貼好的這個再去帶下一個。不信?你看看老郭主持的《歡樂喜劇人》:岳雲鵬成爲冠軍之後,開始爲師弟們助演。
最後,大家都紅了,而且紅得還不一樣。百花爭鳴的,真好。
這個套路也被其他喜劇團隊模仿,小瀋陽、宋小寶爲代表的遼寧民間藝術團,沈騰、馬麗爲代表的開心麻花,抄襲的全都是老郭“一個紅了就帶下一個”的運營思路。
細看老郭給徒弟們貼的一個個標籤,主旋律都被“屌絲、沒文化、接地氣”這些關鍵詞包圍。對於徒弟們氣質這一塊,老郭可是拿捏得死死的。
這樣的標籤有啥好處?
好處大了,以遠遠不如你的姿態,激起你的同情心,順勢迅速俘獲你的心。這樣,在出現負面的時候,也不至於被罵得那麼慘烈。
2017年12月,岳雲鵬被錘上海出軌了辣妹。這個新聞在當時毫無波瀾,連路人都不怎麼相信。
因爲在大家心中,岳雲鵬是春晚上能被“鐵錘妹妹”騙到的老實人啊!是《保安隊的日子裏》剛到北京龐各莊的小保安啊!他是個十足的大loser,怎麼可能幹出這種事?
終於發現了吧,老郭不僅公關玩得6,IP玩得也很6。
回頭看看前段時間非要玩學霸人設的翟天臨,就是因爲給自己貼的標籤太高,才摔得太狠了。玩人設動不動就翻車的明星們,真的應該去郭德綱那裏進修進修。
也曾大戰師傅
何雲偉、李菁、曹雲金、劉雲天……見到這些人名字,恐怕郭德綱都會心生齟齬。
尤其是曹雲金,成了郭德綱口中“欺師滅祖之人”。但老郭忘了,他自己也不乾淨。
1989年,16歲的郭德綱拜時任天津市紅橋區文化館館長、著名相聲演員楊志剛爲師學相聲。
“師兄們都能感覺到,師父最偏愛這個小師弟,對其也是傾囊相授。有次楊志剛生病住院,文化館念及郭德綱與楊志剛既是師徒,又是同事,派郭德綱去陪牀看護。郭德綱便日日夜夜守在楊志剛牀前,楊志剛就在病牀上給他‘說活’(講解相聲),至少教了他二三十段活。”
那時的楊志剛,估計怎麼也沒想到,這個愛徒會在日後把自己摁到了泥裏。
2004年,郭德綱攀上了更高的枝,拜了侯耀文爲師。至此,郭德綱再也沒有提過楊志剛半句。後來,侯耀文也成爲郭德綱口中“唯一的師傅”。
轉拜別人爲師,與打自己的臉無異。
2006年,楊志剛在接受採訪時爆出猛料,披露郭德綱早年模仿領導簽字報銷個人費用,是自己想盡辦法才讓他免於刑事責任,但沒想到郭德綱又偷拿單位行頭,讓楊志剛徹底覺得“這個徒弟我保不住了”,於是這纔有了郭德綱咬牙去北京的故事。關於郭德綱咬牙去北京的事,下文會細說。
往事被曝光,郭德綱隨即發表博客文章《我叫郭德綱》,承認了“僞造”一事,但又稱楊志剛“家中裝修公款報銷”“整郭德綱逼其掃廁所”“與女同事同居”,頓時一片譁然。後來兩人對薄公堂,法院裁定郭德綱在文章中虛構了“公款裝修”“與女同事同居”等事,但因“情節不夠嚴重”,不構成誹謗罪。
最終,楊志剛還是輸了官司。
2016年,當問起郭德綱,楊志剛只是淡淡的一句:“我不認識郭德綱。”
不知在創辦德雲社的過程中,老郭是否傾囊相授,把自己那一段“欺師滅祖”的故事也都講給了徒弟們。
三戰北京
“你要上廁所要先和我打招呼啊,我們後臺人可比你多,關上門打你,你可跑不了。”這是郭德綱在臺上的段子,也是他的真實經歷。
郭德綱入行的時候,相聲行業非常蕭條,上世紀90年代,人們看相聲基本都是單位工會發票,如果掏錢根本不會去。
剛開始說相聲的青年郭德綱
與師傅楊志剛反目,行業也不景氣,種種原因讓郭德綱在天津待不下去了,而北京顯然更配得上他當時的野心。
然而,直到來北京,郭德綱才體會到了什麼叫人情涼薄。
“十冬臘月,大雪紛飛,大柵欄上連條狗都沒有。”這是郭德綱的原話。初到北京的郭德綱給豐臺一個小平劇團唱戲,管飯,沒工資。曾有一次他因演出錯過末班公交,於是壯着膽子問黑車:“大興走嗎?我沒錢,把懷錶給你吧。”
司機理都沒理。凌晨4點,郭德綱才走到家,腳上全都是泡,“我這眼淚嘩嘩地流了下來,這麼多年在北京就哭過一次。”
那時郭德綱22歲,發了高燒沒錢去醫院,只能硬抗。
曾經三次去北京闖蕩,想混出一番名堂。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沒錢沒名的郭老師只能先從基層做起,在各小劇場、小戲院唱戲、打雜、做零工,一有機會就創作、表演自己的段子。最慘的時候,他賣掉小靈通只爲換兩個饅頭。
爲了討生活,他到安徽臺做節目主持人,條件是在鬧市的玻璃櫃裏生活48小時。
郭德綱這天坐了十幾個小時的火車從北京到合肥,第一頓飯就是在玻璃櫃裏喫泡麪。或許是因爲略感心酸,他不禁發出感慨:“能享福,能受罪,不耽誤這一輩子……”喫完了晚飯,郭德綱繼續賣力表演舞蹈。
沒有風扇,衣服整個溼透,而且隔音效果很好,觀衆聽不見他說什麼,只能看到他亂動的身體和甩落的汗水。
堅持到30個小時的時候,郭德綱情緒崩潰了,幾度想要放棄:“這根本不是人乾的活!”可是看到觀衆給他在玻璃外的留言,他決定堅持,並完成了最後的挑戰。
對於相聲這件事,郭德綱執着。他從7歲開始學相聲,除了說相聲,別的什麼也不會。學成之後在“體制相聲”內找了個工作,不是沒人理他,就是被安排拉大幕。
別看郭德綱在節目中任由別人拿自己砸掛,那都是爲了節目效果,爲了運營他的德雲社。郭德綱自尊心何其強,他是受不了這等欺辱的。
成名後回憶起這段,郭德綱還狠狠地吐槽過一把:
“和你們一起穿個小西裝,抹個紅嘴巴兒,演一場一百塊錢,一個月兩千塊錢,我懇求你們收留我啊,生生是他們把我逼出來的呀。
但凡一個有文化的人,說‘讓他來’,留在手底下當個馬仔,我就認投了呀。
我願意給你當狗,你不要,你怕我咬你。你非把我轟出去,結果我成了龍了。”
給郭麒麟的家書屢提“江湖”
今年春節過後不久,演員何冰在《見字如面》上唸了一封“特別的家書”。該信全長僅952字,卻多次提到了一個詞——“江湖”。
“江湖險,人心更險。”
“既落江湖內,便是薄命人。”
“江湖子弟,拿得起來放得下。”
……
這是郭德綱在兒子郭麒麟18歲生日之際寫下的家書。
作爲一個在江湖的食物鏈中從最底端咬牙爬到“最頂端”的人,這封家書看似溫和如玉,但細品起來卻字字珠璣,背後是藏不住的嫉惡如仇。
“一入江湖深似海,從此節操是路人。”
“有人誇你,別信;有人罵你,別聽。”
“登天難,求人更難。黃連苦,無錢更苦。”
……
郭德綱曾說過一句話:“不知我的苦,就別勸我大度!”在成名後璀璨的路上,他沒有選擇和自己的仇恨和解。
名滿天下又譭譽參半,成爲郭德綱前半生的寫照。
還是簡簡單單說相聲就好,“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啪!”收音機裏傳來一聲響木,“我叫郭德綱!”